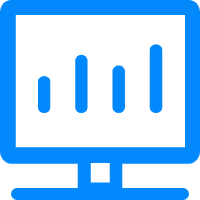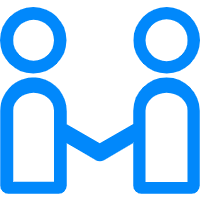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离世。章先生去世后,在诸多悼念文章中,使我们印象深刻的不仅是他的学问和思考,更在于他在不同世代所体现的风骨和精神。在今天这个时常追问何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的时代,章先生的生命历程和独立的人格,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
为了追忆章先生,我们特邀章先生门下弟子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博士后张晓宇先生撰写一文回忆他从章先生治学的过往。在这篇文章中,章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学者,也是一位如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亲切、随和的老人。他对晚辈后进的提携奖掖,晚年对历史与人生的思考,是他在教育和学术之外留给我们的另一笔财富。
撰文丨张晓宇
章开沅先生的办公室,就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的605室。
章开沅的办公室。
2012年9月,我来到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所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是章先生开创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升级而来,资料室在607,紧挨着先生的办公室。为了扶持中国基督教史这个相对弱小研究方向的成长,先生直至晚年都还在基督教史方向带博士生。2014年先生请辞“资深教授”,也不再招收博士生,我就这样极其荣幸地忝列于诸位蜚声海内外的学长们之后,成为先生名下最小的学生。
自我从法律转学历史以来,先生的鼎鼎大名即如雷贯耳。先生之治学和为人,早已是我们年轻学生心目中的典范。尤其是他在历史关键时刻无惧个人荣辱安危的抉择,更彰显了一个历史学家的风骨。2012年9月10日教师节上午,师兄王淼带我去605拜访章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心中甚为忐忑,生怕应答不当,给先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当得知我是山西人时,先生告诉我,他的先人节文公,就曾在山西为官,家族多人葬在太原。先生笑称,“山西也是我的家乡,我们是老乡啊”。随后又说,“我大哥的孙子也叫晓宇,名字和你一模一样”,紧接着先生又补了一句:“啊,我这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啊。”所在皆笑。这一下就拉近了距离,也消除了我的局促感。先生随后又跟我们讲了许多章氏家族的故事。那次见面只有短短二十多分钟,但让我记忆犹新,对我以后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生那时87岁,但身康体健,耳聪目朗,每天上午九点左右步行到办公室。彼时我自由散漫,迟睡晚起,经常是我到资料室时,先生已经坐在办公室许久了。先生一般是上午十点半左右步行回家,临走前还经常到607来转转,跟在资料室的小朋友们聊一聊。经常有海内外的学者来拜访章先生,刘家峰教授和刘莉老师负责联络和接待,我们学生端茶送水,帮点小忙。加之我三年学业中,还有不少文书需要麻烦先生签字,每次见面先生就顺带与我多聊一会,我因此而近水楼台,常得聆听先生教诲。
先生之教导
我在华师求学期间,学校后勤集团经常让学生搬家,三年搬了六次家,苦不堪言。2014年6月时,学校又进行宿舍调整,要求原来住在东区十栋的博士生全部搬入指定之过渡宿舍,再于9月开学时搬入新建成之国交三栋博士生楼。大家对此忧心忡忡,一来“秀才搬家尽是书”,重复搬迁未免劳顿之苦;二来东十本不在装修之列,无需过早清场。众人思量再三,决定联署向学校请求暂缓搬迁,但又因种种原因顾虑重重。那天我正好有事去先生家,遂向先生表达了一下我们的顾虑。先生阅完我写的请求书草稿后说,有意见向学校反映并无不妥,但要注意遵循合法渠道,表达合理诉求,尊重既有程序机制,逐级转呈。随后我们严格遵循先生的嘱咐,向东十宿管老师和我本人所在学院提交了请求书。后来我们与学校各级领导、老师的交流也比较顺畅,最后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我们的请求。这一事件也让我深刻领悟到了先生做事的智慧。彼时我正在研究晚清宗教自由请愿运动,这种经验也让我对先生所倡的“参与史学”,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诸多老师曾言及,先生年轻时颇严厉。而我从先生读书时,先生已经87岁高龄,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家了。有一次我去武汉机场接先生和师母,提早到了十多分钟,想着怎么打发时间,于是打开手机玩起了游戏。这一下不得了,激烈厮杀中,竟然忘记了时间,直到先生站在我的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才发现先生已经到了。此事我至今想起都颇为汗颜,他一定看到了那个贪玩误事的小子在做什么,可是他没有任何责备之意,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
先生对我的错爱和学术上的提挈,应该是在我写完湖州教案的文章之后。我博士论文是从近代国际法角度研究清末教案的,有幸的是,这一课题竟然让我与先生所关注的章氏家族史产生了一些交集。我在研究湖州海岛教案期间,发现该案中的湖州士绅领袖章祖申,竟然是先生荻溪章氏家族的第十五世先人。章祖申尚有一海外遗孤,为瑞典亲王罗伯特·章,先生曾专文论述。我本科学习的是法律专业,从法学到历史的转型也并非一帆风顺。求学之中的挫折只是一种外在的经历,最难的是如何将两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有效结合的问题。对于许多跨专业的学生而言,一种学科范畴上的“身份认同危机”如影随形——你始终要回答“我是谁”与“你是谁”的问题。湖州教案的文章写完后,我呈予先生审阅。先生以近九十岁之高龄,不辞劳苦阅完拙文后说:“尽管你以前不是学历史的,但是从这篇文章来看,你已经是入了门了,考证功夫算是做到家了。”他还跟我讲了许多章祖申的生平事迹。对于我这样一个历史学“半路出家”的学生而言,能得到先生这样的认可,我心中的感慨、感动难以形容。2015年初,我有幸入选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近代史研习营。临行前,先生特地签了不少书,委托我带给他在台北的老朋友们。先生额外还签了十本书,只写了先生的落款,未写抬头,对我说:“这十本书,你带上,方便结交朋友。”我后来才深刻体会到先生帮我拓展学缘的良苦用心!
2017年,我的学长陈新林博士在香港设立开源书局,先生鼎力支持,并把自己1990—1994年在海外访学期间的日记《北美萍踪》贡献出来,作为开源书局出版的第一本书。我有幸受先生和学长委托,帮助先生整理日记,为其中所涉人名、地名、事件作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先生交游广泛,日记涉及人物有几百位,堪称一部海内外中国史学人的“点将录”。且先生写日记时从未想过要出版,嬉笑怒骂,落笔无间,记述内容相当丰富,这也给考订增加了不少难度。除却邮件、电话联系外,我还经常为了解清楚先生日记中人、事的背景,往返于福建和武汉之间。只是我先前从未有任何出版和编校经验,第一次就以先生的日记来“练手”,过程中出了不少错误,校不胜校,也给陈新林学长和编辑杜一鸣兄添了不少麻烦。然先生待我实在太过宽容,从未责备于我。
先生与章氏家族史研究
章先生晚年一直推动两个研究,一个是先生的老师贝德士的研究,一个是先生的家族史研究。前项有徐炳三教授着力进行,后项现在由我来协助推进。与先生初次见面时所聊的内容,也成为我后来着手章氏家族史、企业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研究的开始。2016年12月,章先生转给我一封信,委托我查考他的外公徐襄甫的生平。先生一度以为徐襄甫在1911年前殁于四川,结果《王典章先生年谱》中的一则记载证实,直至1914年徐襄甫尚在安庆造币厂任职。得益于史学数据库资源的发展,我先通过“E考据”,基本勾勒出了徐甫陈(字襄甫)的生平,再先后前往四川省档案馆、宜宾市档案馆和安徽省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较为完整地还原了徐甫陈的一生。这一过程让先生甚为惊讶,他连连惊叹“E考据”的威力。先生就是这样具有开拓性、包容性,对学术界的新潮流保持着敏感度和接纳度。2015年,章开沅先生基金会曾邀请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来华中师范大学讲学,其中就有关于“E考据”的专题演讲。
对湖州教案的挖掘,也加深了我对先生祖籍地湖州的认识。2017年4月28日,我随先生、师母和马敏教授、田彤教授一同来到湖州,在先生的祖居地寻踪访古,也有幸结识湖州当地的多位学者和章氏宗亲。
2017年4月28日,章开沅先生与本文作者(张晓宇)等在湖州荻港村合影。
长期以来,关于章氏家族及其企业史的研究未能获得较大推进,并不是这个议题不重要或不具有学术价值,其直接原因在于相关史料的缺失。安徽社科院钱念孙研究员收藏的章氏家族手稿《手泽珍藏》的发现,为这一研究带来了转机。章先生指出,“这批遗存函札文稿,大体上可以体现维藩公西北从戎,芜湖设厂,当涂采矿,乃至晚年策划在秦皇岛营建钢铁冶炼基地的雄图大略。”
《手泽珍藏》原稿封面(上)和内页(下)。
《手泽珍藏》彩印出版封面。
2019年10月底,章氏家族资料搜集工作也迎来重大突破。我兴奋地给先生打电话,报告新发现。我说,我找到的您的家族史、企业史的资料太多了,周锡瑞教授有《叶家》,我想我也可以写本好书《章家》了!先生在电话里说:“你还有你的其他安排,慢慢来,你的时间还长,我的时间不长了。”那一刻我怔住了,以至于后面怎么回复先生的,我都忘记了。
11月2日,在和徐炳三教授交换了意见后,我郑重给先生回信:
关于章氏家族的研究,我之前一直不敢下手,主要原因就是找到的资料不够多。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找到的资料,已经只有看不完的烦恼了。我完全可以写好一个家族史的故事了。我既可以把您家族的故事讲清楚,还可以保证它的学术性。无论如何,徐老师和我都会努力,让您尽早看到关于贝德士的研究著作,和我关于您家族史的研究著作。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向您请教,请您和黄老师保重身体!
2019年11月28日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的“企业家精神与工业文化遗产:章氏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会议上,我得以结识《手泽珍藏》原稿的收藏者钱念孙研究员。会议结束后,我又在马钢集团朱青山先生的带领下,实地考察了马钢的南山矿、姑山矿各矿场,与史料记载相核对。朱青山先生还带我深入到地下四百米的采矿作业面,现场感受采矿的过程。12月,我又在安徽省图书馆找到一册章维藩书信集,遂第一时间前往查阅。在皖图古籍部主任石梅老师和钱念孙先生的帮助下,我得以获得这份宝贵的资料。有如此丰富的史料,我有信心在章氏家族史和章氏企业史等方面,开展扎实且有深度的学术研究。章氏家族从章节文、章棣父子历仕林则徐幕府、左宗棠幕府以来,一直随着中国近代史的波澜而同进退。他们家族的历史,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章先生在《实斋笔记》中自述他从事张謇研究的缘由:“一是由于干臣公(维藩)的事迹,诱发我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我对张謇的理解;二是由于这样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我与自己某些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使我得以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先生所言实际上颇为谦抑。举个形象的例子,我们历史系师生常开玩笑说,你怎么敢来学历史,家里有矿吗?章先生家里还真有矿,而且不止一座,当然是民国时期的。
章先生的曾祖父章维藩(1859—1921),是安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他生于山西太原,少年随父章棣参与左宗棠西征,负责粮饷转运等,因军功保举,先后就任安徽牙厘局提调、无为州知州、怀宁县令、宣城县令等。1895年他辞官从商,在芜湖开办益新机器面粉厂。民国初年,他又筹资在安徽当涂县创办了宝兴铁矿公司。宝兴公司极盛时期,在当涂拥有十余座矿场。抗日战争期间,宝兴铁矿公司被日伪以低价强购,纳入伪华中矿业公司。1945年光复后,国民政府称其为敌产而拒不发还原所有人,并谋筹组国有铁矿公司。解放后,宝兴公司的原有产业成为马鞍山钢铁厂的一部分。2019年,安徽省国资委将其所持马钢集团股份的51%无偿转让给中国宝武钢铁集团,马钢集团成为宝武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这一股权变更,使得宝武集团的历史渊源可直接上溯至民国初年。先生这样的家世和出身,为他从事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商会的研究,提供了共情的先天条件。
章维藩绣像。
2020年以来,我陆续完成了章维藩书信集的点校和注释工作,并撰写了《章维藩书信所见人物交游》和《怀宁徐甫陈生平考述——兼论“E考据”在家族史研究中的应用》两篇文章,发给先生审阅。2020年9月我再回母校,与马敏教授商议《手泽珍藏》的识读和点校工作。在李寿昆教授及其弟子张萌的帮助下,前项工作得以完成。此时,我对先生家族史的认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章节文、章棣、章维藩到章兆奎、章学海直至章开沅先生,纵观章氏家族成员在近代中国历史大潮之中的选择,他们既不冒进,又绝不保守;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每次都能准确地踩在历史的节点上,既能顺势而为,又有所秉持,创造了章氏清芬堂近百年的辉煌。
9月中旬,先生抱病起身,为我筹备出版的资料集写序。序中先生称,“我从事家族史研究为时较早,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来,大半辈子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张謇家族研究。”早在给周锡瑞教授大作《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家族》的序中,先生就指出,当前仍然要倡导宗族史与家族史的研究,“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至今在观念与实体上仍有大量遗存,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
2021年4月2日下午,我随马敏教授、彭南生教授、徐炳三教授和刘莉老师,一同去楚园拜访先生和师母。我带着初步整理好的《荻溪章氏清芬堂函札史事录》,详细向先生汇报章维藩在创办益新面粉厂和宝兴铁矿公司中的各种经历,及章氏家族的各种故事。先生听着,不时补充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家族往事。先生气色很好,除了行动不便,依旧那么睿智、健谈,思路清晰、敏捷。
4月2日下午,张晓宇拜访章开沅先生(照片为徐炳三教授所摄)。
4月6日下午,我再随刘家峰教授和陈新林博士来楚园看望先生。陈新林博士请先生和师母保重身体。刘老师向先生汇报,山东大学的杨加深教授对《手泽珍藏》中维藩公的书法、诗词造诣,评价极高。这让先生也颇为意外。先生高兴之余,提笔为《荻溪章氏清芬堂函札史事录》题字:野叟知难,古今如此。意即像章维藩这样的“野叟”,不为公众熟知,查考起来颇有难度。我突然想起来,先生曾言,华君武先生的姐姐曾给章先生的长兄章开平写过一封信,叙述章家与华家之间的姻亲关系,我遂向先生讨要信件。先生略一沉思,转头看着我说,“这封信你那里有,你那时候都拍了的!”经先生这么一提醒,我方想起来,2018年一天我回武汉的时候,先生特地拿出那封信,让我拍照留存。只是我拍完之后未详细阅读,即束之高阁。那一刻我除了汗颜之外,倒也非常高兴,因为先生记忆力竟然如此之好。我们甚至觉得以先生的身体状况,活到一百岁也毫无问题。谁知那天竟是我们三人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4月6日刘家峰教授向章开沅先生汇报。
4月拜别先生后,我再前往合肥,查阅皖图所藏的另一本章维藩遗作,为《荻溪章氏清芬堂函札史事录》增补材料,收获颇丰。5月16日,我写完《章维藩函札所见人物交游考》初稿三万五千多字,5月20日在鄙校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报告。5月26日,我终于整理、点校完《荻溪章氏清芬堂函札史事录》的第六部分。点校期间,我还向先生的长女明明老师汇报进度。5月27日,我又在近代芜湖海关报告中找到数则关于益新面粉厂的记载。那天我还在想,下次再去见先生,我又能给老爷子多讲几个乃祖的好故事了。谁想次日,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4月6日章开沅先生题字:“野叟知难,古今如此”。
4月6日,章开沅先生与张晓宇等人在楚园合影。
5月28日上午,当我得知消息后,我脑中一片空白,浑浑噩噩,懵了很久。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是来的这么早,我们都没想到。下午,我坐在办公室帮学院起草唁电完毕,自己又写了一副挽联,痛悼先生。
别楚园五十二日,病未奉殁难视,更伤怀数载庸碌无为愧对教诲,小子一恸千里外;
居武昌六十三年,宏道德著文章,尤可敬毕生不媚时语独寻真知,士林如公有几人!
挽联难称对仗,但情真意切。小子不才,承蒙先生错爱!怪我做事太慢,拖延成性,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以至先生未能等到资料集出版即撒手人寰!我想起2015年6月我毕业临行前,想着不能常陪先生左右了,特来向先生辞行,向先生鞠了一躬,情绪有点激动。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说:“没事,来日方长,来日方长。”那时候,我们又有谁知道这来日究竟有多长呢?天道无知,不假吾师三百岁!痛哉!
5月29日早上,我抵达武汉。我想起以前在武汉念书时,先生每年冬天去广州过冬,春天再回来,我经常在这个到达口接先生和师母。我多么想先生能再拍一次我的肩膀。上午我赶回母校,来到追思堂吊唁先生,实在抑制不住,泪如雨下!中午,我来到先生办公室瞻仰。605室陈设一切如故。我又想起每次面见先生时,先生坐在桌子的那头跟我说话的情景。先生桌上有一放大镜,遇到字小的文书时,先生就会拿起放大镜来读一读。
章开沅先生的办公桌。
以前,当我坐在607乱翻书时,我常能听到先生从605出来时关门的声音。紧接着,就会看到老爷子戴着他的鸭舌帽,拎着他的小黑包,缓缓走过607的门口。
现在,那个身影不会再有了。
作者|张晓宇
编辑|李永博
校对|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