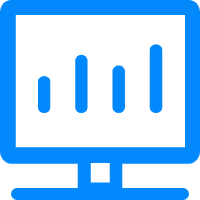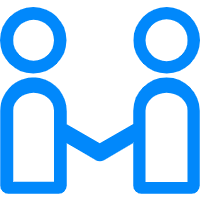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文并摄
何国荣在广西的老家。
何国荣的网贷记录。
何国荣的还款本。
在旺石村,多数村民都已盖起几层楼。
家里的墙壁已布满裂缝。
35岁的何国荣已有不少白发。
何国荣拿着失业证明。
何家有5个成年的儿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旺石村,这样有5根柱子的大家庭看起来是最抗台风的。
可母亲去世后留下的30多万元欠款快压垮了这个家庭。
钱是一定要还的,哪怕每月还500元。老大何国荣怕失了信用,从网贷平台上先借出钱来。这些新掏出来的洞,留给自己日后慢慢填平,他习惯了“拿下个月的工钱补上个月的窟窿”。他把分期还款的时间已排到了后年1月。
他有一个专门的记账本,一份3万元借款的归还情况,写了2页纸。
按计划,他和四弟何国辉去年年底就能还清所有的债务了。可意外一次次到来:先是何国荣生了场病,后来,他和四弟又都在疫情中失业,还账账本的更新停在了今年1月。
1
母亲吴志艺在广东省中山市干家政20年了。5年前的秋天,吴志艺突然感冒,吃药后一个多星期也不见好,很快不能自主呼吸。
中山市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叶红雨记得, 这是他从医20年见过的最大的肿瘤,直径差不多20公分,侵犯了胸膜、肺、心脏表面的心包和膈肌,几乎占据了胸腔。肺部有积液,放引流管,希望减轻对肺的压迫,尝试脱机,可反复几次都不行。
何家决定“搏一搏”。吴志艺在ICU里待了10多天。每天治疗费在6000元至1万元。
后来,吴志艺终于上了手术台。这场手术持续了十几个小时。这家人被医生告知手术挺成功,老大何国荣看见医生端着塞满被切除肿瘤的铁盘,一家人松了口气。
仅仅从ICU转到普通病房3天,吴志艺的呼吸再次变得困难。她的肺部又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只能回到ICU,再戴上呼吸机。
心胸外科护士长苏建薇记得,尽管何家不富裕,但一直为母亲找出路。吴志艺也才52岁,在拼尽全力救人的问题上,何家从没有过犹豫。
这家人也很淳朴,“对医护人员很信任”。苏建薇说,吴志艺的病情总有波动,但何国荣一直挺好沟通,遇到需要护理的时段,他也会主动询问,如何翻身、拍背。
她看到,这一家人穿得整洁干净,吃最简单的快餐,但会把丰盛些的饭食留给母亲。
她记得,科里也和他们沟通过钱的问题。对方表示,欠了钱可以慢慢还,但该怎么治还是要怎么治。
“费用的问题,其实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国荣坦言,一旦切断治疗,就等于直接给母亲判了死刑。
20多天后,他们被医院通知,母亲不治离世。
这次住院,母亲一共花了39万多元的医疗费。这笔费用还等着他们去结。老大何国荣手里只有3万元的存款,一家人又一起凑了3万多元。减去中山市的大病补助等,他们要交的费用还有30万元左右。
母亲只有老家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她12月初去世,买的保险只管当年,生效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了。由于涉及异地医保报销,按照广西的要求,家属要在月底前开出就医缴费的发票前往当地,才能报销花费的40%。
留给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的时间不多了。
少言寡语的何国荣那一个月里,“筹钱、筹钱、再筹钱,直到借无可借”。最终,他借来了14万多元,“找遍了所有关系”。
中山市人民医院的救助体系尚算完备,不过,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多的救助项目能分担这个家庭的压力。医疗费用管理科科长陈满章介绍,医院也是在这两年,才设立慈爱基金等救助项目。
他也记得,之前医保异地结算还没联网。因此,这个家庭尚不能享受在异地不用打印病历、发票、清单、诊断书,就可在医院缴纳全额费用的同时,直接减免医保报销费用的待遇。
筹钱的压力,都压在了何家人身上。何国荣结了医疗费,换乘高铁,再坐两趟公交车,单程的花费就要180元,急急忙忙赶回老家。15万多元的发票,最终分3次报完,合计报销7万多元。
拿到报销的钱后,何国荣想也没想,“肯定是要给医院的”。他每拿到一笔款项,就会再跑医院一次。他给医院交过三回钱,2万元、3万元、2万元。
最后的一笔报销款,只有1万多元。一位借过钱的亲戚遇到困难,何国荣只好先把这笔费用全还给了对方。“我们借的时候,他们也不富裕,但要来账号没几秒就打来钱了,那我们也得讲信用。”
护士长苏建薇给何国荣打过几回电话。她记得,这个男人从未回避过欠费的问题,打去的电话响几声后一定会被接听,他也会在电话里,诚恳地讲自己的筹款进度。
“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他就会过来交一点。”苏建薇回忆,起初那几年,医院会定期起诉恶意欠费的病人,可涉及何国荣的家庭,这个科室明确地否决了。后来,医院也很少给他打去电话。
几次还款时,她亲眼见证了这个35岁男人的变化:第一次来医院,他还是满头黑发,后来,白头发从左鬓角到右鬓角绕头后一圈,他一下子“很沧桑”了。
2
母亲去世不到一年,何国荣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已回老家照顾祖父母的父亲,胸口总是难受,“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很快他就收获了又一个沉重的噩耗:父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已经没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案了。一家人商量后决定,让父亲回家养着,“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些”。在家没几天,父亲就疼痛难忍,住进了县城医院,一个星期后离世。
这3次就诊,一共花了两万多元。这笔钱,又是借来的。
在这个对丧事颇为讲究的村子里,何家安葬父母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叫上村里的几个长辈,出门简单地吃了顿饭。
就连举行仪式之前,遗体暂存一晚的花费,他们也要咬咬牙——他们选择了带冷气的屋子,比普通的贵2000元。
父母就诊的大部分资料已经丢掉了。在仅剩的两张死亡通知单上,底部签署的名字都是何国荣。
他是家里的老大,努力维持着这个家的最后一点儿体面。他的朋友不多,父母去世的事,他没对外说。怕对方知道他们家里有困难,担心借钱慢慢疏远。
村里人也会当面问他,家里是不是还欠着款,他回答,“就快还清了”。
他告诉记者,“毕竟在农村,背着这么多欠款,是要被人瞧不起的。”
何家一共5个男孩,“5个劳动力确实挺多。如果都有本事,条件应该也算很好的。”何国荣声音低沉。
母亲生病时,何家最小的弟弟还没工作,过了几个月,正式工作后也还过几次款。妹妹那时候辞了工,专门回家看孩子,想尽办法凑出了2万元。四弟只有几千元的存款,后来又从丈母娘家借了一笔。
这些兄弟中,还钱最多的,还要数老大何国荣。
何家最会读书的孩子是老二。
何国荣记得,二弟从小的奖状,贴满了老房子的墙壁,盖了新房,又从屋里贴到客厅。他们帮忙收拾过这些奖状,“差不多要用纸箱来装”。
二弟的成绩一直很好,家人都觉得,以后准能有大出息。这个沉默寡言、总是埋头书本的男孩,考上了南宁的大学,因为英语突出,还报了外交专业。
他的学费父母出过,兄弟们出过,也向政府借过款。后来,他向家里要的钱越来越多,每个月的生活费从600元、800元,最后涨到了1500元,还从祖母那里“借”走了1万元。直到他带了一起“搞大项目”的同学回家游说家人,他们才确定,二弟陷入了传销。
后来家人拼凑出的事实是,差不多只上了一年大学,二弟就被人“带偏了道”,最后连大学毕业证也没拿到。
一家人费尽心思劝过他,不过没什么效果。这些年,二弟生活在深圳,母亲生病时也来探望过,可他拿不出钱,反而要走了4000元。
何国荣听人说,这些年,二弟进过工厂,也经常失业;几乎和所有朋友都借过钱,到后来连1元钱都借不到;因为没钱,他穿着破烂的衣服,从县城走回村里,徒步20多公里。
何国荣身边也有人被拉进过传销,不过,发现了猫腻就立马甩手不干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最会读书的二弟会陷得最彻底。
提到老二,一直在深圳打工的二叔也忍不住叹气。“他大学读书借的钱,到现在还欠着国家2000多元”。
二弟的眼睛高度近视,不戴眼镜看东西得靠手摸,他在打工的市场上受歧视。丢了读书的优势后,人内向,有些自卑,没技术,干不了体力活儿,“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3
那根原本最有希望的柱子倒了,之后是又一根。
在何家,老三的成绩仅次于老二。他读到了高中,性格开朗,人也勤快,会主动帮祖父理发。他后来也去深圳打工,做纺织类的工种。一次做工时,他被机器不小心切到手,自此落下了手指残疾。再遇上招工,他总卡在亮出双手的那一刻。
他剪不起20元一次的头发,就由着头发越来越长。人一回比一回瘦,穿着破烂,“看上去像是流浪汉”。
“他能怎么办?只能躲进网吧待着,看着看着也就玩上了。”二叔说。
在网吧,老三一窝就是半个月,吃泡面充饥,整个人“瘦成排骨”。偶尔找到短工,就干几个月,拿到一笔钱,再钻进网游的世界。他没存下过钱,轮到过年给小孩的压岁钱时,能拿出来的只有1元。
何国荣给三弟介绍过看厂的工作。没人在的时候,三弟把卷帘门拉下来,又跑去网吧打游戏。最严重的一次,老板回来找不见人,被关在门外。
后来,何国荣也不敢帮他找活了。
母亲躺在ICU时,何国荣曾叫三弟从深圳来中山探望。约好的时间,三弟不见人影。母亲整个住院期间,他仅来过一次。
母亲生病后,三弟找到份工作,分两次共给过4000元。后来他说自己又失业了,拿回了1000元。
这两个曾被家人引以为傲的儿子,如今成了家中“最失败的人”——没正儿八经的工作,也没一丁点儿积蓄,常年打零工将就生活。至于找对象的事,“那是早就不考虑了。”二叔说。
他们很少和家人联系,没人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二叔也无奈,“家里这样,他们心里苦,但身边看不起他们的人很多,到最后他们也就不说了,憋在心里。”
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要打工,几年里,他们分散在三个地方,中山、深圳、老家县城。他们忙于做工,休息的时间很短,即使在同个城市,一年也见不了几面。
母亲在时,家里的一切由她张罗,“挺热闹的”。在深圳打工的三弟也会来中山,几兄弟短暂聚在四弟的出租屋里,一起吃饭,或住上几天。
父母接连去世后,背着一笔沉重的欠款,他们在各自打工的地方漂着。怕被人看不起,他们想回家又不敢回家。现在,这家人相聚的时间只有春节,人也始终不齐。
维系家庭的主角变成了老大何国荣。每个月,他会主动给弟弟妹妹打去几个电话。对沉迷网游的三弟,他也总是劝诫,“做人要绝对靠谱,别晃悠悠地过”。结果电话号码被三弟拉黑。
“只有他找你,你找他基本都找不到。”几乎每讲到三弟,何国荣都要叹气。
他感觉,家里这些年,“就像是本不牢固的房子,一处接着一处裂开缝”,还没等他填补上,又裂开了更大的部分。“这个事来了,那个事又来了。”因此,他格外害怕意外。
4
可意外总不错过这个家庭。
双亲接连去世后,何国荣心情不好,睡不着,吃不下饭,1米74的身高110多斤,皮肤发黑,总没精神,走路晃晃悠悠的。跑了趟医院,他被确诊为严重的肝病。
“真和天塌下来一样。”他说,那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走在外面,天是晴的,可自己感觉是就是黑的。”
他只能再次请假,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每月还要再去检查、开药,持续3年多。因为总是请假,他差点儿丢了工作。
恢复上班后,他的身体也经常撑不住。他做巴士司机,只能在跑长途的过程中到服务区休息40分钟左右。碰上乘客提意见,他就解释,天气实在太热了。
他做过最叛逆的事也在那段时间。因为压力大,他开过“斗气车”。他本来习惯礼让,但路上总有小车挤他,他就回挤过去,猛按上几声喇叭。
“每次都很后悔。”他说。从前自己不会这样。这个极少在家人面前表现出压力的男人,把它视作唯一的发泄渠道。
他的检查单从31岁摞到35岁,4年治病用掉了三四万元。后来,他的指标才慢慢恢复了正常。
不过,生病的事,他没好意思和亲戚朋友说。那些日子里,他仍在每个月照常还钱。
3年前,第二个女儿意外降临了。“前前后后又用掉了三四万元。”
生完大女儿后,为了带孩子,妻子有三四年没去上班。如今,这样的日子还得来一遍。
更多的责任压在他和四弟身上了。两人盘算着一起还钱。
“四弟每月赚3000元,我每月赚5000元。”他盘算着,“不出意外的话,2019年年底之前,差不多能把欠医院的8万元还清了”。
意外再一次不打招呼地降临。何国荣原本有着何家赚钱最多的工作。他很满意这份在中山市最大的大巴公司当司机的工作。
他开过货车、公交车,工作差不多都在3000元,不够开销。后来,经人介绍,他跑去开大巴,跑珠三角线,一干就是7年。
差不多每天,他要跑两个来回,一趟8小时。忙起来,连着上班20多天。
父母去世的几年里,中山也变了很多。高铁连通了珠三角,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路,兴起的网约车带走了大巴车的大部分生意。大巴线路关闭了一些。他的巴士从以前50个左右的座位塞满了乘客,还有人挤着上,到现在有时空车出发。
这场疫情也加速了大巴车的衰落。他的月工资变成了1720元,减去社保跟公积金,只剩1000元出头了。
何国荣习惯拍下车站的值班表。他看到原本一面墙那么大密密麻麻的表格,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空白,车辆数量减下来了。每条线两三趟车变成一趟,基本上“每条线都亏钱”。
5月底,他正式接到裁员通知。劳动合同是一批一批解除的。“今天找十几个人,明天又找十几个人”,不解除也可以,只给最低工资。
犹豫了两天,他决定“解除算了”,“在外面找找事做,总会有三四千吧”。
闲在家里的日子,他外出干过几回临时活儿。他开广告车,跟着绑了喇叭的小车,在中山市和周边乡镇一圈圈地绕,一天要跑差不多12小时。广告推销电瓶车——在人们习惯用电瓶车代步的中山,一项新规定出台了,电瓶车要换成国家统一标准的,违标的要被淘汰。
不过,他自己家的电瓶车还没换。“哪儿有钱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家人眼里,何国荣是典型的“好男人”,不打牌、不喝酒,不抽烟。为了还债,他节省再节省。他最奢侈的花销不过是在一年在网上买两件100元以内的衣服。
他的小女儿只有两岁,“肉嘟嘟的”。女儿喜欢的玩具,超过10元钱,他基本都不考虑,“出去10趟才买一回”。有时候,女儿急得哭了,他只能安抚她,下次再买。他努力做一个诚信的父亲,“个别时候一定要实现她的愿望。”
他嫌住的月租金700元的屋子太贵,在此之前,他租房子的价格一直在300元左右,有的在一楼,蚊子多,潮湿到发霉,下雨时还被水淹过;有的对门养狗,半夜总叫。
朋友间的聚餐,如果定在了“稍微高档一点儿的酒店”,他基本都不去。他自己做饭,一天花16元左右。 36G内存的手机,他用了三四年,到后来“卡得要死”。
何国荣几乎没出门旅行过,他就在车上看风景:连州空气好,深圳发展快。他离港澳近,但没去转过。他只带孩子去过一回杭州。
疫情之下,同在中山打工的四弟日子也不太好过。他做制衣,后来工厂不开,他没活做,索性回了老家。前几天,他才在镇上找了份工作,工资下降了1000多元。
四弟夫妇有两个孩子。今年9月要上小学。回老家的一个原因是,这里的幼儿园只要2000元一个学期,是中山的三分之一。
夫妻俩在8年前结了婚。“一嫁过来就是还债。”四弟媳说。多数时间里,这个家没人到访。两个孩子就在老房子周围自顾自地玩。四弟忙着做工,没时间带着儿女在县城转转。
最能赚钱的两个兄弟还在硬撑,他们有不能倒下的理由:家里还有好几个人等着吃饭,等着读书。
5
何国荣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连账也记得“一塌糊涂”。但他的账本上,每一笔欠账记录都很清楚。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何家的还款模式是,老大老四各还500元。
一位堂叔借给何国荣1万元。之后,堂叔的小孩早产,进了保温箱,眼睛也有问题,都要用钱治。何国荣直接转给他5000元。这笔钱还是网贷借来的,还上用了两个月。
每个月,他最盼望的日子就是发工资的那天。到账的工资基本都用来填坑了。“这几年都是这样过的。”
7月末,何国荣今年第一次回了老家。他已经失业两个月,闲下来的这些天,待在老房子里,他总觉得不习惯。
他现在的收入,一部分来源于失业金,剩下的就是运营网上的店铺。他卖太阳能灯,赚十几元的差价,这是他近期最投入的事情。
只要手机一响,他就会迅速地拿起来。他花时间研究店铺推广的攻略,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没雄厚的本金,打不出量的优势,买不起好的推荐位置。为了保持“信用值”,他必须在3分钟内回复顾客的消息。
太阳能灯的价格不算低,下单的人不多。何国荣靠这个赚来的钱,仅能维持生活。
他也不时在网上翻招工的消息。不过,他仅有的技术就是开车。他仔细考虑过,如今这个行业司机多、线路少,自己“之后肯定不会做了”。
他没开出租车的打算,“现在赚不了多少钱”,也交不起门槛费。他同样买不起自己的车。
何国荣打听过,开集装箱挂车,一个月工资能有快1万元,可他还需要另外考证。他问过驾校,整个学下来要1万元,全程七八个月,不保证拿证,他放弃了,“等不起”。
身边一起打工的人里,也有人有“吃香的真技术”。拿制衣来说,有人专门跑领子,工资高出一倍,但四弟和弟媳只是干些压线打蜡的杂活儿,就是“跑边的”。“技术不是谁都能学,师傅基本只教自己的亲戚。”
他也听过有人在医院欠了一笔钱,为了逃缴费连夜逃走,就连出院手续也没办。不过,在还钱的事儿上,他从来没犹豫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借钱对象是身边的亲戚,生活都不富裕,最大的一笔借款是5万元,最快的10分钟到账。
这个失业的男人始终觉得,“现在的社会,诚信‘最重要’,那是能代表整个人的东西。”
他知道,被拖着欠款的滋味儿不好受。也有人问他借过钱,直到说好的还款期过了五六个月,那笔钱才到位,“感觉很不好”。
何国荣干脆把“绝对靠谱”写进自己的社交账号昵称。网贷平台上,他也用这个注册。
事实上,他第一次离开村子前往中山,下了汽车就被骗了。那时候,他不到15岁,刚从初中辍学,汽车到站的地点,离母亲工作的地方还有差不多20公里。他握着一张写了母亲位置的纸,上了一辆揽客的摩托车。
对方要30元,结果带他在汽车站周围兜了一圈,又把他扔在了陌生的工业区。他四处找路,对方就跟着他不说话,无奈之下,他又多给了那人10元,请他拉自己回去。
不知不觉,他来中山20年了。他觉得自己努力过,不过,“可能是因为运气不太好,实力不比别人强,也可能用的方法不对”,反正就是没赚到什么钱。
他还想着再拼一把。但他35岁了,体力下降,容易疲惫。他把微信头像换成一个白底写着黑色大字的“近我者富”,自嘲也是自勉。
他理想的生活已变得很简单:找份工资高点的工作,尽量把钱还上,能和家人一起生活在中山,堂堂正正、轻轻松松的。
原来“发展慢悠悠的老家”,这些年也加速向前了。老家村子热闹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停满了车,赶上两辆车子错车,得倒腾半天。只有他家的门口是空荡荡的。
他的祖父母也已80多岁。祖母患有支气管炎,去年住了两次院,每次都是半个多月;祖父的腿脚常年没力气,从屋里挪到客厅也得人扶,因为老年痴呆,每天不太清醒的时段眼睛会直直地瞪着天花板。
两个老人都有慢性病,有些药吃了20年,每人每月有120元的“老人金”补贴,但进口药最便宜的一盒也要80元。
如果能攒更多的钱,老大何国荣还想把老房子翻修一遍。他下单了自家店里的一个太阳能灯装到老家的屋檐上,这是这座房子里最近唯一添置的新用品。
如今,这座房子落伍了,每堵白墙上,都出现了黑色的缝隙,有的裂缝裂出对角线,赶上雨季,天花板漏雨,在屋里要拿盆子接水。
那几年比较好的光景里,一家人常年在外打工。春节是最热闹的时候,因为手机像素不够高,这个家没有一张完整的全家福。
再往前几年,是这家人最幸福的时刻。父母打工回来,带回了全村第一个煤气灶,在村里第一批盖了新房子,何家的孩子都“感觉好日子伸伸手就可以够到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