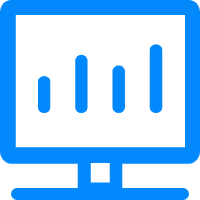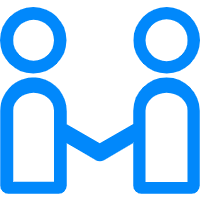王莫之
周璇这个名字并非本名,而是她从艺之后别人帮她取的艺名。当事人曾经撰文提过一句:“十三岁的那年,由章文(作者按:原名‘章锦文’)女士的介绍,我就加入了黎锦晖先生主办的明月歌舞社,周璇的名字就是黎先生为我起的。(我的小名是‘小红’)”(《万象》1941年第一卷第二期)很可惜,没有展开来谈。
周璇为《春色》杂志拍摄的封面,1936年
周璇为《大同新歌选》拍摄的封面,1940年
关于周璇艺名之由来,有两种说法。最主流的版本认为它出自爱国歌曲《民族之光》的歌词“周旋于沙场之上”。基本上,为周璇立传著文的作者们都是这种说法的信徒。唯独吴剑女士剑走偏锋,她从1934年6月14日的《大晚报》翻到一篇文章,内中写道:“她原名小红,自己嫌这芳名儿太平凡,教我改做今名。女士性情温柔,心思灵敏,而对人接物偏偏又很圆通周到,猛然想起‘璇’字的字义是圆形的美玉,于是取定了这个隽雅的名字……”吴剑女士笃信这段文字,认为“歌词说”以及相关异说在“54年前印在《大晚报》上的黎锦晖的文章面前都是不能成立的”(《何日君再来——流行歌曲沧桑史话[1927-1949]》,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
我估摸吴女士的信心源于这段文字的作者叫黎锦晖。黎先生是时代曲的鼻祖,学界公认中国的流行音乐史要从他1927年发表的歌曲《毛毛雨》算起;而且,周璇从艺的第一步,是加入黎先生统帅的明月歌舞社。可问题是,“歌词说”的旗手也是黎锦晖。1965年,黎先生在王人艺、王浮的协助下,完成了数万字的回忆录《我与明月社》。这篇长文生不逢时,要到1983年才公开发表,里面有一段写到周璇:“这时在沪还公开招考一次,聂紫艺(聂耳)、李果等五人被录取。不久,章锦文又介绍一个十二岁的孤女周小红。我觉得小红这名字不雅,那时正在‘一·二八’后,抗战期间,我写《民族之光》一剧的歌词中有‘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一句,于是为小红改名‘周旋’。她正式当了电影演员又改为‘周璇’。”(《文化史料(丛刊)》第四辑,1983年1月版)
黎锦晖,1930年留影
不少人轻信了这段回忆,随后依据周璇从影的时间,判断周璇这个艺名诞生于1935年。其实只要登陆《申报》的数据库,检索“周璇”二字,就会发现1935年的推理是错的。《申报》上最早的周璇记载是一条演出预告,刊登在1933年5月11日的12版上,同样的预告在同一天的《时事新报》上也有露出,涉及周璇的有两个节目:《特别快车》《泡泡舞》。
人在回忆过往的时候,很难做到滴水不漏。黎锦晖在1965年发出了“歌词说”的强音,在1934年写下了“圆形美玉说”的底本,或许在吴剑女士眼中,时间更早的版本更接近周璇改名的真相。可是我仍旧倾向于为“歌词说”投上一票,因为除了黎锦晖,周璇生前的其他同事、朋友在他们晚年接受采访时对周璇改艺名的回忆是高度一致的。
1979年12月12日,黎锦光在中唱小红楼接受梁茂春的专访,他说:“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黎锦晖编演爱国节目,其中有一首爱国歌曲叫《民族之光》,让周小红上台演唱。歌的最后有一句‘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她唱得特别动人。根据这句歌词,黎锦晖就给她改了名字叫‘周旋’,后来又在‘旋’字旁加了斜玉,成了‘周璇’。”(《天津音乐学报》2013年第1期)王人艺给出的解释与之大同小异(详见《音乐艺术》1985年第3期)。黎、王两位先生都是明月社的骨干,是周璇的前辈。“明月”之外的文艺界人士,导演郑君里早在1957年周璇去世后即写下纪念文章《一个优秀电影女演员的一生(周璇的生平和她的表演)》,内文谈到周璇改名也是高举“歌词说”的大旗(《中国电影》1957年第10期)。
那么多亲历者的“供词”如果无法指向真相,那么,他们便有“串供”的嫌疑,换言之,他们都忘了周璇为何改名,于是人云亦云。同样的,假设“歌词说”真实可靠,那么黎锦晖为何1934年会在报纸上虚构一个“圆形美玉说”呢?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应该了解黎锦晖写那篇文章的背景。
1934年5月,《大晚报》发起了“三大播音歌星竞选”的活动,评选结果登在同年6月14日的报纸上,白虹、周璇、汪曼杰当选。报社的编辑为这三位歌星配了照片以及独立的介绍文章,类似于今日的颁奖词。为冠军白虹撰文的是民国画家丁悚,而介绍周璇的那篇则由黎锦晖操刀。在如此喜庆的气氛下,假设黎锦晖告诉读者,周璇的艺名来自一句反帝国主义反殖民统治的歌词,是否会对刚刚起飞的周璇女士产生不良影响?关于这个话题,我向几位民国文史的研究者求教,祝淳翔老师给出了一种解释:“在1937年国民政府正式表态抗日之前,抗日有时是一种禁忌话题。”
周璇(后排右一)、白虹(右三)1933年参演《泡泡舞》,该舞由胡笳(前排)主演
周璇(左一)、白虹(左三)1933年参演滑稽歌舞《特別快车》
我在黎锦晖的自传里为这种解释找到了一个证据:“《民族之光》应准上演。其中我作的歌词曾录有唱片,以后也遭到日本通知租界禁唱。”王人美的自传里也有相似的证据:“说到这里,我想起周璇的改名。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初春,歌舞班又增加一名十二岁的孤女周小红。她来之前,上海刚刚发生过‘一·二八’抗战。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中,黎先生为歌舞剧《民族之光》写了主题歌。以后歌舞剧虽被禁止上演,但主题歌《民族之光》却多次演唱……”(《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时空环境的改变会导致彼之砒霜今之甘露的局面。到了1965年,黎锦晖为自己立传,写到周璇时,他非但可以公开抗日,而且需要公开抗日,毕竟在新社会,他一直活在“黄色作曲家”的阴影里。他何尝不希望公众能够看到他在民国的光明面,能够公允公正地对他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这种心理活动并没有因为黎锦晖的去世、平反而消失,哪怕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王人美仍然要在她的自传里为恩师疾呼:“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黎锦晖的代表作是《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并由此断定他是三十年代创作黄色歌曲的代表人物……黎锦晖先生写过许多进步的、爱国的歌曲。”
以上所述,并非旨在驳倒吴剑女士的观点,而是研判“歌词说”的可靠程度。显然,推演“歌词说”的成立,第一步是得证明歌舞剧《民族之光》以及同名歌曲的存在。我在1933年的《申报》上翻到了三则广告。登载于2月18日第29版的广告宣传了明月社于2月19日开启的上海公演,演出场地是北京大戏院,广告底下注明:特别排演《野玫瑰》《民族之光》《娘子军》。2月23日第8版、2月28日第12版的广告则是RCA胜利公司投的,预告即将上市的新唱片,歌曲《民族之光》赫然在列,演唱者是王人美、白丽珠(白虹)、严华,这三位都是明月社当年的台柱;在这两则唱片广告里还登了一句宣传语——“王人美女士等曾表演于北京大戏院看过诸君应即购其唱片时时开奏取乐”。
明月社歌舞剧《民族之光》公演广告,《申报》1933年2月18日29版
歌曲《民族之光》的唱片广告,《申报》1933年2月28日12版
假设歌舞剧《民族之光》是1933年2月19日在北京大戏院首演的,那么黎锦晖为周璇改名字应该发生在2月19日或那日之后,5月11日之前(上文已表,目前可查考的最早的周璇记载刊登于1933年5月11日的《申报》与《时事新报》)。这个区间还可以进一步缩小。参考黎锦晖的自传,明月社在1933年初春有过一次解散,之后,周璇改投严华主导的新月歌剧社。至于明月社那次解散的具体时间,《聂耳日记》给出了答案。3月1日,聂耳去明月社串门,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明月’便是这样瓦解了!人美大概是没问题的和‘联华’定了约!我们谈起过去最快乐的时期不禁感伤几至流泪。她说‘明月’的尾声是227一II,这是一个没有静止的尾声。”
明月社解散后,周璇加入严华主导的新月社,几个月后改投新华社,此图为周璇1934年留影
文中的“人美”指王人美,她当时已是成名的影星,与联华影业公司签了合同,所以聂耳说她大概没问题。这段日记我请杨宁老师过目,他说“227”应该是简谱里的re resi,“一II”是长音和表示结束的小节线,整体来看,是一个没有终止感、悬停的结尾。可我也不敢排除王人美语带双关的可能性,也许明月社解散的日子是2月27日。
3月1日也罢,2月27日也罢,这都不影响将周璇改名字的具体时间锁定在1933年的2月下旬。
说起《聂耳日记》,有一件事情让我相当费解,它牵扯到周璇加入明月社的时间。这个时间点历来没有定论,只是因为黎锦晖在自传里写道:“这时在沪还公开招考一次,聂紫艺(聂耳)、李果等五人被录取。不久,章锦文又介绍一个十二岁的孤女周小红。”许多人便断言周璇加入明月社是在1931年,因为聂耳考取“明月”(当时叫“联华歌舞班”)是1931年4月——借助《聂耳日记》,甚至可以精确到4月8日。假定周璇真是聂耳进社后不久来的,那么周璇在《聂耳日记》为什么迟至1933年1月31日才第一次露脸呢?(那日,涉及周璇的内容如下:“想起红小姐的事,也就可笑,他们竟以为是真的,其实他们已给我开了玩笑。他们以为所以有如此成绩者,全在昨晚小白的寿餐。”)
章锦文女士,改变周璇命运的大恩人,明月社的琴师,人称“胖姐姐”,1934年改名“章文”
明月社那么多的鸡毛蒜皮都进了聂耳的日记,阿狗阿猫都不放过,即便周璇当时只是一个跑龙套的,我仍旧无法理解她在《聂耳日记》中的长期失踪。因此我猜想,周璇加入明月社时,聂耳已经退社了。聂耳离开明月社源于著名的“黑天使”事件,因为文艺路线与黎锦晖、黎锦光发生了激烈冲突,他是被动退社的;参考他的日记,时间点是1932年8月6日。次日,他离开了上海,乘船北上。
我推断周璇是在聂耳退社之后才加入“明月”的,有一个重要依据,那是周璇的第一任丈夫严华1986年3月写的文章《难以淡忘的回忆》。那篇文章是严华应周璇次子周伟的委约,专门为《我的妈妈周璇》一书写的。文中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周璇时的情景:“那是在‘一·二八’淞沪战争后,一九三二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里。我吃过晚饭,正在明月歌剧社排练大厅外的天井里和音乐队员张其琴老先生闲聊,恰逢钢琴手人称胖姐姐的章锦文领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瘦小的姑娘走进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严华签名照片,1935年《夜城》杂志
周璇严华婚后在茂龄新邨住过一段时间,这组照片由翁飞鹏拍摄于1940年
1932年的深秋,彼时聂耳已在北平,这恰好解释了周璇为何不曾在“明月”时期的聂耳日记中出现。
1932年11月8日,聂耳回沪,隔天的日记写道:“在卜万苍宅午饭后往‘明月’取箱子,遇七嫂子。四处参观一周,一切如故,可是凄凉多矣!七嫂子好像比以前活泼些,对我很好感。”
所谓七嫂子,指七爷黎锦光当时的太太(白虹是黎的第二任妻子,第三任是祁芬)。聂耳对一位住在“明月”的非“明月”成员都要记上几笔,何况周璇?难道聂耳在明月社供职的那五百多天(1931年4月-1932年8月),周璇就无法给他留下任何印象吗?
聂耳重返上海之后,偶尔回“明月”串门,周璇在这一时期的聂耳日记里有两次亮相,也是她在整本《聂耳日记》里仅有的两次登场,第一次的称谓是“红女士”,第二次叫“小红”。
从1932年深秋加入,到1933年初春离开,周璇在明月社其实只待了半年。这半年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她从孤苦少女周小红变为歌舞新星周璇;这半年是如此关键,这也是我深感有必要费心耗时地把一些事件、时间梳理清楚的原因。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