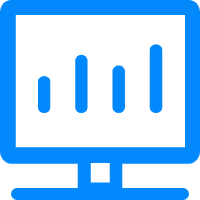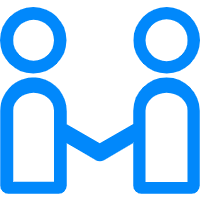被困职工宿舍21天后,上海感智盲人按摩公司的推拿师傅张相聪说,他“听”手机已顾不上白天或黑夜。宿舍和按摩店两点一线的生活被打破,现在,他困缩在更小的宿舍床上。
健全人或许觉得隔离难以忍受,但视障者早已习惯出行的种种限制。真正的难是嵌于疫情时代的种种琐碎小事:辨认口罩的正反和上下,去往全然陌生的核酸检测点,在黑暗中扫健康码,通过健康云的人脸识别,在买菜软件上抢菜。
3月15日,按摩店停业,3月28日,浦东实施封控管理,4月1日,解封仍未到来。包括张相聪在内的32名盲人技师被困在不足20平米的3间职工宿舍。宿舍没有厨房,也没有冰箱,封控前购买的面包、泡面正一天天减少。4月5日后,他们只在清晨喝一碗白粥。
4月7日,同样是视障者的按摩店管理人李建明开始求助。他打市民热线12345,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居委会电话,城管电话,残联电话。有一位女士联系了李建明,她收集了宿舍的地址,电话,他们的需求。“我把信息填到互助平台,应该会有人看到联系你的。”他记得她这么说。4月12日,残联送来第一批物资。4月15日,李建明接了“将近有100个电话”,收了十多个快递。打开后,大米、腊肉、鸡蛋,各种青菜铺满了宿舍的地板。
盲人们看不见世界,对物资的来源同样一无所知。发生在4月15日3个半小时内的接力救助,隐匿在盲人漆黑的瞳孔。电话那头的好心人们有不同的声音,他们不肯告诉李建明他们的姓名。
2022年4月1日凌晨3时至4月5日凌晨3时,按照上海市关于做好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的统一部署,浦西地区的核酸筛查全面展开。上海市民进行核酸检测登记。新京报记者 王飞 俞金旻 摄
疫情时代的琐碎小事
走去核酸检测点的路程并不遥远,只不过是对健视人来说。3月28日,视障者李建明和按摩店的同事们离开位于茂兴路71号的职工宿舍,准备前往塘桥新路与浦东南路交叉口天桥附近的核酸检测点。32根盲杖在地面敲敲打打,遵守着从前在这条路上行走的规律,他们排成一列走得缓慢,不熟悉路的人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
从宿舍楼一层下5级台阶,就来到了茂兴路路面。沿路店面一一关闭,从前出行时依仗的气味和声音,无论是热汤馄饨的香气,还是超市播放的促销广告也都随之消散。唯一不变的是斑驳断裂的盲道和香樟树荫下的凉意。沿着道路向北走,盲杖继续敲打,带着手握它的人绕开路旁的自行车,花坛,垃圾桶和电线杆。行进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右转至塘桥新路。
辨认出酒店大堂特有的香氛味道时,李建明知道自己正经过如家酒店,路程走完了一大半。塘桥新路路面宽阔,障碍不多,盲人们加快了步伐。导航语音提示路过麦当劳,也提示着李建明是时候上天桥了。走天桥靠的是一种“感觉”,李建明无法准确描述,那种感觉是存在于黑暗中的立体地图,详细记录着天桥台阶的宽度,高度,延伸的方向。左手拿着盲杖,右手扶上冰凉的栏杆,他们顺着栏杆右转,向前,再右转,下天桥。
普通人只需5分钟左右的路程,他们走了超过10分钟。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盲人们收起盲杖,走进做核酸检测的队伍。做完后,又开始了另一个10分钟的返程。3月28日之后,李建明隐隐松了口气,他和同事们只需要每天下楼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楼下也有了集中核酸检测点,他们再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
疫情时代,接受核酸检测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视障人士李建明41岁,与人交谈时总是微微侧着头,用耳朵对准声音的来源。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位视障者相同,李建明沉默,不善交际。他说话时语速极慢,开口前习惯用思量掩盖轻微的口吃。两岁时因医疗事故全盲后,李建明遇到过太多事,心酸的,委屈的,痛苦的,艰苦卓绝的。相比之下,出行做核酸的“艰难”似乎不值一提。
同样不值一提的是嵌于疫情时代的种种琐碎小事。戴口罩时要摸一遍口罩,先摸到口罩的金属条,确定上下,再摸口罩两边的折痕,折痕方向朝下的是外面,朝上的是里面。扫健康码时要先摸到贴码的地方,确定手机和健康码的距离,再像划十字般一横一竖地平移手机,这样才能更快扫到码。
最难的是健康云的人脸识别。人脸识别有时间限制,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完成人脸表情动态识别。多数时候,李建明需要请身边的人帮忙,没有人时,他会摸摸脸,再摸摸手机,确定位置后才能保证人脸在框中。有时需要眨眼和点头,他就只能笨拙地一直眨眼,一直点头。
去商店买菜也是难题。茂兴路71号附近有一家小型超市和一家大型超市,生活算是便利。因为宿舍没有厨房,按摩店又包两餐,李建明和其他盲人很少去超市。超市是一种未知的浩瀚,蔬菜和水果隐藏于黑暗中,李建明只能靠嗅觉和声音辨认它们的种类。芹菜,大葱,蒜苗有强悍的气味,那些没有味道的蔬菜,他只能侧耳细听,“这个莴笋不错啊,多少钱?”他收集其他顾客的声音,跟在他们身后,拿起相同的蔬菜。
2022年4月19日,工作人员在上海一处物资仓库卸货。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两片黑暗
对李建明来说,上海是两片不同形状的黑暗。一片黑暗位于浦东南路地下一层的按摩店,另一片黑暗位于茂兴路71号3层的集体宿舍。
3月28日浦东实施封控管理后,李建明和其他31位盲人技师被困于集体宿舍。宿舍规整,狭小,不足20平方米的空间满满当当塞了6张高低床。床下的脸盆、暖壶、拖鞋和挂在床栏上的衣物密密匝匝沿床冒出来,本就狭窄的过道显得更逼仄了。困于这片黑暗中,李建明唯一的活动是去洗漱或者上厕所,他下床,出门,沿着墙壁缓慢地挪动脚步,走向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
囿于宿舍和按摩店两点一线的规律生活被打破。从前每天早晨8点,李建明会敲打着盲杖离开宿舍,穿过早餐店外的馒头香气,穿过小饭馆里阿姨和阿叔的语笑喧阗,穿过垃圾箱、共享单车、电线杆等他口中“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行走10分钟后,从地面下7级台阶,他到达按摩店,置身于相识11年的黑暗。
“客人说就像迷宫”,李建明说,“吧台左边是客用休息室,往右是按摩的房间,向右拐,是一个四人间,再往里走,右手边是一个两人间,两个一人间,左拐是一个两人间……”不足一米宽的走廊弯弯拐拐,串联了36张按摩床和9个足浴位。盲人摸象,这片600平米的黑暗真的是一个大象。在这里,他度过一天中的14个小时。午饭时间一般是中午12点,晚饭大概在下午6点。吃饭是仅有的休息时间,剩余的时间被分割成7、8次上钟,每次上钟又分割成不等份的40分钟到两个小时。
深夜11点后,李建明下班回宿舍休息。宿舍距离按摩店仅270米,这段花费盲人们10分钟的路程对健全人来说只用走4分钟。32位盲人的日子挑选出任意一天都和前面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健全人或许觉得隔离难以忍受,但32位盲人早已习惯这种限制,毕竟270米的直径比一个普通小区更小,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仅是两片黑暗之间的往返。
3月27日深夜,“听”到上海发布的封控消息前,李建明和几个同事去楼下的超市买了一些物资。宿舍没有厨房,没有冰箱,他们买了一些面包、泡面、挂面——一些可以充饥又能速食的食物。公告上说4月1日就能解封,“买点东西将就过去就行”,李建明想。他们没有准备更多。
盲人们在黑暗中等待。4月1日,浦东仍未解封,食物在32张嘴的咀嚼中越来越少。另一位视障者,27岁的张相聪开始担心。“没吃的了怎么办?”,“会不会饿死”,这样的声音开始在宿舍出现,焦虑随之蔓延。张相聪想到按摩店里的食物,以往,他们每天要在店里呆将近11个小时,按摩店包两餐,店里应该有储存的米面。不上钟的时候,推拿师傅们习惯吃点小面包,小饼干,辣条这样的零嘴打发时间。4月2日,李建明和宿舍楼的保安沟通后,带着两位盲人一同下楼,前往工作的按摩店。他们拿回了大米,挂面,电饭锅,还有店里的所有零食。
位于茂兴路71号的集体宿舍狭小,逼仄。4月17日上午10点40分,按摩店的员工正在为盲人们做午饭。受访者供图
“孤岛”
社区团购,团长,这些封控时期的热词,李建明并不了解,只是偶尔听同事们说过“团购很难,东西都非常贵”。他也从未使用过买菜软件,更别提知晓抢菜攻略。
更熟悉智能手机的张相聪和其他年轻些的盲人,尝试着在买菜软件上抢菜。每天早上6点,张相聪打开平台准备抢菜。蔬菜的图片张相聪没办法“听到”,只能听读屏软件读出蔬菜的种类和价格,加入购物车,再点进订单支付。等手机读完“该货物仓储不足已下架,请重新选择”,“前方拥挤请重试”等提示后,购物车里的东西也空空如也了。
“抢菜软件,我们搞不定的”,李建明说。茂兴路71号是旅馆式公寓,是外来务工者来上海打工的落脚地,住在这里的很多是保安或饭店服务员。流动性强,并没有形成所谓的社区,更没有社区群的存在。无法用买菜软件抢到菜,也没有社区团购群,青菜和肉是奢侈品,连米面也即将吃完。4月5日后,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最饥肠辘辘的清晨,他们喝一碗白粥,然后上床休息。实在饥饿难忍时,他们下一把面条,伴着老干妈吃。
多数时候,盲人们躺在床上,醒时就用旁白功能和读屏软件“听”手机,无聊了就睡一会儿。宿舍里飘荡的是短视频的声音,读屏软件机械的女声,还有《漠河舞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这些网络歌曲。
4月7日,李建明不得已开始求助。他打居委会的电话,打市民热线12345,又按照电话里的指示打给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打给市场监督管理局。他打过太多电话,也接听了太多电话,有时他会忘记电话那头是谁,只是反复地说着自己的需求,“32名盲人被困在茂兴路71号,我叫李建明,我的电话是……”4月10日,他接听了一个电话,一个女士收集了他的信息,“我把信息填到互助平台,应该会有人看到联系你的。”他听着,并不抱太大希望。
4月11日,李建明给残联打了求助电话。残联记录了他的信息,告诉他会很快处理。没有得到确定的回复,李建明不敢告诉其他同事,怕引起他们失望,只能一人焦灼地等待。4月12日下午6点40分左右,残联的物资送到了茂兴路71号,不仅有猪肉,腊肉,包菜,蒜苗,辣椒干和萝卜干,还有生活用品洗手液,香皂,卫生纸。
“兄弟们都很激动,大家把物资放好,嚷嚷着够吃好几天了。”李建明说,脸上挂着软绵绵的笑。李建明没想到的是,这份喜悦在三天后持续地冲击着他。那个他不知道的表格在网络上被人看到,网友们转发了这条求助消息,又转发到上海互助群组里。
4月15日傍晚,李建明收到了十几个快递。快递里有大米,鸡蛋,水果,面条,牛奶,各种物资铺满了宿舍的地板。“孤岛”中的盲人们得到救助,他们不必再忍受饥饿。满当当的物资是确定的,可触摸的,尽管它的来处是一个谜。物资来自哪里,捐助物资的好心人是谁,这些物资如何在运力紧张的当下送来茂兴路71号,对此,李建明一无所知。
2022年4月15日傍晚,李建明收到了十几个快递。大米、腊肉、鸡蛋,各种青菜铺满了宿舍的地板。受访者供图
三个半小时的接力救援
在上海这个拥有约2500万常住人口的大型城市,居住着约9万名视障残疾人,像李建明这样的全盲约有3万人。疫情可见的各种求助信息中,盲人们的求助声微弱。多数视障人士并不擅长交际,也不擅长求助,他们的朋友以视障者居多,认识的健全人也多是按摩店的顾客。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向认识的人求助时,李建明说自己开不了口。“我们一共32个人,32张嘴。现在大家的物资都不算充足,我们能不给社会找麻烦就不给社会找麻烦。”他没有想到,看不见世界的盲人们,在4月的上海被圈层外的越来越多人看到。一份上海疫情残障群体互助表格开始在网络上传播,多个志愿组织也开始行动。
收集32位被困盲人信息的表格来自于“爱沪有我”抗疫紧急志愿组。4月10日后,李建明的求助信息开始传播于社交媒体:“本人李建明,1583642xxxx,是一家盲人按摩店的管理人员,本店有32名盲人技师,自3月15日停业到今日,没有收入被关在宿舍,因视力障碍不让出门买不到东西每天吃一顿饭,喝的白粥,直到今天已经没有吃的了,希望政府及各部门给我们这些盲人弄点物资,尽量方便及时地送达救命救助物资。”
4月15日下午3点半,某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罗荣在微信群里看到了这则求助消息。罗荣45岁,对看到的求助信息从不拘于转发和呼吁。“行动的公民是建构良心社会的唯一希望”,罗荣常说。自上海封控管理以来,他和朋友们组织了多次互助行动,帮助的对象多为独居的老人。行动的经验告诉他,疫情中最需要帮助、最缺物资的,是残障人士和老年人。
核实救助信息后,罗荣决定再次行动。在朋友群里,他问茂兴路71号附近谁有物资。群里一位朋友在浦东找了3袋60斤的大米,另一位群友表示可以提供蔬菜,但是没有运力。
3点50分,罗荣联系了与公司常有往来的货拉拉小哥涛哥,“浦东有32个盲人被困在宿舍,今天断粮了,我们捐了一批大米,从张江送到浦东新区茂兴路71号,你能帮个忙不?钱你说。”涛哥很快同意,回复道,“捐赠的物资,我不收钱!”
提供物资的人和运输物资的人被拉入“茂兴路71号”群组里交流信息。下午5点,涛哥去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拉了米,去德州路拉了菜,载着物资的小面包车开始驶向茂兴路。下午6点50分,3袋大米和蔬菜送到了茂兴路71号。
同时,罗荣发动公司的同事打市民服务热线12345, 4月15日下午4点49分,市政府来电,经街道和属地派出所核实,政府已将物资配发送达,送去了方便面,给了订餐电话,后续会发放糕点类物资进行保障。
来自市政府的物资,残联的物资,社会各界好心人的物资都涌向了茂兴路71号。
2022年4月15日下午,涛哥开着小货车,拉载着三袋大米和蔬菜驶向浦东茂兴路71号。受访者供图
身为视障者
对大多数盲人来说,生活是重复的。走路要按照确定的路线,时间要按照确定的计划。自2021年夏天来到上海后,张相聪生活在规律中,开工的时间固定在每天10点半,回宿舍的时间是夜晚11点,午饭是店里固定的两菜一汤。这让张相聪感到安全。
封控打破了这种规律。被困职工宿舍21天后,张相聪说,他“听”手机已顾不上白天或黑夜。他怀念以往的生活,怀念步行5分钟就能在黄浦江边散步的夜晚。风声开阔,流水声不易察觉,船驶过的声音,都让他感到愉悦。
对在上海居住超过11年的李建明来说,这个城市意味着更多。2011年2月10日,是李建明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日子。“重要的日子,我都清晰记得。”李建明一字一顿说得郑重。那年他30岁,2002年从事盲人推拿工作后,他辗转过多个城市,老家河南周口,商丘,郑州,也去过江苏宜兴。因为严重的口吃,他被大按摩店和医院拒绝,只能在一家又一家小按摩店打工。“哪儿不舒服?最近怎么痛的?轻重可以吗?”推拿时需要说的话结结巴巴地说不出。
来到上海前一年,他坚持每天6点半起床,站在按摩店门前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人说一句他大声说一句,主持人讲一句他讲一句,他反复练习,口干舌燥,却不觉得疲惫。
胆怯,焦虑,自卑,在去上海的路上,这些情绪虚虚实实地包裹着他。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是广袤的,文明的,他把上海当作一个赌注,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有所成就。初到上海火车站时,工作人员称呼他为“盲人师傅”,引领着他走去地铁站,这是来自上海的声音,那个声音告诉他,“先生,请慢走。”
就是从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赌对了。他不再是旁人口中的“瞎子”,他是“视障人士”,是“盲人师傅”,他和那些“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
在上海,他不再畏惧出行,闲暇时他喜欢去恒隆商场,正大广场,南京路,盲杖带着他探索这个城市,体会普通人的快乐和生活。逛商场不是为了买什么,他喜欢闻商场的味道,喜欢听店员们的声音,“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有一次,他坐在咖啡店里出神,一位女士上前来和他搭话,很少有人会认真地听视障者讲话,他感到欣喜。他们聊了整整一下午,那位女士后来成为了他的顾客。
这些际遇可爱有趣, 4月16日,李建明收到了顾客寄来的速冻饺子。他也接到了罗荣的电话,在电话里罗荣问他有冰箱吗?他的语气听来关切,“有冰箱我给您送点肉,光喝粥也不行。”他回答没有冰箱,罗荣回复他,“那我再找点午餐肉罐头送过去。”
上海正是艰难的时候,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忙,收到这么多东西,李建明说自己坐立难安。“食物已经够吃了,您把东西送给需要的人吧。”他告诉罗荣。讲述时,李建明语速依然缓慢,但流畅清晰,他说,是上海治好了他的口吃。
(文中李建明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杨柳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