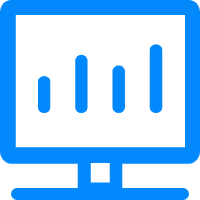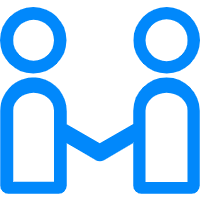独立出版品牌成为一种趋势,出版人、媒体人开始创立自己的出版工作室,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图为行思、鹿书、拜德雅、乐府文化的代表性图书(各三种)封面。 (资料图/图)
如果不做出版,任绪军最想做的职业是厨师。“厨师也很有创造性。”他说,他甚至想过要出一套饮食文化方面的书。
2017年,任绪军和同事邹荣辞掉了在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但他没有去做厨师,新的工作仍然是图书编辑。只不过,这次是将图书品牌“拜德雅”从重庆大学出版社分离出来,成了一个独立的出版品牌。
从出版机构旗下的子品牌,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图书品牌,这样的发展模式近年来在出版界并不鲜见,无论是国有出版社,还是大型民营图书出版公司,都出现了这样的“裂变”。
“鹿书”走上了和拜德雅一样的道路。2022年3月7日,原武汉大学出版社下属品牌“鹿书”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声明,表示鹿书团队三人已从武汉大学出版社离职,后续将成立新的独立品牌“惊奇”。
在同一天,另一个出版品牌“行思”也发布公告,称“由于全资投资方山东布克图书资金链出现问题,在连续三月拖欠薪资的情况下,编辑部全员决定从公司剥离,原团队就地组建成立独立出版品牌‘新行思’”。
两家在业内颇有知名度的新锐独立品牌在同一天发生变故,给出版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完全是巧合。”鹿书创始人周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当天“和社里提了辞职,马上就发了公众号”。
树立独具特色的出版品牌,是各大出版机构抢占细分出版市场、提升出版知名度的常用手段。近年来在读者中拥有较高知名度和鲜明辨识度的出版品牌,如专注于世界史的“甲骨文”、挖掘前沿新知的“万有引力”、深耕日本文学的“文治”,就分别隶属于国有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和民营的磨铁文化。
中国的图书市场化从1990年代起步,从一开始的国有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到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概念,民营出版机构终于作为“新兴出版生产力”在政府文件中得到认可。此后民营出版品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如今处于市场“头部”地位且已上市的几个民营出版公司均成立于这一时期,比如果麦在2012年成立,读客和新经典则成立于2009年。
如果说这些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受到青睐的大型民营出版机构代表了出版行业迎合市场的一端,那么数量众多的小型独立出版品牌则位于行业的另一端。出版是一门生意,同时也是一项创意活动,当更多的出版人、媒体人开始创立自己的出版工作室,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打造“小而美”的出版品牌,出版业的触角才能伸进更多值得关注的角落。
“这二三十年间,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健全的。”任绪军回顾了这些年出版行业的发展,“国内这个市场原来是什么热了就做什么,有很多空白。豆瓣上外文书的页面经常会有人问,这本书怎么没有人做?这个领域怎么国内没有书?这些年,慢慢地我们觉得发生了一些变化。小的图书公司,小的出版品牌,它们的存在,就是来丰富整个出版行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鹿书与行思的“裂变”与“新生”,代表了出版业内的有生力量在不断突破新的生长空间,也反映出更精细的分工合作和更成熟的行业生态。而鹿书和行思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近年来独立出版品牌遇到的问题的缩影。拜德雅从重庆大学出版社分离为独立出版品牌的过程,“和今天行思、鹿书遇到的问题有点相似。”任绪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为什么书店里买不到你们的书”2016年底,周昀回到了家乡武汉。
大学毕业那一年,他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待过,后来他去了北京,入职了一家业内知名的民营出版公司。“那时候,想从事出版,或者想要做一些文化上的事情,就得去北京或上海。但从事出版的年轻人却很难在一线城市立足。”在北京工作了几年后,他又回到了武大出版社,但这次却带着不同的目的。
武大出版社是面向高校的出版社,出高校教材或教师的专著较多,周昀想要做的那些面向市场的书,在武大社基本没有人做。带着在北京工作的经验,周昀也想在武大社建立这样的平台。“我希望有这方面想法的年轻人,不用再北漂,可以在武汉做相同的事情。”周昀说。
社里的老领导听说周昀要回来做“市场化的书”,做一个新的品牌,决定给他“一个试验的机会”。周昀是做事不拖泥带水的人,鹿书的诞生过程极为紧凑,2016年12月31日周昀回到武汉,2017年1月元旦假期后立马就到老东家报到上班了。“没敢奢望做成武汉文化里地标性的东西,但想让武汉也有一个做这类书的品牌。”
周昀的这个理想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有了实现的希望。“收录李沧东1983-1987年的短篇小说,此时距离他拍出第一部电影还有十年。第一次接触韩国文学,也着实被‘李部长’的文学造诣震撼。”一位网友在李沧东的短篇小说集《烧纸》的豆瓣页面这样评价。2020年《烧纸》出版之前,很少有中国读者知道导演李沧东是一位真正的严肃文学作家。《烧纸》的出版方正是鹿书。《烧纸》在影迷圈和文学爱好者中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乘着“烧纸热”,周昀马上签下李沧东的另一本小说集《鹿川有许多粪》。两本李沧东的小说集均卖出了超过5万册,鹿书的牌子打响了。
鹿书在武大社的五年多时间里,“社里面支持力度还可以,选题都是我们自己在把握,社里面也不会太干涉。现在盈利的情况也还可以,自己维持生存是没有问题的。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做得比较成功。”周昀总结了过去五年鹿书在武大社的发展。
然而驱使他离开武大社的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原因。鹿书的产量并不太高,每年差不多推出六本书,盈利可以保证。“但是如果想要继续做大,社里不会给太多的投入,毕竟我们是非常小的一块试验田,对社里的影响也没那么大。”这和周昀当初的理想有了差距。
武大社的性质也让它们有了分歧。作为一家以出版教材为主的高校出版社,不只它出的书是针对高校的,发行渠道、营销等各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都是针对高校的。“我们做大众书,和社里就存在着错位和不对口,有些方面会受很大的限制,比如版权、设计、营销、发行,所有这些方面社里都不太能提供帮助,因为这些配置针对的不是我们这类书。”周昀说。曾经有读者向周昀抱怨:“为什么书店里买不到你们的书?”武大社的发行渠道并没有涵盖某些民营书店。
和周昀另立品牌“惊奇”不同,任绪军和邹荣出走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时候,继承了拜德雅的品牌。“因为出版社的人事变动,或者发展战略的变化,导致出版社里面的子品牌,继续原来的路子做书变得难以为继。我们当时就选择独立了出来。”任绪军说。
2017年之前,拜德雅一直是重庆大学出版社下属的图书品牌。2013年,邹荣开始做一套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导读丛书。2015年,任绪军加入,这个小团队想在导读丛书的基础上做一个图书品牌。社里讨论了好几轮,“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于是成立了名为“拜德雅”的子品牌。
拜德雅既是音译,也是意译。古希腊语单词paideia,指的是古希腊城邦用于教化和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学内容,而德雅二字又暗合中国古代对“士”的培养理念。拜德雅专注学术与人文的出版调性,让它显得有些小众,然而它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读者,“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系列中的《导读拉康》甚至第八次印刷,卖了超过三万册,成为学术类图书中的畅销书。
刚出走的那几年,是拜德雅最困难的时候,这样的困难也许未来的“惊奇”也会经历。2017到2018年,拜德雅的出书量很少。“那会儿要搭建新的框架,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那两年不是很好,2019年也很困难。”2019年之后拜德雅进入到了一个平稳的状况,任绪军回忆,“特别是2021年,情况逐渐改善了。”
“大家作为一个整体,感受完全不一样”“《三只忧伤的老虎》身上有一种光晕会吸引读者。”杨全强充满自信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部古巴作家因凡特的“实验作品”,因其较高的阅读门槛多年来徘徊在中文世界之外。2021年,出品方行思和译者范晔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推出了它的首部中文译本。
“读到170页左右实在不知道在说什么,连主人公是谁也不是很清楚。放弃了。”一位豆瓣网友给这部书打了一星。但行思的创始人杨全强的出版经验告诉他,即使很多读者读不懂,但它的“光晕”会是销量的保证。
杨全强是在业界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老出版人。在业内,他被称为“杨师傅”。2006年,他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了鲍勃·迪伦的《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那时候杨师傅曾写道:“或许十年之后迪伦会获得诺奖。”2016年,鲍勃·迪伦的歌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13年,杨全强转投河南大学出版社,创办了出版品牌上河卓远。他的口味没有变,上河卓远时期,文学译介和社科类新书依然是他关注的对象。2022年,随着译者金晓宇被大众所知,他曾经翻译过的日本作家多和田叶子也被读者重新翻了出来。人们发现,这些书也是上河卓远出品的。
杨师傅出版嗅觉敏锐,文学品位前沿,但他的职业生涯似乎并不顺坦。2018年河大社对业务进行了战略调整,上河卓远的牌子随之消失。2020年他与业内好友杨芳州以独立出版品牌“行思”为名重新出发,但短短一年,行思的资方又突然撤资,“投资人突然决定终止,不再投入一分钱在出版上。这是他的决定,我们也无法影响他的决定。”杨全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行思在2021年的经营状况并不差——整个团队全年出书量不大,不到二十本,但《三只忧伤的老虎》半年卖了三万册,《詹姆斯·伍德批评作品全集》一套六册10月份出版,一个月后加印,“将来卖两万套没有问题”。成本方面,十个人团队的人员成本,十几本书的印制成本,还有几十种选题储备成本大概一百多万元,“整体上我们的投入超过五百万元。”资金已经在慢慢回笼,杨全强相信如果2022年能坚持下去,行思就可以健康循环下去。然而资本选择了撤出。
变故发生之前,杨全强对这个新的团队充满信心。他说这个团队是他从业二十多年来带过最好的一个团队。“不是说现在团队的人素质比之前的强,而是我在一个大型的国有出版机构里面,作为一个编辑,跟现在大家作为一个整体,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确实是独立出版的团队。”
和鹿书团队的主动出走不同,行思的变故背后是出版人与资方的矛盾。从“行思”到“新行思”,杨全强不仅要找到新的投资者,也要保证这个团队的完整性。“我们的团队十个年轻人,都刚刚硕士毕业,刚刚进入这一行,有热情、有能力,2021年磨合得很好,就此散去非常可惜。大家也都不愿意散。”杨全强动容地说,他是团队里资历最老的人,他想看看他最远能将这个团队带到哪里,他希望他的团队“一个都不要少”。
“独立出来,继续做,热爱肯定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责任。”任绪军和杨师傅身上,似乎都隐约可见出版人的一种担当。拜德雅独立的时候,很多选题在出版社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也买了版权,找了译者,如果不做了,会对版权方、国外的出版社还有译者,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独立出来之后,觉得也有责任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并且还要做得更好。”任绪军说。
“用自然农法来做出版”2016年,涂涂辞掉了媒体的工作,搬到大理,创办了独立出版品牌“乐府文化”,开始了他作为独立出版人的职业生涯。他和住在大理的朋友苏娅见面、聊天,苏娅对他讲了自己在大理遇到的人,有白族的手艺人,也有一个种地的日本人,说想写一写这些人。
听说那个叫“六”的日本人在大理用“自然农法”种地,涂涂来了兴趣,苏娅对他讲了好些六的故事,涂涂对她说:我们来出一本这样的书吧。那时候苏娅甚至还没有动笔。《六:一个日本人在大理的耕食与爱情》这本书的起点就在这里。
涂涂总是说自己对什么都想“试一试”。决定出版《六》的时候,乐府文化成立不久,根基不稳,但涂涂被这个故事打动,决定要试一试。
苏娅以前跟六种过两年地,她去了六的家里,说服了六,说要把他写成一本书。涂涂读到第一章书稿的时候,对就这本书非常笃定:“它有极强的感染力。它准确地把握了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六和土地、音乐、流浪……所有这些东西的关系。”
乐府文化的书看起来没有什么选题的范围。这些书不像拜德雅那样专注学术,也不像行思那样文艺,它们的作者看起来也很不一样:六是种地的,《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的作者胡冰霜是医生,《诗人十四个》的作者黄晓丹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守山》的作者肖林是个护林员……但对涂涂来说,它们好像又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作者都真诚地、投入巨大心力去做一个事情,上下而求索的那种感觉”。
涂涂觉得,《六》这本书,写的是一个现代人如何在纷乱的外部世界里寻找内心。“它不是宗教,但有一点点那个向度。自然农法恰好是六的一个方式或者道路。”他之所以被六触动,是他觉得六所做的事情和做书有类似的地方,“就像六用自然农法种地一样,我用自然农法来做出版。”
《六》首印2万册。新人第一本书印2万册,是一次市场的冒险。涂涂觉得六这个人有传奇性,一个传奇加上好的文本,他觉得它应该会好卖。然而他对市场的判断失误了,最后这个书卖得不好,到现在快四年了,库里还有几千本。
涂涂一直说乐府文化能坚持下去,是个偶然。他说自己贪婪,碰到一本好书,就想签它、想做它。现在团队20人,手里在编的还有150本书,作为一个出版公司来讲,他知道“这是不大对的”,但他又觉得它们太好了,“想把它们都做出来”。
涂涂知道乐府文化的很多实践都有点反商业规则,他从媒体转行,不是出版业内的人,有人说他的选题有“媒体感”,他苦笑着承认。“你现在让我来说,一个人要做出版,我会跟他建议说你不要像我这样做,这样做从商业上来说可能就是不太对。”
一开始他们出书太慢了。在爆红的《秋园》出来之前,他们已经成立了两年多,但总共只出了六七本书。小有收益,但养活不了一个团队。《秋园》的出现让乐府文化有了更多的可能:乐府文化在2020年实现了盈亏平衡,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受到杨本芬奶奶的启发,会带着故事、带着初稿来找涂涂:“可能和大部分出版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真的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和人交往、听故事以及读初稿,甚至不成熟的初稿。”
每个出版社,或出版品牌,都期待着一本像《秋园》这样的书。“它不是说你想遇就能遇到的,放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有这样一个方向、一个回忆。如果在十年前,可能它的销量不见得像现在这么好。像后浪当年做涂色书,直接给他们的经济带来大起色。”任绪军说。
“1980年代我们热什么?存在主义、美学。1990年代热什么?文化研究。2000年之后呢?文明冲突、女性主义,一定会有这样的变化。”杨全强的团队里都是年轻人,他希望每一代年轻人都要有自己关注的领域。
涂涂念念不忘的还是《六》。他打心里觉得这本书好,值得更多人看到。他觉得当时出版的时候,也许时机不对,也许书名起得不好。他打算今年把这个书重新出一遍。“我给它改了个名字,叫《土地的禅》,想再试一次。”他说。
出版《导读拉康》这样的理论书,出于拜德雅创始人邹荣和任绪军的个人兴趣,却意外达成了七次加印、超过三万册销量的成绩。图为拜德雅工作室内景。 (受访者供图/图)
“不能总是用爱发电”“独立出版品牌,在很大程度上,创始人的性格决定了这个品牌的走向。”姚萼是独立的图书出版策划,曾经接触过多个出版领域的独立品牌,在她看来,正因为独立出版品牌的规模小,专注的领域细分,创始人的气质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你的气质或关注点正好是社会热点,你是不是做得就更容易些?”
杨全强的兴趣和关注点决定了上河卓远、行思和新行思的调性。“社科新知、文艺新潮”,杨全强说他很喜欢世纪文景的这句关于自身定位的口号。
邹荣和任绪军一开始做导读系列,也是自己的兴趣所至。“像《导读拉康》这样的书,一开始是我们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们自己有这个需求。我是学文学的,我同事邹荣学心理学,自然要用到这些理论。导读也是我们自己进入这些思想家的研究领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就把这个书做了,由此就衍生出来后面的这系列出版的行为。”
媒体人转行的涂涂可能对各种行业内的商业逻辑满不在乎:“我是那种有点天马行空的人。同事们能够脚踏实地的,有些时候能拉住我。我骨子里可能有一点爱冒险的东西。签选题,遇到新人,我都想试试。”
姚萼关注到了其他看起来不那么“文艺”的独立出版品牌。“有一家品牌做的方向是流行网文,书做得很美,配各种周边,他们就活得很好。同样是独立品牌,也并不都像杨师傅那样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根据国内相关出版法律法规,图书出版必须要有书号,而只有国有出版社才能拥有每年定额的书号。这就决定了无论是民营出版大公司还是小型出版品牌,最终一本书要呈现在读者眼前,与某个出版社的合作都是绕不开的。由此形成了出版行业多头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局面。
韩实是某一线城市国有出版社的编辑,在他看来,为了在选题上更有自由度而出来开工作室单干,面临着更高的人力成本、书号成本,如果书卖得不好,“这些成本有可能会被转嫁到译者和编辑身上”。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长远来看,主要还是书这个产品由于各种原因——电商打折、新媒体渠道带货等,利润空间非常低,即便大卖也可能只赚几个点,久而久之都是亏的多。虽然选品看似很有价值,但真的做这行的人不能总是用爱发电。”
姚萼用“八仙过海”来形容目前国内独立出版品牌的形势。她最近接触的一个独立品牌,在商战上的“打法”令她印象深刻:“出来一套书,上市一周卖了10万册。”这家品牌自己总结了方法:第一,打闪电战,所有人压上去做营销。一共只有五个人,四个在短期内铺开去做营销;第二,它的文案根据市场反馈一直在变。“这个也是‘读客’的方法。市场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这个东西跑通了,一下子起量了。当然学术书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先天的气质就不一样,但它们也是独立品牌。”
除了独立出版品牌,其他的出版业态也在兴起。姚萼的工作相当于独立编辑,比出版品牌更加游离,更加自由。她一头接触作者,编辑作品,另一头接触出版社或出版品牌,联系出版。另外一种业态“版权代理”,在国外已经成熟,在国内才刚刚起步。版代也和独立出版策划一样,架设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间,但它和作者的关系更加紧密,且买断版权,兜售作品。姚萼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成为独立代理版权的策划编辑。
周昀的“惊奇”刚刚起步,版代公司对它的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出版品牌的裂变,我觉得这是一种趋势。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是出版业成熟的标志。这几年国内也陆续出现了版权代理公司,它们会去挖掘更多的国内原创作者,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一些新的模式出现,这些模式会不断优胜劣汰,会出现一些有生命力的新迹象。”周昀说。
“出版最有意思的部分”杨全强、周昀和任绪军都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人。他们对体制内外的出版环境都有切身的体会。对目前小出版品牌成群涌现的现象,都保持了乐观的态度,“如果国家政策没有大的变化,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小品牌出来。”杨全强说。
做独立品牌和做出版社下面的子品牌,都有各自的难处和“轻松”之处。对杨全强来说,独立出来虽然多了很多肉眼可见的成本,但在出版社内部,消耗的却是无形的“人际成本”,“你可能意识不到,但它可能会对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人天生不愿意去交际,他就想好好做几本书。有时候好书需要培养,出版社愿不愿意培养你的作者呢,社里资源就那么多,它要养你的作者,编辑室主任的作者要不要养?”
杨全强现在更偏爱独立品牌,“几个人的小品牌,只要跟出版社沟通好了,书号的模式确定好了,几本书磨合下来,这样更自在。”
拜德雅在这两个模式中都有长期的实践,对任绪军来说,愿意放弃什么、争取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在出版社当然有出版社的好处,至少你在经济、经营层面,不用太操心。当然你牺牲掉的,可能是选题做不了,和来自系统本身的消耗。做书某种程度上是精神、心灵层面的东西,有时候你很难去说服自己去接受这些妥协。”
拜德雅选择了放弃安逸、舒适,“或者说放弃掉那个可以给你兜底的东西”,以期获得“相对多一点的自由和更多想象空间”。
“做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冒险的事”,热爱冒险的涂涂说,“一个真正想做书的编辑,他在体制化的出版社里面,我觉得会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冲突,但是他没有办法克服这种冲突。他可以努力找到一点点空间,做一两本自己热爱的书。一些有能力的编辑想出来试试,就出来了。这种内心的冲突,可能是现在独立出版品牌遍地开花的重要原因。”
韩实在2021年做了13本书,这在出版社的编辑行业中算是翘楚。这13本书中,“有小领导给的资助选题,也有大领导给的项目选题。资助选题就是作者出资助费,铁赚。项目就是国家资助,也铁赚。”在做好这些的基础上,他在这一年里可以“精心地做一两个自己喜欢的选题”。
尽管很多出版品牌在书号问题上选择与出版社合作,以出版社的发行和利润分成来摊薄书号成本,但是对一些更加微型的出版品牌来说,每本书五六万元的书号成本,却关乎其能否盈利。
“这个书号成本确实跟在体制之内不太一样。现在独立品牌很多采取了与出版社合作的方式,比如出版社提供书号,参与了印制、发行和宣传,最后也利润分成,出版品牌就相当于它的外包策划编辑团队。”杨全强说。
但是姚萼看到很多与出版社合作并不愉快的例子,“实际上一本书要不亏本没有那么难,它只要把首印差不多卖掉,肯定是不赔。印制书本身成本并不高,但因为书号成本的存在,很多独立的小品牌做不起来。”作为一个比独立品牌更加“独立”的图书策划,书号成本对她来说有更加深刻的切身之痛,“想独立地做一本书,实际上遇到最关键的困难就是书号不开放。”
尽管有着种种困难,姚萼还是对独立出版怀抱着信心。“出版就是一直会有人投入热情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去做各种实验,我觉得这是出版最有意思的部分了。”她说。涂涂的想法更加直接明了,“其实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找到好书,然后把它们出版出来。”他说。
(姚萼、韩实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