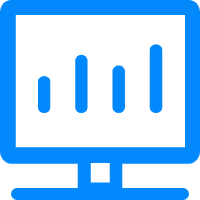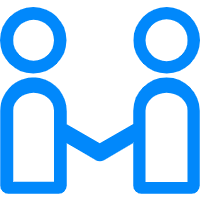内容提要:作为明成祖嫡系君主所控制的《明实录》,在对待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的年号及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态度和掩盖倾向,反映了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被打倒的重要人物上的处理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人物失载的命运。随着皇权的松弛和士风的变化,由史臣们具体纂修的晚明实录,开始改变以往掩盖建文历史的做法,频繁载录建文的历史以及为之平反的请求,表明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与代表上层建筑的君主之间,在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明实录》是太宗朱棣“靖难”篡位后,由他本人和其子孙主导纂修的,《太祖实录》虽然初修于建文朝,但经过朱棣的两次改修,早已成为其政策和情感的承载工具。因此,这13朝实录基本上都是朱棣嫡系主修的作品,对于被推翻的建文帝朱允炆的态度自然有着明显的排斥倾向。通过探讨《明实录》对于建文历史的记载,能够看出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被“打倒”的重要人物的处理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人物悲惨的历史命运,同时也能够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官方史学对建文历史掩盖和控制的松弛,以及时势的变迁和人心的变化,特别是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与代表上层建筑的君主之间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的差异。关于本题目所涉及的问题,黄云眉对《明实录》在建文帝史实上的篡改作过指正①,牛建强、杨艳秋等从野史角度对建文帝史籍的出现和发展作过探讨,吴德义对建文史学的史料作过搜集与考订②。不过,黄云眉并非专力于建文历史被实录歪曲的揭示,牛、杨二人则主要是通过建文野史的发展展露明代史学政策的放宽,吴德义则着眼于综合性的史料搜集,而专门探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记载的态度及其变化,特别是以关键词的统计来促进此一问题研究的论著,迄未寓目,故本文之撰,仍有独特的价值。
一、从关键词汇的统计看《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
朱允炆(1377~1402?)是朱元璋嫡孙,太子朱标之子,朱标死后,被封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继皇帝位,年号建文,但于建文四年被“靖难”的成祖朱棣推翻,不知所终。此后,为朱棣嫡系操控的13朝实录,除直接记载建文历史的《太宗实录》持歪曲态度外,其他的实录基本上对建文历史是掩盖、忽视和不敬的,只是到了晚期,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下面分三种情况作一叙述。
(一)《明实录》总体上对建文帝历史采取掩盖和忽视的态度
根据笔者用关键词进行统计,发现长达1600余万字的《明实录》中,记载建文事迹的地方很少,提到的地方也不多。“允炆”一词只有8处,专指朱允炆的“皇太孙”一词有10处,“太孙”一词有1处。“建文”一词最多,有307处,其中一部分是表达时间的概念,如“建文中”有88处,“建文时”24处,“建文间”2处,“建文年间”1处,“建文年号”11处,“建文元年”1处,“建文五年”2处。加起来,共有129处是时间概念,而另外的178处大概指建文帝本人,其中“建文君”有58处,“建文皇帝”3处。但后世通用的“建文帝”一词则无一处见载。表现朱允炆失位的“逊国”一词,仅有4处;与之相关的“革除”一词有41处。这就是《明实录》有关建文历史的全部记载。
若单独统计建文帝的相关数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笔者以与其同辈、同由储君继承皇位的仁宗朱高炽来比较,就很能说明一切。“仁宗”一词在明宣宗以后的《明实录》中出现628处;年号“洪熙”一词出现187处;名讳“高炽”没有一处,显系避讳。不涉“仁宗”二字的“昭皇帝”一词有10处(“昭皇帝”共有231,其中“仁宗昭皇帝”221处)。以上统计,笔者未将《仁宗实录》计算在其内,因为朱允炆被推翻后无人为其修实录,为了有可比性,仅从仁宗的儿子宣宗的《实录》开始计算。朱允炆被推翻后无庙号,长期以来也无谥号,代用的称呼为“建文君”(58处)、“建文皇帝”(3处),有时径以“建文”(129处)指称,将这些加起来,共有190处;远远无法与“仁宗”一词多达629处相比,加上“昭皇帝”一词10处,共639处;几乎可以说是建文帝的3.4倍。至于年号,“洪熙”出现187处,“建文”出现129处,也少58处。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建文帝在位4年(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至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而仁宗在位不足一年,约九个月左右(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至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建文帝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而仁宗则是第四个皇帝,建文帝的资历远比仁宗要深(以皇帝身份出现在实录中,应该早26年,多两部实录的篇幅);建文在位时锐意改革,对明代历史触动很大,而仁宗则毫无建树,两相比较,建文帝应该在明代官方史学中得到特别的关注才是,然而继位时间短、资历浅、平庸的仁宗却在《明实录》的记载上处处胜出,显见被朱棣嫡系掌控的实录对建文历史的掩盖和忽视。至于从感情上来看,实录直呼“允炆”名字8处,而对于“高炽”则避讳甚严,一处不及,也反映了实录偏颇的态度和倾向。
(二)直呼朱“允炆”名讳与抹除建文年号
直接称呼本朝皇帝的名讳,在传统社会中是大不敬的。然而,《明实录》中却有8处直接称建文帝为“允炆”,其中4处出现在《太祖实录》。该实录卷116载: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皇第三孙允炆生,皇太子次子也。”同书卷221载: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庚寅,“册立皇第三孙允炆为皇太孙,祭告太庙。”卷242载: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癸卯,“册光禄少卿马全女为皇太孙允炆妃。”特别是卷247的记载,更是耐人寻味:洪武二十九年九月甲寅,“皇曾孙文奎生,皇太孙允炆长子也。上曰:‘十月数之终,又生于晦日。’命内庭勿贺。”另4处出现在《太宗实录》中,《太宗实录》卷1载,洪武二十五四月丙子,“立允炆为皇太孙。”另外,在朱棣继位和祭天的诏书中,多次点名“允炆”并加以抨击。通过直呼其名,以达到降低建文帝神圣性和尊崇性的目的。
为去除建文帝的历史痕迹,朱棣嫡系在修《太宗实录》时,故意将建文年号隐去,仅在《太宗实录》卷1介绍建文帝继位时,用了1次“建文元年”,其他各处皆曰“元年”、“二年”、“三年”和“四年”,不提“建文”二字。《太宗实录》卷9下在记载(建文)四年六月庚午时,忽改称“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朱棣并且下令“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遂仍以洪武纪年。今年称洪武三十五年”。将“建文”年号给改换和革除了,以并不存在的“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取代之。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很快就把建文朝历史遗忘了。到万历年间,儒臣们对建文历史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连他继位多长时间都不清楚了。有的认为是3年,如弘治十二年,致仕礼部主事杨循吉称:“臣闻洪武后有建文君,乃太祖高皇帝嫡孙,躬受神器,称帝建号者三年。”③有的认为是5年,如万历三十年,礼部在覆核通政使沈子木奏议时,提到“建文以高皇帝之孙、懿文太子之子,嗣位五载”④。显然,无论是沈子木还是礼部,都已记不清建文帝继位到底有多久时间了。失忆的并非沈子木一人和礼部一个衙门,南京给事中黄起龙竟也在上疏中声称“建文五年正朔,统顺系明”⑤,误以建文在位有5年。直到天启二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欧阳调律在奏疏中仍然误以为建文帝在位有5年时间:“建文皇帝乃太祖高皇帝嫡长孙也,……故臣谓国史另编建文五年,以昭统系。”⑥其实,建文帝在位时间是四年零一个月。直到神宗时,群臣建议恢复建文年号,于是“建文年号”这一词汇才出现了11次(《神宗实录》9次,《熹宗实录》2次),但具体以“建文元年”、“建文二年”、“建文三年”和“建文四年”面目出现的时间副词,基本上仍无记载。
朱棣“革除”建文年号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建文”一词只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成为他人生活经历的一个背景,而与建文帝本人的历史无关。《太宗实录》卷51载:“实授李琦广西道监察御史。琦初为沧州儒学训导,坐事谪戍云南右卫。建文中,以荐为御史……”《宣宗实录》卷46在讲述已故的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向宝的经历时称:“宝,字克终,江西进贤人,洪武乙丑进士,……应天府尹,建文中坐累谪广西。”《宪宗实录》卷19,成化元年七月甲戌,在叙述南京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王瑛的父亲王裕的经历时称:“建文时为百户。”“建文”完全成为一个模糊的时间副词,不能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联系起来组成具体而明确的年号和纪年。
(三)从“建文君”到“建文皇帝”的用词反映了历史禁忌的松弛
我们将最能反映对建文帝尊敬的词汇找出来加以讨论,以此观察实录对待建文帝的态度。《明实录》中对建文帝最尊敬的称呼是“建文君”和“建文皇帝”。两个概念出现的时间前后不一。
“建文君”的称呼共有58处,竟然有40处都出现在《太宗实录》中,其中31处出现在卷1至卷9。这一部分内容基本上来自于永乐初年的一部佚名史书《奉天靖难记》,但该书并未用“建文君”一词,而用的是“允炆”,即直呼其名。到宣宗修《太宗实录》时,便改用“建文君”一词,说明当时对建文帝的敌对情绪有了一些缓和。将“允炆”改称“建文君”,很耐人寻味,因为既表明了宣宗的大度,又没有直接称呼其为皇帝,它既可指“建文国君”,也可以理释为一般性的尊称。据《太宗实录》卷1,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载:“一日朝罢,建文君谓子澄曰:‘忆昔者东角门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须密。’”于是黄子澄与齐泰商量先剪除燕王的同母弟周王,“明日入白建文君,喜曰:‘黄先生善谋矣。’”当燕王上疏为周王求情时,“建文君观之戚然”。除了《太宗实录》密集使用“建文君”一词外,后来的《实录》则应用日稀,《仁宗实录》无一处用之,宣宗、英宗和世宗《实录》各1处,《孝宗实录》2处。至万历年间,对建文历史的控制开始松动,于是“建文君”概念的使用又骤然增加,《神宗实录》达12处。此后的《熹宗实录》也有1处。
“建文君”虽有尊称之义,但在承认朱允炆皇帝地位上并不明确。到了晚明时期,“建文皇帝”一词开始出现,在《神宗实录》中出现了2次,《熹宗实录》也出现了1处。“建文皇帝”比之于“建文君”,直接承认朱允炆的皇帝身份和地位。“建文皇帝”概念的出现,与小皇帝朱翊钧的求知欲相关。据《神宗实录》卷30载,万历二年十月戊午,“上御文华殿讲读,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从此,“建文皇帝”一词开始被官方的衙门和官员所使用。同书卷361载: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巳,“礼部言:‘建文皇帝祀典久湮,请于懿文太子庙侧别立一庙,四时致祭。’”《熹宗实录》卷29载:天启二年十二月庚寅,南京户科给事中欧阳调律奏:“建文皇帝乃太祖高皇帝嫡长孙也。继统则正,享国亦久。”以上三处均使用了名正言顺的“建文皇帝”的概念。第一处是史臣在撰写《实录》时使用的,第二、三两处,是大臣们在奏书中使用而为《实录》照录的。无论如何,都反映了晚明时期政治氛围的宽松,以及对历史禁忌的松弛。
二、《明实录》对建文帝历史处理的方式与倾向
对建文帝直接描述和记载的是反映“靖难”之役的《太宗实录》的第1~9卷。在这9卷中,对建文帝历史的处理有特殊的方式,反映出作者十分鲜明的主观倾向。
(一)直接贬低建文帝的人格与行为
虽然将“允炆”改称“建文君”,但这9卷中却肆意攻诋和诬蔑被推翻的建文帝的人格与言行。该录载:“太祖崩。是夜即敛,七日而葬。皇太孙遂矫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踰月,始讣告诸王,且止毋奔丧。”并称建文朝廷“日益骄纵”,“遣宦者四出,选女子充后宫,媚悦妇人,嬖幸者恣其所好,穷奢极侈,亵衣皆饰珠绣,荒淫酒色,昼夜无度,临朝之际,精神昏眩。百官奏事,唯唯而已”。还称建文“倚信阉竖”,“凌辱衣冠,虐害良善,纪纲坏乱,嗟怨盈路”。除了上述对建文帝的人格及政策进行攻击外,还利用“天人感应”观念,极力将朱允炆的行为与天变联系起来,说明建文帝之亡出于天意:“于是太阳无光,星辰紊度,彗扫军门,荧惑守心,飞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疾疫,在在有之。文华殿、承天门及武库相继灾,君臣之间恬嬉自如。”⑦
(二)以建文帝作为配角衬托成祖朱棣的英明形象
在《太宗实录》卷1~9中,更多的是将建文帝加以矮化,将之写成朱棣的配角,以突出后者的高大形象。
首先,《明实录》故意借朱元璋之口,盛赞朱棣而贬低朱允炆。《太宗实录》卷1载,洪武二十五四月丙子,“太子薨。太祖愈属意于上。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长孙弱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托。’翰林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长,可继承矣。’太祖默然,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于天耳。’遂立允炆为皇太孙。”通过太祖一贬一褒的评价,烘托成祖的英明和理该继位的正统形象。
其次,实录总是借建文帝及其大臣之口,间接地歌颂朱棣的英明和伟大。据《太宗实录》载:当建文君臣谋划削藩时,齐泰竟说:“燕王英武,威震海内。”黄子澄也称:“燕王素孝谨,国人戴之,天下知其贤。”当建文帝被朱棣上书所打动时,齐泰、黄子澄二人私下议论建文帝是“妇人之仁”。在寻找削燕藩借口时,建文帝称“彼罪状无迹可寻,何以发之?”齐泰、黄子澄却说:“欲加之罪,宁患无辞?”建文帝复以为“何以掩天下公议,莫如且止”。黄子澄说:“为大事者,不顾小信。况太祖常注意燕王,欲传天下,陛下几失大位矣。非二三臣寮力争,则固已为所有。陛下安得有今日哉?”要求向燕王开刀。结果建文君却说:“燕王勇智绝人,且善用兵。虽病,猝难图。宜更审之。”⑧这段对话,就通过建文帝及齐、黄之口,将自己的对手描绘成“勇智绝人”、“英武,威震海内”、“素孝谨,国人戴之”的形象;又通过齐、黄之口,将建文帝说成是“妇人之仁”。如此一来,建文帝的卑琐软弱、犹豫不定与燕王的高大威武、勇智绝人形成鲜明对比。这充分反映了《太宗实录》的偏颇倾向。
其三,实录总是把建文帝写成被朱棣的上疏和口信所感动的形象。据《太宗实录》卷1载:太祖崩后,建文君臣将燕王的同母弟周王橚降为庶人,特地让燕王“议其罪”,于是朱棣写了一封十分感人的奏疏,请求建文帝宽宥其弟,“其言恳恻深至”,结果是“建文君观之戚然”,将奏疏给齐泰和黄子澄看,并说:“事莫若且止。”⑨卷8载,(建文)三年闰三月癸丑,朝廷派大理少卿薛嵓赍诏至燕王军中。薛嵓受燕王之托,回来后劝道:“燕王语直而意诚,累千百言皆天理人心之正不能难也。其将士虽不及吾十一,而皆与王一心,父子不过焉。吾军虽众,然骄而懈,疎而寡谋,且诸将不和,未见有胜之道。今日之事,朝廷但当处之以道,不当以力。”结果,“建文君以语孝孺曰:‘诚如嵓言,曲在朝廷。齐、黄误我矣。’”把建文帝塑造成燕王的应声虫。同卷又载,当朝廷将领吴杰、平安、盛庸发兵扰燕兵粮道时,燕王遣指挥武胜等“奉书于朝”,结果,建文帝再一次被感动:“书进,建文君览之,益感悟,有罢意。”总之,建文处处被燕王的“真情”所打动和支配。
(三)把建文帝塑造成听任“奸臣”摆布的无能君主形象以证明“清君侧”的合理性
《明实录》常把建文帝写成无主见、懦弱无能、任凭“奸臣”摆布的形象。据《太宗实录》卷1载:太祖死后,建文帝将“朝廷政事一委黄子澄、齐泰,二人擅权怙势,同为蒙蔽,政事悉自己出,变更太祖成法,而注意削诸王矣”。二人还“私谋”曰:“今上少,不闲政事,诸王年长皆握重兵,久将难制,吾辈欲长有富贵,须早计。”齐泰说:“此易易。但使诬告其阴私,坐以不轨削之。削一国可以蔓引诸国。”并强调“他事不足动,惟大逆则不宥。”这番对话,《太宗实录》的作者何以知晓?其实不过是有意诽谤建文帝倚重的大臣,从而达到贬斥建文帝的目的。这里把建文帝君臣削藩的大业,说成是齐、黄二人“欲长有富贵”的企图,显然是在为“清君侧”寻找理由。实录把建文帝说成是被“奸臣”欺隐的瞎子和聋子。《太宗实录》卷5载:(建文)元年十一月戊寅,“黄子澄等知李景隆败,匿不言。建文君间问子澄,曰:‘外间近传军中不利,果如何?’子澄曰:‘闻交战数胜,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暂回德州,待来春更进。’子澄遂遣人密语景隆,令隐其败勿奏。景隆奏如指。由是,内外蒙蔽朝廷,所得军中奏报,皆非实事。景隆之为将也,盖子澄荐之,故所言悉听云。”
甚至连给燕王的诏书用什么口气来写,建文都不能做主,而要听“奸臣”的。《太宗实录》卷8载,(建文)三年闰三月癸丑,朱棣兵至大名,听说建文帝已将齐泰、黄子澄等放逐,于是致书朝廷。建文君以书示方孝孺。方孝孺建议回封诏书,先疑惑之,以待后援。“建文君善其策,遂命孝孺草诏,宣言欲罢兵。建文君览诏曰:‘既欲怠之,则当婉辞,庶几肯从。’孝孺曰:‘辞婉则示弱矣。’”结果朱棣“读诏”后,见“辞语□慢”,便知道“此诏必非出陛下意。盖奸臣挟诈以欺我也”。
有时实录还将建文帝写得“仁慈”和“柔弱”一点,以突出“奸臣”的凶恶和无情,以及建文帝被摆布的“事实”。《太宗实录》卷8载,(建文)三年五月庚寅,燕王派指挥武胜等出使朝廷,建文帝读了朱棣的信后,给方孝孺看,并说:“其词甚直,奈何?……此孝康皇帝同产弟,朕叔父也。今日无辜罪之,他日不见宗庙神灵乎?”方孝孺指陈道:“陛下果欲罢兵耶?天下军马一散,即难复聚。彼或长驱犯阙,何以御之?骑虎之势可下哉?且今军马毕集,不数日必有捷报。毋感其言。”于是,“孝孺出矫命,锦衣卫执武胜系狱”。
以上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其视角和态度都值得重新检视。
(四)客观陈述建文帝的言行
当然,《明实录》也有客观地陈述和记载建文帝的历史和言行的地方。《太宗实录》卷1载,(建文)元年三月,“建文君命都督宋忠调缘边各卫马步官军三万屯开平,燕府护卫精壮官军悉选隶忠麾下,护卫胡骑指挥关童等悉召入京,调北平永清左卫官军于彰德,永清右卫官军于顺德,以都督徐凯练兵,临清都督耿瓛练兵山海,诸将防于外,张昺、谢贵防于内,约期俱发。”这些记载都是陈述事实,并无明显的褒贬成分在内。同书卷3载:(建文)元年八月丙寅,“建文君闻耿炳文败,始有忧色。语黄子澄曰:‘奈何?’子澄对曰:‘兵家胜败常事,无足虑。……区区一隅之地,岂足以当天下之力?调兵五十万,四面攻之,众寡不敌,必成擒矣。’曰:‘孰堪将者?’子澄曰:‘曹国公可以当之。前不用长兴侯而用此人,岂有失哉?’遂遣曹国公李景隆代之。”这虽然写了建文帝闻说耿炳文战败后有忧色,但却是客观描述,并不存在故意抹黑的意图。
作为胜利者,很多时候只需客观描述已发生的历史,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无需故意歪曲。如《太宗实录》卷9上载,当燕王率师直逼南京时,“朝之六部大臣皆图自全之计,求出守城,都城空虚,上下震悚。建文君乃下罪己之诏,遣人出徵兵。”这些记载也基本上是客观描述。此时,方孝孺出了个缓兵之计,“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召募壮丁,当毕集。天堑之险,北军不长于舟楫,相与决战江上,胜败未知”。于是,“建文君善其言,乃遣庆城郡主度江至军门,白其事。郡主,上之从姊也。”这些记载也大体上是客观的。
三、《明实录》反映了君臣之间对建文帝态度的歧异
对建文帝的历史,明代君臣之间既有相同的观念,也有不同的立场。对于朱棣嫡系的君主们来说,他们可以接受为建文帝的忠臣们平反,因为这可以鼓励臣子们为自己尽忠效力;然而,他们难以接受为“成祖”所推翻的建文帝平反,因为对建文帝平反,意味着对成祖的否定。对于儒臣们来说,他们不可能总是受成祖嫡系的影响,有时候更多的是从太祖的统系上思考问题:“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要求承认建文帝的统系,当然也照顾朱棣“靖难”的合法性,不过,建文继位是“大经”,朱棣靖难是“微权”。这就与成祖嫡派子孙的君主们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尽管儒臣们苦口婆心地劝谏君主为建文帝恢复年号,举行祀典,但基本上都遭到了否决,只在部分观念上趋向一致。晚明时期,在君臣产生分歧的情况下,掌握实际修纂权力的史臣们,开始在《明实录》中增多对建文帝历史的记载,并将君臣之间的分歧载入史册。
(一)实录记载了儒臣先臣后君、先易后难的平反策略
建文历史无法永远“革除”,不时有儒臣对建文历史进行探索,直接提出对建文帝平反,复其位号的建议。据《孝宗实录》卷149载,致仕礼部主事杨循吉奏:“臣闻洪武后有建文君,乃太祖高皇帝嫡孙,躬受神器,称帝建号者三年。”后遭成祖“削建文位号,今百余年未蒙显复”。他认为“建文虽以一时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实则生民之主”,应该按宪宗“帝景皇而不以入庙”的方法,“仍复建文君尊号如景皇帝故事”。孝宗下其疏于礼部聚议,终未允准。于是儒臣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先从“革除”年间的忠臣入手进行翻案。据《世宗实录》卷177载,嘉靖十四年七月乙酉,吏科给事中杨僎首次上疏提议对革除时期的忠臣铁铉、张紞、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进行平反,称他们“均能奋不顾身,以义自殉,视死如归,不为势屈”,要求“将铉等死忠实迹,付史局编集,垂诸不朽”。事下礼部,但遭到代表正统立场的尚书夏言等人的反对,认为那些人“是当时误国有罪之人”,不能平反,并指出杨僎“实新进儒生,不识忌讳,所据奏内事理实难准议”。世宗“责僎不谙事体,轻率进言,姑宥之”。
神宗继位后,趁皇帝年幼,大臣在为“革除”忠臣平反这一点上与幼主达成共识。据《神宗实录》载,在为圣母上尊号时,神宗下诏旌表和祭祀建文年间的死难忠臣:“革除间被罪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无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士”,因此应当“褒表忠魂,激励臣节”,并要求各地方官为忠臣“特为建祠,或即附本处名贤忠节祠,岁时以礼致祭”。⑩在此背景下,神宗开始关心建文历史。万历二年十月戊午,12岁的神宗在文华殿讲读时,“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问建文帝下落。张居正答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传言建文“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正统间忽于云南邮璧上题诗,才被发现,“验知为建文也”。当时七八十岁了,“后莫知其所终”。神宗于是命张居正将建文帝全诗“书写进览”。(11)
神宗的这种态度,让儒臣们得陇望蜀,在为革除间忠臣平反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对建文帝平反的要求。万历十六年二月丁丑,国子监司业王祖嫡指出革除间臣子既然能获平反,建文帝更应该给予平反:“建文以太祖嫡孙,临御四载,别无他过,不得援诸臣之例以慰幽魄,恐成祖之心,亦必有未安者”。于是他特地上奏,提出应该恢复建文年号和历史编年。他认为,建文帝是太祖亲选的法定接班人,建文当政是“大经”,而太宗靖难是“微权”,因此应该肯定建文帝的年号:“高皇帝艰难百战,奄有天下,挈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经也。文皇帝际时艰危,兴兵靖难,挈神器而完之高庙,济变之微权也。钟虡不移,人代顿没,此何说也?”于是从五个方面证明“建文纪年之不可泯”的理由,特别是从太祖而非成祖的立场出发,论证了建文纪年的合法性:“夫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视成祖、建文同一子孙也。今日之视二祖同一祖宗也。不革除谓不能仰体成祖心,必革除其为仰体太祖心乎?书靖难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纪建文在位之实,何悖之有?”王祖嫡还从抵消野史的影响上,要求对建文历史进行正面记录:“夫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纪建文者,无虑数十家,谬无相承,至有不忍读者。逞其雌黄,遂淆朱紫,岂细故也哉?”他建议:“今宜复建文位号,仍付史馆,将四年事绩,修辑为录,尽废野史不经之说。”三月壬辰,大学士申时行上奏称,境遇类似的景皇帝位号已复,“惟建文年号,自靖难以来,未有请复位号、修《实录》者。事繇创举,未经会议,臣等擅难定拟。伏乞圣断施行。”神宗谕曰:“建文年号仍已之。”(12)看来,儒臣们低估了已经长大成人的神宗的政治判断力。
(二)实录反映了君臣在恢复建文年号上达成部分妥协
到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时,朝廷在礼部尚书陈于陛的主持下,开始纂修纪传体的国史。这自然牵扯到建文帝的本纪和建文年号问题。《明实录》对这一重大问题,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八月癸酉,礼科左给事中孙羽侯条奏:“纂修正史,议本纪则建文、景泰两朝,宜详稽故实,立二纪,勿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但是,疏被留中。(13)二十三年九月庚辰,大学士赵志皋指出,此前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乞于纂修正史内议复建文年号”的建议,“考订详明,议论正大,似宜准从。谨拟票帖呈览。”(14)礼官范谦等人指出:“夫革除云者,欲后世不复知有建文耳”。然而,“今历年二百,历世十叶,靡不知有建文君者。今日之闻见已不可除,何况后世天下万世,自有耳目,稗官野史各有纪载,欲以建文纪年作洪武虚号得乎?此于势亦有难掩。”为了消除成祖嫡派君主的抵触,范谦等礼部官员为之折中和辩解:“成祖之嗣服也以戡乱,建文之出亡也以逊国,其名正,其言顺,何嫌何疑而假俺饰以起后世纷纭之议?”然后通过夸奖今上的宽容,希望能达到复建文年号的目的:“我皇上登极诏内,开革除被罪诸臣,令各祠于其乡,其坟墓苗裔有存者厚加恤录。万历十六年允本部题覆司业王祖嫡疏,特复景皇帝,实录俟纂改正。夫元史可修,奈何失其寔于当代?胜国之君可谥,奈何削其号于本朝?景泰之位号可改,奈何靳其名于建文?一时死事之臣可褒,奈何遗弃其君而令淹没于百世?”他提议“及此纂修之时,命史局于高庙实录中摘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遗事,复称建文年号,辑为《少帝本纪》。”奏上,“诏以建文事迹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号”。(15)至此,明朝政府终于承认了建文年号。
然而,明廷对建文年号的承认,只限定在当时正在纂修的纪传体国史的本纪部分,将建文元年至四年历史附于《太祖本纪》之末,但并未同意在各个领域都承认建文四年的历史和全面恢复建文年号(16)。直到万历三十七年,南京给事中黄起龙仍在就建文年号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疏请求:“建文五年正朔,统顺系明,迄今正史尚悬,因循祖号,殊乖明旨。”(17)《熹宗实录》中,仍然记载了儒臣们要求全面恢复建文年号的企图和努力。该录卷29载:天启二年十二月庚寅,南京户科给事中欧阳调律虽然承认“国史另编建文五年,以昭统系,无俟再计”,但却指出建文皇帝“始终年号不著”,则似乎又表明,朝廷并未全面承认建文的年号和历史。天启三年,户科给事中罗尚忠仍然在上疏“请追复建文年号、庙祀”。(18)天启四年,欧阳调律再次就“建文君编年、庙祀”上疏请求:“至编年一事,成祖诏中原无降削位号之说,前此祗属承讹。今即列建文年号于永乐之前亦有嫌忌,而强附之洪武后,统系不明,乞敕廷议,毅然举行,成一代之美。”皇帝仍然“不许”。(19)看来,建文年号下统摄的建文四年的历史,只能附录于纪传体国史中的《太祖本纪》后面,而不能全面地予以恢复。但自史馆失火和陈于陛的去世,纪传体国史的修纂宣告失败(20),建文年号合法出现的规定区域业已消失。建文年号从此再也没有出现于明朝的国史系统中。
(三)实录反映出君臣在建立建文帝祀典上始终对立
根据实录记载,儒臣们在议复建文年号的同时,也开始议立建文帝的祀典。而从祀典方面入手要求为建文帝平反的臣子,多数都是礼部或太常寺等机构的礼官以及给事中等言官。《神宗实录》卷361载: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巳,礼部言:“建文皇帝祀典久湮,请于懿文太子庙侧,别立一庙,四时致祭。”但是神宗“不报”。同书卷374载:万历三十年七月癸未,礼部覆通政使沈子木的奏议,从太祖的角度申明建文帝与成祖都是一家:“不知天下,高皇之天下也。正朔,高皇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两敌。代邸天授,少帝何尤?”因此“请于懿文太子庙侧别立一庙,四时致祭”。万历三十八年九月辛亥,南京太常寺少卿刘曰梧奏道:“夫建文君非他,高皇帝嫡孙”,后“君临天下,宽仁恭让”,虽然因“文柔不断,更张无序,取怨宗亲”被成祖推翻,但这只不过是“家庭禅受”,并非易姓改国,“何必嗫嚅而讳言之!”还通过神宗登极之初祭祀“死事诸臣”来反衬不祀建文帝的缺憾:“而于建文君则否,是有臣可以无君也!”提出:“如以太庙难于议祔,山陵年远难稽,则请别立一庙,岁时享祀如制,或准先科臣万象春议祔主于懿文太子之庙,一体致祭。”尽管声情并茂,但仍打动不了君王之心。(21)直到《熹宗实录》中,仍然记载了儒臣们为建文帝议祀的决心和行动。该录卷6载,天启元年二月庚戌,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称“建文、景泰二帝,未沾庙享,恐列圣会聚之时,必有不安者”。天启四年三月辛巳,欧阳调律上疏奏道:“臣备员南垣,数趋陵庙,及望东陵,爽若有失。夫建文太子庙貌宛然,岁九祭,而建文生为帝王,殁无谥号,既不得入祔太庙,又不得别享一祠,封墓莫识,魂魄安依?”要求廷议后“毅然举行”。熹宗干脆直言“不许”。(22)
四、结语
朱棣及其嫡派子孙主导修纂的《明实录》对于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历史采用了始则歪曲、不敬,继则掩盖、忽视的态度,致使这部明代唯一保存下来的官修国史未能如实记载和反映建文帝的历史。不过,到了晚明,皇权专制开始松懈,儒臣们对建文帝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纂修的《神宗实录》和《熹宗实录》,开始大量记载有关建文帝的历史以及对建文帝历史进行平反的要求和奏疏。这些奏疏从太祖统系和正统史观出发,不断提出对建文帝历史及其年号予以记载和恢复的要求,迫使君主与之达成了部分妥协,同意在修撰纪传体国史时,于太祖本纪后附录建文四年的历史,然而,在全面承认建文年号和历史、建立并举行建文帝祀典上面,仍然受到成祖嫡系君主们的顽固抵制。
晚明的儒臣已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不再像前期那样完全受到君主意志的支配。在儒臣们看来,能够推动建文历史的平反和进行公正的记录,无论成否,都将成为他们一生值得炫耀的骄傲和光荣。如文渊阁大学士沈鲤死后,《神宗实录》特地强调他“于核庙祀,请复建文年号,及罢矿税诸疏,尤其著者”(23),说明当时的士大夫已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念和评价标准,这与革除建文年号的成祖及其子孙们的价值观已大为不同。直到明朝覆灭后,匆忙建立的南明政权才对建文帝锐意改革的精神和建文君臣之间的忠义极其重视,于崇祯十七年七月正式追谥朱允炆为“嗣天章通诚懿渊慕觐见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追赠庙号为惠宗。君主与儒臣在对待建文帝历史的态度上才又趋向一致。不过,从整个晚明来看,由儒臣具体纂修的《明实录》,在记录如何对待建文历史的态度上,显然已偏离君主的航线,倾向于儒臣的立场。这一现象说明,晚明的儒家意识形态与君主专制制度之间,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裂痕。
注释:
①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牛建强:《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反正过程——以明中后期建文朝史籍纂修为视角》,载《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杨艳秋:《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载《炎黄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吴德义:《建文史学编年考》,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③《孝宗实录》卷149,弘治十二年四月乙巳。
④《神宗实录》卷374,万历三十年七月癸未。
⑤《神宗实录》卷463,万历三十七年十月壬申。
⑥《熹宗实录》卷29,天启二年十二月庚寅。
⑦⑧⑨《太宗实录》卷1,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
⑩《神宗实录》卷3,隆庆六年七月辛亥。
(11)《神宗实录》卷30,万历二年十月戊午。
(12)《神宗实录》卷196,万历十六年三月壬辰。
(13)《神宗实录》卷276,万历二十二年八月癸酉。
(14)《神宗实录》卷289,万历二十三年九月庚辰。
(15)《神宗实录》卷289,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乙酉。
(16)有人认为“建文年号在修史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写在史籍中了”,“(万历)中期又恢复了建文年号”(牛建强:《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反正过程——以明中后期建文朝史籍纂修为视角》,载《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这一表述过于乐观,其实建文年号并未全面恢复。郭培贵《建文帝有实录吗》(《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对此已有所察觉,惟未作进一步论述。
(17)《神宗实录》卷463,万历三十七年十月壬申。
(18)《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癸酉。
(19)(22)《熹宗实录》卷40(梁本):天启四年三月辛巳。
(20)李小林:《万历官修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1)《神宗实录》卷475,万历三十八年九月辛亥。
(23)《神宗实录》卷574,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辛丑。
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