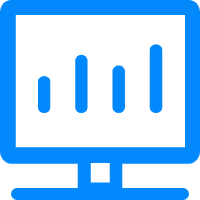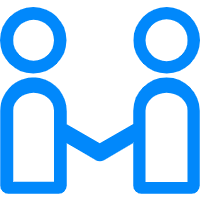向玉琼:走向行动主义:建构风险社会中的政策分析范式
作者:向玉琼,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2期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摘要:政策分析范式是一种政策建构框架,随着社会历史情境变化而变迁。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在工业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后受到后实证主义范式的影响,但政策分析中理性设计的特征并未被削弱,实证主义范式的根基并未动摇。风险社会的到来从根本上质疑了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推动了第三种政策分析范式的生成,那就是行动主义范式。行动主义政策分析范式否定了划界式的分析式政策分析,融合了民主与科学两大主题,综合技术理性与经验知识,强调问题情境与即时行动,重塑制度与行动的关系。总体上说,行动主义从横向知识体系与纵向政策流程两方面对实证主义范式做出批判式发展,主张在合作行动中开展政策分析应对风险社会。
关键词:风险社会;政策分析;实证主义;行动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政策过程中共识构建的政治哲学研究”(20BZZ077)。
范式(paradigm)一词由库恩提出,用以描述自然科学中的知识生产模式,彼得·霍尔(Peter Hall)将范式的概念引入公共政策研究中,强调政策过程中存在的信念和表征,这些信念和表征构成了政策工具的选择,并有助于理解政策变化的动力。[1]之后,政策范式成为政策研究的中心,用以更好地理解政策过程中知识与观念的作用。不过,霍尔只是将范式视为“社会学习”的一种方式,后来霍根(John Hogan)与霍利特(Michael Howlett)对政策范式作出了具体界定:“‘政策范式’是一种理论工具,用于具体说明和理解制定公共政策的指导原则或理念,以及参与其中的各种行为者为何参与其中,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实施他们所采取的战略。”[2]范式与框架(framework)不同,相比于框架,范式具有更为抽象的概念内涵和知识体系。但本文不明确区分政策范式与政策框架,而是将二者都用来指称政策过程中的原则与理念,以及政策建构的认识论和知识生产体系。
人们将现实政策问题纳入认识体系中进行加工得出结果,这种政策建构的过程就是政策分析。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中,政策过程的思维、假设、方法、技术等都全然不同,所得到的政策结果自然也不同。公共政策自20世纪中期成为一门学科之后,长期受到技术理性的主导,后来在政策科学运动中形成了具有典型性的政策分析范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要谈到政策分析,就会与实证主义的思维和方法联系在一起。但由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在现实应用中出现了大量的政策失灵,政策分析被拉回政治和价值的场域,政策范式从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转换。不过,后实证主义并未完全动摇实证主义范式的根基,反而可以看成是对实证主义范式的修正。而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社会问题具有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这推动政策分析范式做出第二次转换。本文认为,这一次转换走向的是行动主义政策分析范式,这也是未来政策分析的发展方向。
一、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及其发展
实证主义政策分析源于逻辑实证主义方法和技术在政策过程中的应用,与工业社会中关于理性和科学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科学主要指称应用于物理学领域中的研究范式,通过分析性思维和实证主义方法来认识社会问题,实证主义成为科学化的具体路径。二战期间兰德公司应用实证主义进行战略分析,到20世纪中期实证主义几乎对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产生了影响,系统分析与成本-收益分析被引入政策过程中,确立起了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
实证主义政策分析基于政策建构主体与政策对象分离的前提假设,强调政策过程中的归纳推理与因果逻辑,将政策过程转变成一个揭示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过程。“科学思维认为主观思维是无效的。科学思维坚持,客观思维是做我们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情的必要过程。其目的是证实世界的连贯性。”[3]政策分析中努力排除主观偏见,通过大量的模型设计与公式推理来模拟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以此生产出具有逻辑合理性的科学成果,这一成果就是公共政策。其中,政策分析运用了分析性思维,对所有政策问题进行分析和分解,政策问题被解剖成为一个个可分析的部分,经过深入而细化的研究之后再将碎片化的认识联合成为整体,由此完成对政策问题的完整认知。通过分类和分析,政策问题与社会背景、历史演进等因素隔离开来,成为可以独立存在并可分离处理的观察对象,也是适合于技术分析的对象。
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政策模型中:效用决策模型和博弈模型。1944年,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发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个体被建模为一个效用最大化的机器,进而效用函数被确立用以分析社会决策,政策过程中出现了正式的数学模型。接着,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其理论发展中分化出两个互相联系但又各具特色的方法论集合,即“多属性效用”(multiattribute utility,MAU)和“成本效用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CBA)。CBA试图用货币来表示人的效用,而MAU是运用与货币毫无关系的效用单位,也就是社会效用的总和。这两种方法都将多维度简化到效用这个单一维度上,并通过数字表达出来,这就出现了雷加诺所看到的,“无论如何,这一同时涵盖了MAU和CBA的分支从本质上都以数字或基数表达个人的效用,使得我们可以将效用相加(或者采用其他的运算方式)从而得出一个集体答案”[4]。基于货币这一载体或者一元化的社会效用,人能对自身利益进行计算进而进行效用排序,政策结果也通过效用结果的最大化来决定。效用决策模型的另外一个分支也起源于个体效用最大化模型,但是不包含基数效用的概念,其表现形式不是数值,而是简单的排序。在面对可选项时,决策者往往不会为可选项赋值,而是通过对选项排序来做出选择,如投票就是人们表现序数的一种方式。这时决策方案没有对应的数值,只有序数,但是序数对偏好的表现力更强,也更易于计算和选择。
效用无论是以数值还是序数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都是通过计算得出结果进而成为政策选择,这一过程被概括为理性决策模型。理性决策模型假定决策过程的完全理性,决策行为追求整体效用的最大化。“人们用备选方案及其结果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与此相似,人们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也通常会想象出一组期望和偏好以使他人的行为理性化。”[5]在理性决策模型中,无论是社会价值、善、社会福利函数,还是目标规划等等,都被转化为统一的计算符号并进行加工,决策所关注的是偏好的最大化满足,决策结果因此具有最优解和唯一性。这正好符合了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思想的创始人边沁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效用。在边沁看来,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可归于效用,效用具有可计算性与可通约性的特征,通过效用的概念可以将政策问题的多面向统一起来,简化为单一维度。继而,政策过程就只需对效用进行计算,然后根据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结果主义导向,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作为政策选择。尽管20世纪30年代时梅里亚姆就一直强调政策问题的现实性,其学生拉斯韦尔也呼吁政策过程的民主化维度,但政策过程仍然深受技术理性的影响,政策分析的目标就是将不稳定的、意识驱动的和纷争的政治世界带入理性的、科学的知识统治之下。康德的道德推理被边沁的测量运算所代替,绝对主义道德命令被结果主义取代,数学思维主宰了决策过程。
博弈论在效用决策模型基础上将约化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将理性选择在个体层面表现出来。博弈论几乎完全继承了决策理论中的基本假设,如决策主体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决策方案都可以通过赋值来表现优劣并实现排序,社会政策是在多个选项中进行效用测算的结果,等等。“古典的‘经济人’和现代形式化的决策论与博弈论中的理性人,都是在有严格限制和明确界定的情境中,作出最优的选择。理性要求在这些限制与情境下,行为体本质上如霍布斯式般无情地追求价值最大化、进行一致的测算(reckoning)或调整。”[6]理性经济人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追求产出的最大化,或者在产出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投入的最小化,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则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但是,与效用决策模型不同的是,博弈论认为决策结果应当考虑个体的行动选择,而一旦考虑个人行动,则可能出现个体理性无法带来集体理性的结果。也就是说,社会选择的均衡结果并不总是并且往往不是社会效用最大化的那个选项,其中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都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在实际应用中,博弈论不适用于处理真实情境中的政策问题,也很少用于建构或者解决现实问题,更多的是根据抽象的假设和模型来检验决策选择,博弈论在政策话语中的影响主要是为一定的模型或者方向进行合理性论证。“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政策话语中,博弈理论被用来抽象地合理化既有政策,而并非一个应用于实际情形的实践模型。”[7]
无论是效用决策模型还是博弈论都假定现实问题可以而且应该被纳入一个既定的认识论框架中来进行加工并得出结论,都将计算结果最大化的方案作为政策产出。所不同的是,效用决策模型塑造出了一个更为纯粹、更为理想化的决策情境,认为政策就是社会效用最大化的选项,而博弈模型考虑到了偏好的易变性以及个体选择行为的复杂性,认为个体选择并不一定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不过,两种模型都贯穿着实证主义逻辑与分析性思维,只是在具体实施方案上存在差异。多元模型的兴起代表着实证主义的演进和发展,使得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更具有解释力和适应性。
但即使在理性决策模型受到大力吹捧时,也有着批判的声音。不过,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策科学运动的兴起,继而在“向贫困宣战”、建设“伟大社会”以及越南战争中出现政策失灵,才推动了对实证主义政策范式的全面反思,继而追溯到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上。实证主义范式将政策过程设定为科学过程,“政策科学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受客观主义理想的驱使,将决策问题的结果简化为无结构的群体,以某种或多或少的质量来表达替代行动方案的结果,其中明确确立了可通约性标准。此外,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简化主义方法在我们的思想传统中是多么普遍,以及对某些结构特征或不连续假定是多么不可接受”[8]。政策问题与社会政治背景紧密相关,无法将其剥离开来并表现在可计算可独立的符号上,因此政策问题也不能限定在科学范式内进行建构。博弈论在强调个体理性选择行为时,也显示出个体偏好、道德准则、社会目标、历史因素等对决策行为的重要影响,这表明复杂的政策问题并不能化约为统一的符号系统,政策目标也不能限于单一的最优或者最大。相反,博弈论的发展也表明,政策分析中应当降低实证数据的绝对性和严格性要求,综合道德、偏好、价值等多重因素,这为政策分析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向做好了铺垫。
二、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的修正
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思潮整体从实证主义转向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也出现了第一次转换,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转向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不过,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并未提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假设,其观点是在对实证主义分析框架进行批判的同时做出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做出了修正。
第一,从人文解释学派出发认为政策意义是社会建构的。实证主义分析运用规范的科学方法、统一的概念体系、严格的因果推理以及标准化的流程开展政策分析,这被看成是现代性与科学性的体现。而基于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发展起来的解释学则从根本上解构了统一性、标准化以及权威主义的假设。索绪尔通过符号概念的引入,提出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确定性。在索绪尔看来,任何符号的意义都会随着不同的符号系统而发生变化,因此符号的所指是流动的或者是随意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索绪尔的这一观念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发展,针对当时备受拥护的逻辑主义,维特根斯坦提出,所有的知识都只是一种语言游戏,意义的来源是随意的,需要结合当时的情境来加以解释。如此一来,政策以及政策方案作为一种文本或者符号,其意义也是不固定的。这就意味着政策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所有的政策方案都需要对符号进行意义界定,政策方案都是社会建构起来的,并且同等的有效。
第二,从法兰克福学派出发批判政策过程中的工具理性。缘起于早期马克思学派和韦伯,法兰克福学派承继了关于人的异化的观点,全面批判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将政策分析的视角转移到结构与关系层面,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根本性问题。只要社会中存在支配-依附的关系,政策过程的参与机会与参与分量上就不会是平等的,整个政策流程也必然是单向度的和控制导向的。其中使用的技术和方法在本质上都只具有工具理性,政策过程失去了价值与关怀,无法使人实现真正的解放。“科学直接导致了控制,而不是解放所需要的自我反思。这一趋势又强化了技术决定论的意识及其决定性的社会效果。”[9]因此,政策过程应当从结构上来做出根本性的转变。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动理论,以交往理性来挑战西方的技术理性中心主义,以此批判资本主义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交往行动理论推动了商谈伦理和商谈政治的出现,提出通过商谈来重振民主,通过民主来解构单向度的技术和控制,这也推动了政策过程中的民主化转向。
第三,倡导政策过程中伦理和价值的“复魅”。政策科学运动的兴起模糊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的边界,同时新公共行政学派明确提出跨越政治-行政二分框架,在行政过程中注入民主和价值,由此可以推论,政策过程无论是在哪一阶段,在关注科学的同时都不能忽视价值。不过,对功利主义冲击最大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功利主义强调结果主义和总和排序,将个人权利仅仅理解为选票或者数值,罗尔斯认为这忽视甚至是有意排斥了个人偏好和具体诉求,使得个人权利的实现流于形式。罗尔斯重申契约正义的观念,通过无知之幕的提出以及优先原则的确定,将政策过程转到协商与合作的层面上来。在罗尔斯看来,个体一旦具有理性就必然是偏私的,因此应当通过制度的设计如“无知之幕”的设立来消除个人私利追求对制度正义的影响。罗尔斯强调制度对交换关系和有序竞争的保障作用,不仅如此,当竞争带来不平等和差异扩大时,制度还会实施分配功能来缩小社会差距。罗尔斯所持的是“公平的正义”观,强调通过制度途径来保障工业社会中的个体权利,实现政策过程中的公平与平等,以此实现政策正义。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社会选择中价值的回归,政策分析从技术路径转向价值层面,在其之后,阿玛蒂亚·森、麦金太尔、纳斯鲍姆等学者纷纷对罗尔斯的正义论进行了扩展和补充,如森论证了能力对于正义实现的重要性,而纳斯鲍姆将森的能力理论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正义领域,进一步阐释正义与美德,倡导价值回归,构成了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面向。
第四,用经验知识补充政策分析中的专业知识。受到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教育学认为在知识获取与传授中要从重视理性知识转向重视经验知识和实践知识,这扩展了实证主义范式对知识的狭隘理解。实证主义强调知识和方法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所获得的知识都是通过系统学习与专业训练来获得,而在杜威看来,“不管一个人的知识有多么的丰富,所受的训练有多么的专业,他对新科目的理解或对旧科目中新的内容的理解,都必须通过直接体现这种存在或这种性质的活动来完成”[10]。知识不能仅仅来自于头脑中的理论连接和方法复制,而是必然来自于实践和经验。只有经验才能将人们的知识整合起来,才能使得理论认知具有现实意义。“经验哪怕只有一两,也胜过一吨的理论,实在是因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在经验中才有生命,有可核实的意义。一个经验,一个很卑微的经验,可能产生并且承载无限量的理论(或智能要义)。一个理论若是离了经验,甚至不确定仍可成立为理论。它可能变成只是文字公式,只是一组口头禅,有了它,思考或真正的理论说明成为不必要与不可能了。”[11]继而,皮亚杰将弗洛伊德那种相对随意的、缺乏系统性的临床观察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认为人的智力是一种适应形式,是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的认识是建构出来的,认识的心理发生是在动作和实践中产生。[12]对经验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强调也对政策分析中的专业主义提出了挑战,政策过程被导向社会性与实践性的方向。
总体来看,后实证主义否定了政策问题的客观性假设并对政策分析中的技术理性提出质疑,从不同维度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将被实证主义所排斥的情境与经验重新拉回政策过程中。但是,后实证主义政策范式对实证主义做出的纠偏具有矫枉过正之嫌,其对客观性与技术理性的否定使其陷入了相对主义的一端,也给自身招来了诸多批评。“理性主义的方法至少能回答这个领域的基本问题。后实证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后实证主义形成的答案与观点和看法一样多,所有这些观点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有效性。理性主义者认为,这根本不是答案,只是政治混乱的放大。”[13]对技术理性的否定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答案,相反,政策过程中的技术理性追求是有其合理性的,政策过程不可能完全放弃技术理性。“在政策分析和规划中争论的转向并不是以科学为代价的,更不是以理性为代价的,而是以人类事务中对科学和理性不必要的狭隘误解为代价的。”[14]正因如此,后实证主义的发展只是缓和了政策分析中对技术理性的极端追求,但并没有动摇实证主义的根基。相反,后实证主义所做出的纠偏在一定程度上警醒了实证主义范式,推动其有意识地纳入价值和社会因素而避免偏狭和封闭,实证主义因此而得到修正和完善,其地位反而得到巩固。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政策分析中的技术工具得到优化,政策分析的技术合理性再次突显出来,人们越发依赖技术分析来应对社会风险。到21世纪初,费希尔看到,“理性选择,尤其是从经济学中借鉴或实践的,显然是占优势的。它现在是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中最流行的理论取向之一”[15]。理性选择理论仍然得到广泛应用,这意味着实证主义在现实的政策分析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走向行动主义政策分析范式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整体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就是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也有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自反性现代性等多种表达。相比于工业社会中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低的状态,风险社会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中个性化与差异化因素突显出来,无法被简化和统一,这就打破了标准化的符号表达系统,政策问题表现出多元且凌乱的一面。另外,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因素都处于高速流动的状态中,不断发展和变迁,同时彼此关联形成高度复杂的网络和联结。社会网络所牵涉的因素众多,任何环节的断裂都可能影响到整个网络,每个节点都可能引发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政策问题因此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
风险社会成为新的政策背景,推动了对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的全方位解构。虽然实证主义内部有不同的分支,观点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出现了演进与调整,但总体来看,实证主义仍然遵循着固定的思维和规范的程序,坚守着技术理性的优越性与排他性,实证主义主导下的政策分析是在科学范式内部开展,基于制度所划定的有形和无形的边界和程序来做出行动。而风险社会的到来挑战了实证主义范式的合理性。实证主义囿于技术路径对政策问题做出界定,但高度复杂性的政策问题并非一个明确的客观存在,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数值化的对象,也不能在技术路径上做出有效应对。“把社会背景和意义排除在技术风险分析角度之外提供了一种抽象性,它提高了结果在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有效性,但却以忽视风险的社会过程为代价。”[16]技术工具的发展与分析性思维的完善都只是在技术路径上的优化,而不能对社会风险做出全面表达与建构。实证主义范式遵循对事物化繁为简的原则,但高度复杂性的政策问题却超出了技术所能化简的范围,或者说根本无从化简了。“这种复杂性排除了政策过程的‘一般理论’;任何理论都只抓住了多方面背景的一个方面。它排除了任何可能从一个价值取向提供建议的单一政策分析工具。它排除了过分简化的个人模型,这些模型忽略了情感的作用、启发式的功能和人类思维的复杂性。”[17]实证主义范式所做出的标准化的政策建构都失效了,制度化的与常规化的政策分析范式需要做出根本性的转换,即转向行动主义政策分析范式。
行动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拉图尔等人为解决科学哲学或知识社会学的问题而对传统科学范式的知识学科提出挑战,“他们认为科学自身如何作为一个社会构成物,受制于传统、共识与偏见”[18]。这种观点认为科学与社会无法分割,而是逐渐融合,这推动人们对主客体分离的认识框架、科学的边界、理性与非理性的界定等问题做出反思。反思的结果是,既定的结构与边界都不存在,科学并不存在于真空中,也不具有相对于其他知识的优越性,因此政策过程并不能在封闭系统中开展。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的社会背景下,政策分析不再遵循既定的结构和制度,不再遵循所设定的程序和规则,高度不确定性的存在解构了一切设定和边界。结构对行动的规范意义减弱,行动逐渐摆脱了结构的单向束缚而反过来对结构做出修正。行动主义是相对于制度主义而言,但由于实证主义注重标准化程序与规则因而具有了典型的制度主义特征,为了突出政策分析中对形式规则的突破,本文直接用行动主义的概念去指称这种新的政策范式。当科学与社会无法分割、行动与结构彼此互构时,实证主义所设定的边界和规范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政策分析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了。行动主义政策分析范式不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但更注重政策问题与方案的社会建构性;不否认技术理性的合理性,但也看到其片面性;不否认制度与规范的重要性,但否定单向度的流程和控制。总体来看,行动主义突破了固定的结构和边界,强调融合、包容、灵活与互构。
第一,在价值上融合民主与科学两大主题。拉图尔以TRF(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为个案,通过对实验室的观察发现,即使是在实验室里的所谓事实也是制造出来的,是将事实脱离了时空情境而视为历史从而成为事实。“客体只有作为两种记录材料的差异时才存在。客体无非是一种信号,它能区分领域内一般的背景噪音和仪器所发出的噪音。更重要的事实是,提取信号并承认它的特性,取决于为拥有稳定的鉴定基础所应用的重要的和费用大的程序。”[19]拉图尔认为,科学实验过程中应该避免使用这样的表述:“物质是借助生物鉴定被发现的”,或“物体产生于对两个峰值之间差异的确定已被证实”。“使用这样的表述无异于传递错误的印象即某些物是先验地存在的,它们只等待科学家把它们的存在揭示出来。”但是,实验室的推断的逻辑不能离开它的社会学根据。同样,行动主义政策分析并不否定科学路径,只是不再将科学等同于实验室封闭环境中的技术发明,而是将科学置于民主化场景中,在民主路径中实现科学。行动主义看到,人的认知无法发生在主-客体分离的框架中,技术路径始终与社会背景相关,政策主体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策对象,因此政策分析发生在政策主体与政策对象的互动中,也只有在互动与协商中才能实现科学的政策分析。
第二,在知识上综合技术理性与经验知识。行动主义分析框架认为,经验对于人的认知是必不可少的。政策认知一面朝向自然,将认知过程视为科学发现过程,另一面朝向人类世界,也就是现象学所界定的“生活世界”,在这一意义上认知可以被视为经验。这也就是说,政策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技术和工具,运用各种先进技术工具来提升政策效能,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技术的局限性,基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知识来对科学认知作出补充。实际上,人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经验中,科学也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当要研究认知或心智本身的时候,不考虑经验就显得站不住脚了,甚至是悖谬的。”[20]相比于后实证主义对实证主义的修正,行动主义分析框架更积极地倡导技术理性与经验知识的融合,理性的政策设计与情境性的政策试验的结合,重视常识、想象、直觉等之前被认为是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实现政策分析中多元模型、多重知识、多元体验的共同作用。这也可看成政策分析的实践视角,“政策分析的实践视角不仅意味着一个层面的变化(微观与宏观)或分析方向(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而且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是,在对待政治参与者、官员、行政人员以及通过自身行动和兴趣来填充公共生活的公民时分析焦点的类似变化。政策分析的实践视角改造了传统的分析对象——政策制定、实施和政策效果。正如我们所说的,实践不仅是工具性的,甚至是务实的。相反,它总是需要一个综合的判断,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客观的和个人的”[21]。实践导向强调将政策分析置于现实的真实背景中,将政策还原为具体的场景,这一场景是具体而真实的,充满了个体之间的互动与反思,因此,政策分析也应基于技术理性与经验理性的完整认知来做出。
第三,在流程上强调问题情境与即时行动。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注重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希望将现实问题纳入科学范畴之中进行分析和处理,将社会问题清晰化、简单化,但是,风险社会中政策问题是在特定时空中发生的,具有强烈的社会情境性,具有突发性与不可预见性,这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失效了。风险社会中的高速流动与快速变迁对决策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时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影响因素和变量,也不可能先交付技术专家或者政治精英进行分析之后再进行执行,固定的分工和流程都会带来政策的时滞,因此,政策分析应发生于具体的、即时的行动中。“风险社会中的决策是在行动中发生的,可以理解为决策与执行的一体化。”[22]行动主义政策分析超越了线性的政策流程以及任何制度设计和规范,超越了决策与执行等不同阶段的划分,超越了决策过程中集权与分权的争论,而是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开展政策分析。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都可以成为政策分析的行动主体,这一行动不局限于事先的安排或者设计,完全依托于事情的当时状态而开展分析。政策分析摆脱了组织与结构的限制,从抽象原则的王国中走下来,体现在灵活性与弹性化的行动上。
第四,在结构上重塑制度与行动的关系。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都是强调结构、制度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性,强调政策分析中各种规范、程序和步骤的合理性,而行动主义否定了政策分析中制度主义的假设,将行动从制度规范中解放出来。“如果说新制度主义(对制度主义)的反思是回溯性的,那么行动主义的反思则是重构性的。”[23]行动主义认为行动并不是受到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行动与制度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因此可以摆脱制度的束缚来进行政策分析。“行动主义承认制度之于行动的规范效力,因而不能完全脱离制度而盲目行动。但更为重要的是,行动主义主张行动对于制度的建构权,认为任何制度都需要接受行动的建构与重构,要求把制度放在行动中去认识、理解和加以检验。”[24]在制度主义框架中只存在受到制度约束的“行为”,“行为”是在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模式下开展,是与主客体分离的认识结构相适应的一种行动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发现作为真理存在的客观问题,其中所运用的叙述、分类、抽象、设计与规划,都是科学范式中的手段而已。行动则对应于具有自主性的组织,是摆脱了等级结构与框架束缚之后作为自主的行动者所开展的思考与判断。制度依然存在,但转化为行动中的理性信念,成为支持行动开展的平台。行动是面对具体问题时所做出的即时反应,是对真实的问题和差异表达的关怀和尊重,行动会对制度进行建构,持续的行动会转化为制度存在。
四、政策分析范式的发展
行动主义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实证主义范式做出了批判与修正。
第一,在横向知识体系上,行动主义强调通过协商对理性知识做出补充,这推动了政策分析的民主化。人们重新审视理性的概念,发现科学不应自成一个权威系统并终结其他的话语体系,而只是众多理性解释体系中的一种。“人们希望通过技术的推动来更好地回应生活问题,但却发现,科学化与技术化成了公共政策与具体生活隔离开来的另一道屏障。”[25]政策过程不应受到技术理性的垄断,相反,为了寻求意义,政策只能是社会建构的。这样,政策过程从强调科学性与技术性的理性决策模型中被拉开,多元政策模型出现。如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模型将政策过程拉回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认为任何问题都包含着技术分析所无法包容的因素,“除非考虑任何社会冲突中的价值或利益,否则这些问题就不能得到全部解决。解决问题需要的与其说是分析,而不如说是政治”[26]。政策评估中不再无视主体的存在,不强调评估者与被评估者之间的边界与距离,而是认为评估结果是在评估者与评估对象之间的互动结果。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推动了协商民主的兴起,以此推翻技术专家主导、技术工具垄断、理性逻辑主宰的政策过程,民主的议题复兴并推动政策分析的开放性。到20世纪90年代,费希尔明确提出政策分析中的论证转向(argumentative turn),德雷泽克、施耐德和英格兰姆等提出审议性政策分析(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亚诺(Yannow)等提出诠释性政策分析(interpretative policy analysis),雷恩、斯密特等提出批判式政策分析(value-critical policy analysis),德利翁、托格森等提出参与性政策分析(participatory policy analysis),哈杰尔等提出协商式政策分析(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倡导政策分析中的民主价值。雷加诺的后建构主义政策分析将政策视为文本,而文本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其中的分析任务就是理解意义是如何建构的以及何种意义在公共领域中有显著性。政策过程中不再强调绝对性,而应当是在特定情境之下的或者相机行动的“绝对性”。[27]哈基宁等提出叙述性政策分析作为对传统政策分析的替代路径,寻找基于共识与共同基础的政策建构方式。[28]这些观点和概念的出现都强调了政策分析的政治性与社会性,在政策分析中补充了经验性与实践性的内容,推动了政策知识的包容性发展。
第二,在纵向政策流程中,行动主义弱化了政策分析的设计导向与阶段划分,强调政策分析中的行动调适和阶段延展。政策阶段论可以看成是理性主义应用的产物,强调政策阶段之间的顺序、政策过程的线性流程、专家话语、阶段之间的分界,以及政策系统与社会背景之间的边界。政策阶段论将政策分析分阶段、分步骤地分割开来,政策过程因此变得清晰而明确。但萨巴蒂尔认为,现实中政策分析并不遵循严格的阶段论,并总结了对政策阶段论的六个非常具体的抱怨[29]。政策阶段论体现出了设计导向,而行动主义政策分析强调政策分析中的学习与延展。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如萨巴蒂尔和詹金斯的倡导联盟框架(ACF,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以及韦布尔的资源依赖理论(RDT,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30],二者都致力于解释政策子系统中的政策变迁,前者认为多元主体形成的政策信仰的变化会推动政策变迁的发生,后者认为政策过程中往往是在行动者的相互依赖和合作中推动政策变迁。这些观点都可以纳入行动主义的框架,政策过程是在具体行动中不断延展。政策分析不只停留在政策制定阶段,或者说,行动主义直接忽视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分界,认为政策分析发生在政策全过程中。决策者总是根据他们对情境和经验的解释,来预测当前行为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结果继而决定如何行动,也就是说,决策者的行动都是相机而动的。“通常很难描述决策的历史。当(甚至是否)做出一个决策时,谁做出的决策、决策的意图是什么、决策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都不清楚。许多决策都是在对方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过程通常会讨论问题但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决策不是在明确的决策过程中做出的,决策过程通常也无法做出决策。”[31]在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政策分析更不可能在政策制定阶段完成,而是在执行中不断学习和调适,这也是行动概念本身的意义所在。
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实证主义政策分析发展到后实证主义的修正和纠偏,再到行动主义政策分析范式,其中经历了两次范式转换。范式转换受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程度提高的推动。工业社会中政策问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低,基于技术理性主导的政策分析能够对政策问题做出清晰化表达和简单化处理,由此形成了标准化的、模式化的政策分析框架。而在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实证主义政策分析屡屡带来政策失灵,致力于划界与分类的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失效了。基于后实证主义所带来的知识基础,结合新的社会情境的推动,政策分析范式转向行动主义。行动主义从横向知识体系与纵向流程设计方面对实证主义做出批判式发展,具体体现为知识的开放性与流程的灵活性。行动主义政策分析表现为包容、灵活、弹性与延展,最终落脚到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行动上,也可以认为,行动主义政策分析范式是一种合作范式。
向上滑动阅览〔参考文献〕
[1]Peter A. Hall,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5, No.3, 1993.
[2]John Hogan and Michael Howlett, Reflections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Paradigms and Policy Change, in John Hogan & Michael Howlett, Policy Paradigm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algrave Macmilan, 2015, p3.
[3][美]拉尔夫·P.赫梅尔:《官僚经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韩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4][美]劳尔·雷加诺:《政策分析框架——融合文本与语境》,周靖婕、刘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5][7][31][美]詹姆斯·马奇:《决策是如何产生的》,王元歌、章爱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129页。
[6][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王伟光、王云萍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7页。
[8]Laurence H. Tribe, Policy Science: Analysis or Ideology? Philosophy &Public Affairs, 1972, vol.2, No.1, pp66-110.
[9]戴黍、牛美丽等编译:《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10][美]约翰·杜威:《我们如何思维》,杨韶刚、刘建金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
[11][美]约翰·杜威:《民主与教育》,薛绚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132页。
[12]Jean Piaget,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court, 1929.
[13]Kevin B. Smith & Christopher W.Larimer, The Public Policy Theory Primer, Westview Press,2009, p103.
[14]Frank Fischer and John Forester, The Argumentative Turn in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p213.
[15][21]Maarten Hajer and Hendrik Wagenaar, 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10,167.
[16][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英]多米尼克·戈尔丁编著:《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7]Paul Cairney, Christopher Weible, The New Policy Sciences: Combining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Choice, Multiple Theories of Context, and Basic and Applied Analysis, Policy Sciences, 2017,50(4).
[18]Raul P.Lejano, Frameworks for Policy Analysis: Merging Text and Context, Routledge, 2006, p89.
[19][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张伯霖、刁小英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20][智]F.瓦雷拉、[加]E.汤普森、[美]E.罗施:《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李恒威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22]张康之:《论风险社会中的决策》,《行政论坛》,2020年第4期。
[23]柳亦博、玛尔哈巴·肖开提:《论行动主义治理——一种新的集体行动进路》,《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期。
[24]张乾友:《行动主义:合作治理的神髓——兼评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河北学刊》,2017年第3期。
[25]向玉琼:《从生活出发:复杂条件下的公共政策建构逻辑》,《学海》,2020年第6期。
[26][美]查尔斯·E.林布隆:《政策制定过程》,朱国斌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27]Raul P.Lejano, Frameworks for Policy Analysis: Merging Text and Context, Routledge, 2006, p144.
[28]Hukkinen, Emery Roe, and Gene I. Rochlin. A Salt on the Land: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Irrigation-Related Salinity and Toxicity in California’s San Joaquin Valley. Policy Sciences, 1990, 23 (4): 307.
[29][美]保罗·A. 萨巴蒂尔、汉克·C. 詹金斯-史密斯:《政策变迁与学习:一种倡议联盟途径》,邓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30]Christopher Weible, Beliefs and Perceived Influence in a Natural Resource Conflict: An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 to Policy Network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5, 58 (3): 461.
〖JY〗责任编辑:陈琳〖HT〗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数字经济智库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