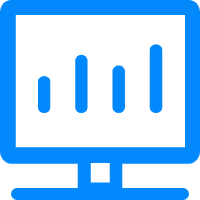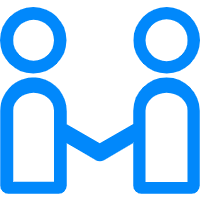2015年3月20日,为纪念次日的“世界诗歌日”,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发行了一套六枚邮票——每枚邮票上都用对应的母语印一首名诗——包括中、英、法、俄文和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李白的《静夜思》被作为汉语诗歌的代表印在了其中一枚上。
这则花絮,遥远地呼应着1975年版美国大百科全书的“李白”词条:“李白与杜甫是被世界公认的产生于中国的伟大诗人。”也有外国学者称“李白诗歌是人类的心声”。李白诗作自1830年代开始被介绍给西方读者,但直到2020年,英语世界近两百年才出现了关于李白的第一部完整传记——由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华裔作家哈金写作的The Banished Immortal:A Life of Li Bai,书中哈金首次完整地串联和重述了李白传奇的生命历程:童年入蜀、青年出蜀,两次婚姻,壮年干谒,老年流放,客死他乡……
李白诗作自1830年代开始被介绍给西方读者。1915年,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根据东方学学者芬诺洛萨(Fenollosa)在日本学习中国古诗的英文笔记遗稿,整理和译出了《华夏集》(Cathay),其中收录的李白《长干行》译作由此成为现代英文诗歌的杰作。1950年,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撰著的《李白的诗歌与事业:701—762年》(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po, 701—762 A.D.)出版。1981年,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专书《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出版,35年后他译出了6卷本的杜甫诗全集。
然而,英语世界近两百年来并无一部完整的李白传记。2020年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引进和推出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华裔作家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传》,该书译自神殿出版社(Pantheon)2019年初的英文版The Banished Immortal:A Life of Li Bai,哈金首次完整地串联和重述了李白传奇的生命历程:童年入蜀、青年出蜀、两次婚姻、壮年干谒、老年流放、客死他乡……
Ha Jin:The Banished Immortal—A Life of Li Bai,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2019.
哈金:《通天之路:李白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哈金1985年赴美国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攻读研究生,在1993年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前3年即开始正式用英文写作,三十年间累计出版了4部诗集、4部短篇小说集、8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论文集,其中,《好兵》(Ocean of Words, 1996)与《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 1997)分获海明威奖和奥康纳奖,《等待》(Waiting, 1999)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战废品》(War Trash, 2004)再获福克纳奖并入围普利策奖。“在英语世界中,写不出新书,你就不是作家了。”哈金的作品迄今累计被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的文字,与这些等身作品相比,《通天之路:李白传》颇为独特,与哈金作为讲席教授在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学部教授的“小说创作”与“迁徙文学”也关系不大,它以非虚构写法为主,也借助文学化手法和适当的推演想象。
继哈金2014年和2016年两部近作的翻译合作之后,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系讲师汤秋妍再次受邀翻译《通天之路:李白传》,她说最为费时费力的是书中大量专有名词的查找和确定,“我个人认为这部传记翻译回中文的意义,就是让对此感兴趣的人可以了解李白在英语世界中如何‘被介绍’,同时里面有哈金老师自己对李白人生的理解”。在汤秋妍看来,作者试图写出李白的两个“通天”追求:一是政治上的“通天”追求:去皇宫、佐明主,当皇帝身边的重臣;二是宗教上的“通天”追求,即“得道成仙”,“但这两个追求因为种种原因都失败了。最后,李白只留下了一些作品,还有一种人格形象,这个人格形象让我蛮感动”,“不管李白个性上可能有多少缺陷,比如酗酒而不靠谱、狂妄、太过天真,也不管他人生多么失败(除了成就了诗名,那两个‘通天’理想都落空了),但至少有一个‘尊严’(dignified manner)似乎是李白一直要维护并且可以说是维护住了的。这对当代的人生或许还有意义:不管生活多难,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尊严;不管理想多荒谬,要有理想;要为人真诚,要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2020年5月中上旬,笔者通过电子邮件书面专访了哈金。此外,本专访写作参阅了2019年10月号《北京文学》由该刊副主编师力斌先生撰写的“本刊特稿”编者按,赵雪芹、汤秋妍二女士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燕舞
喜欢比较老一点的细致磅礴、流畅又透彻的传记
燕舞:这个春天波士顿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很严重,您和家人是怎么应对的?
哈金:都居家隔离一个多月了,马萨诸塞州说是就要解禁了。两个月来教课全在网上进行,学生都待在家里。我太太免疫力太弱,出去购物、办事都由我来做。我现在担心今年招收的国际研究生拿不到签证,无法来入学。
燕舞:去国外多年,您是否听说过故乡东北的一批青年作家如今在国内走红,甚至被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
哈金:听说过双雪涛和班宇等年轻作家,但这里只有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有国内的文学期刊和新出版的中文书。我住在乡下,一般不去那里。三年前见过双雪涛,但没能多谈,人很多,当时我的状态也不太好。
燕舞:过去四十年您比较推崇的中外传记有哪些?
哈金:我喜欢比较老一点的传记,比如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写的《乔伊斯传》,还有厄尼斯特·西蒙斯(Ernest Simmons)写的《契诃夫传》和《托尔斯泰传》。他们都是大学者,传记写得细致磅礴。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写的纳博科夫的夫人的传记《薇拉》也很精彩,流畅又透彻。
燕舞:在Shambhala出版社2015年夏向您约稿中华人物的微型传记时,您最初报的传主候选名单中除了李白还有杜甫、孙中山、鲁迅等十余人,在王德威教授主编的《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您也受邀撰写了关于鲁迅的章节,孙中山、鲁迅各自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哈金:当时Shambhala要的只是很小的介绍性传记,每本才12000字,类似一篇长文,所以我并没多考虑,只给了一个名单。
燕舞:国内有媒体给您贴标签“继林语堂之后,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华语作家”,而1940年代末在纽约和伦敦出版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成为了解林语堂上世纪30、40年代在英语世界推介中国文化绕不开的一项工作,您怎么看林语堂?
苏东坡58岁时书录过李白佚诗并编成《李白仙诗帖》。在林语堂的英译实践中,苏东坡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一个诗人典范,也是历代文人从政的一个样本,那您试图呈现和“输出”一个怎样的李白?
哈金:我跟林语堂不同。他自认为是文化大使,他的主要成就是他的介绍中华文化的文章和图书。苏东坡是林语堂心目中的英雄,1936年赴美时他就带了大量的资料,要为苏东坡立传。在他之前,汉语和英语中都没有东坡传,他的工作是开拓性的。而我写李白传只是权宜之作——太太病了,我无法写长篇,就写了这样一本书。
燕舞:《苏东坡传》最末一段里,林语堂总结“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的遗产时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那么,李白“万古不朽”的又是什么呢?
国内两年前引进了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副教授杨治宜的《“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Dialectics of Spontaneity: The Aesthetics and Ethics of Su Shi (1037—1101) in Poetry),她认为,苏轼文学的价值体现在对于自然的“自我否定”式的追寻中。李白呢?
哈金:他们是从理念方面来衡量诗人,而我以语言来衡量,所以,李白是更大的诗人,他丰富了汉语,我们的语言中仍能听到他的语声。
燕舞:代后记中,与“写作”并置的关键词是“生存”,您强调新书写作缘起“是与我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存状态相关的”,尊夫人前几年生病确实是您家的一个大事件,但您毕竟已经是名作家了,与1990年代初来乍到美国并艰难融入本地社群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何以还使用“生存危机”这样的严重措辞?
哈金:有许多知名作家都不存在了,都是“青春之歌”,虽然人还活着。在英语世界中,写不出新书,你就不是作家了。这跟国内不太一样,没有“一本书主义”的说法,不能吃老本。我如果不出书,连我的学生很快都会瞧不起我。
“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燕舞:最新人教版1—6年级统编《语文》教材中共收录了112首古诗词,其中李白的代表作就有9首。您1990年代初出道是以诗歌开始的——第一首英语诗《死兵的独白》刊发于《巴黎评论》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您的首部英语诗集《沉默之间》(Between Silences),作为一个“50后”的现代诗的创作者,您如今对1960年代初期辽宁金州童年时期的小学古诗词教育还有印象吗?
您的儿子Wen也像您当年那样背过唐诗吗?
哈金:我对金州有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大连和我家所住的那个小镇亮甲店。我是上世纪70年代前期在部队里服役时开始接触李白的诗的。一位在黑龙江的老教师退休后要回上海养老,卖给我父母两袋课本和图书。其中有《唐诗三百首》,当时反复读过那些诗,也背了一些。
我儿子对诗不感兴趣。他的博士学位是历史,他读了许多书,多跟他的专业有关。与大多数华裔移民的孩子们一样,他能听懂也能说基本的汉语,但读写不行。
燕舞:新书的主要参考书目只列了8种:李长之先生的《李白传》(东方出版社,2010年)其实是将他1940年香港商务版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1951年北京三联版《李白》两本著作合二为一,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初版早在1971年就出版了,《李白评传》和《李白传》所代表的汉语李白传记“两极”的作者周勋初、安旗都是1920年代生人;亚瑟·韦利的《李白的诗歌与事业》和宇文所安的《盛唐诗》两部英文专著分别出版于1950年和1981年。可以说,您援引的这些中外文著述成果相对较早(文中的少量页下注则主要涉及传主身世与婚恋等方面的论文),您是觉得这些文献资料对于您撰写李白传来说已经够用了?
像程千帆、周勋初二先生的弟子、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莫砺锋和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陈尚君,这批与您算是同代人的当下顶尖唐宋文学研究专家,您却并没有援引他们的研究成果。
哈金:我比较注重专题论文,而不光是名家的专著。《中国李白研究》对我帮助很大,这套年刊集中了国内李白研究的最新成就,其中的每一篇论文都是专门研讨某个专题。另外,我这本传记主要不是给学者读的。一开始神殿出版社的编辑就强调不要“学术著作”,我故意往学术方面偏移,希望它在学术上也能站住。
燕舞:众多版本的李白年表中,对您帮助较大的是詹锳先生的?
哈金:我手头有五六个李白年表,差异不是很大。詹锳先生的年表主要在讨论李白女儿平阳时给了我帮助。
燕舞:您将新作定位于“非虚构”,尽量避免“李白学”大家安旗的《李白传》那种“像小说,一大半是对话”的写法,但您又“更注重有趣的细节,希望通过连接和描述它们,能勾画出一个完整鲜活的李白”,在细节的选用和文学化的描写方面,您怎么确保真正做到“非虚构”?新书中也出现过杜甫去参加李白接风晚宴前的心理描写,还有一些天气状况的描写似乎也带有想象成分。
哈金:我比较依靠叙述。至于细节和景物,我可以查看它们那时是否存在,都有什么特色。这是我与学者们写作不同的地方之一。至于杜甫赴宴前的心态,主要是从他与李白交游时的状态推测的,我觉得不会太离谱,他的确崇拜李白,心切得有点惶恐。我是在讲故事,如果不描写杜甫的心态,就会有一个大漏洞,所以权衡之后就写了那一段,即“杜甫不禁有些胆怯,他想:见面时,李白会把自己当成诗人同道来打招呼吗?李白连朝廷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对他这样一个无名后生,会不会更不屑一顾呢?若表现得过于热诚,李白会不会觉得自己在溜须拍马呢?”。但我不认为这完全没有凭据,虽然是推测的。
燕舞:您对既往英语世界中缺少完整的李白传的一个猜测,是李白诗作的英译需要付给原译者高昂版税,除了花300美元有偿引用卡罗琳·凯瑟关于李白与杜甫友谊的那8行诗,您自己在传中一共独立翻译了多少首李白的诗?
在英美诗歌方面的训练,具体是怎样帮助到您这些翻译的?
哈金:大概有四五十首吧。有些诗并不都是他的代表作,但有些讲故事需要也就翻译了。李白的诗风主要是轻易自然,我也尽量用接近口语的英语来译。当然失去很多东西,我只能做到译诗读起来是诗,有独特的风格。
在用英语写李白传《通天之路》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很多汉诗的特点,也使我坚信古今中外的诗文法度很多是相通的。李白作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就是说无论思想多么深奥,都必须像月光那样直入人心。纵观汉诗,最优秀的诗句都具有这种明净透彻的品质。叶芝也反复强调寻找能“刺透人心的词语”,这个说法跟李白的“明月直入”相类似。古代诗人们意识到诗中的思想不应该太玄奥,那样会减低诗的感染力。复杂的表达方式跟诗歌的情感冲击力往往成反比。
燕舞:李白“他的生平大框已经在那里”,书中有哪些文献资料是您这几年为新书写作而新看的?写这样一部17万字的传记,资料积累和吸收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动笔了,而不会被淹没在史料里?
哈金:既然大框在那里,我就一块一块研究,一块一块写。这跟写小说不一样,不需要完全沉浸在作品中。我并没读所有的新书,只根据故事的需要来做研究,所以我用的专题论文多些。
燕舞:如果要给李白生命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如“童年入蜀”“青年出蜀”“两次婚姻”“壮年干谒”“老年流放”等各挑选一首代表性诗作来对应,您会选择哪几首诗?
哈金:如果这样分,不太容易来标出他的代表作。老年流放时他写了一些杰作,像《朝发白帝城》和《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子夜歌》应该是“壮年干谒”时写的,《长干行》是李白刚出蜀后的作品。至于两次婚姻,他很少写关于夫人的诗,而且都不是杰作,给他孩子的《寄东鲁二稚子》却十分感人,也写得飘逸。
从一开始李白就对格律诗不感兴趣——他不是不会写这种诗歌——他只是不喜欢被形式束缚。他最喜欢的三种诗歌形式是古风、乐府和楚辞。楚辞在气质上特别投合李白的个性。
神殿出版社编辑芦安把本书稿交给她的助手凯瑟琳来做,凯瑟琳是华裔,汉语名叫董琳,她对整个文本做得十分认真,提出应该加入李白的原诗,我立即同意,并提供了繁体字的原文。书出来后,有位著名的美国诗人对我说他欣赏书中有李白的汉语原诗,让英译有所对照,否则英文读者会觉得这些诗句“不过是些拼音字母”,有不可靠之感。
燕舞:同为诗人,对您深入理解传主有什么帮助?“以诗证史”是中国文史研究中的一个悠久传统,研究者在这方面经常举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的例子。李白是一个诗人,“跟着他的诗歌走”,在“诗史互证”的过程中如何确保这些诗作不沦为干瘪的史料,而保存其作为心灵和思想结晶的活力?如何祛除千百年来历代李白研究专家累积在李白身上的“逸事和神话”?“从文学(诗歌)内部来谈文学(诗歌)”又如何兑现?
“虽然写的是盛唐的李白,这本书多少也应该与当下有关”,您尝试理解的盛唐的时代氛围、时代精神有哪些突出特征?这部传记的“当下性”具体又怎么讲?
哈金:那些并不在我考虑的范畴内,我只想讲一个动人的故事,也通过这个故事来展现唐代的诗歌文化。写一个8世纪的中国诗人,最难做的是把故事讲得有趣、丰富,又不浅薄。我更注重写作技术层面的东西,像一节、一段怎样转折连贯。
我们谈到李白时,应该记住有三个李白:历史真实的李白、诗人自我创造的李白,以及历史文化想象所制造的李白。理想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多地呈现真实的李白,同时试图理解诗人自我创造的动机与结果。但我们也必须了解,由于李白一生史料稀缺,这一野心势必受到局限。
燕舞:新书作者简介中称您“主要教授小说创作和迁徙文学”,“迁徙文学”这个译法有什么特殊考虑?在别的文学史家或批评家那里,有“离散文学”或“移民文学”等不同提法,“旅行文学”最近这些年在国内也很流行。
李白少年时由西域迁回内陆四川、成年后的云游与干谒也都是“迁徙”,您则是从中国迁徙到美国,这种生命状态的近似应该有助于您理解这位一千三百年前的同行和传主,哪怕您无法回国重走一遍部分或全部他当年的线路?
哈金:“迁徙文学”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中包括流亡、移民、旅行、战争、传教等,目的是选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这门课主要是为创意写作的研究生开的,是关于长篇小说的形式的课。
李白是一个矛盾的人
燕舞:汉语世界过去关于李白配偶、子嗣的周边研究较为欠缺,关于其生命历程中的关键年份745年的直接书面记录几乎没有,您这次是怎么实现突破的?增进对李白745年活动的了解,主要是得益于李长之、安旗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吗?像青年文史学者唐德鑫在《李白的访道人生及其死因刍议》中呈现的大量信息,按说既往李白学专家也很容易注意到的。
哈金:这方面的资料的确不多。我也没有什么突破,只不过按照常理和史料推断了几处。范震威的《李白的身世、婚姻和家庭》是部丰富的著作,对我帮助很大。
燕舞:李白“一个字都没有写过自己的母亲”,是因为母亲“是少数民族,甚至可能是土耳其人”的异族身份让他自卑吗?按说,唐朝是一个“相对宽容”的时代呀。我们倒是能从新书中看到一些李白的书童丹砂的信息,比如他730年和李白结发妻子安陆许氏府上的丫鬟成亲并留下来照顾女主人,如果没有他的侍奉和陪伴,李白的云游和干谒经历可能难以想象。
哈金:这些李白在诗中偶尔提及,丹砂也被提到,但频率不高。后来的学术成果基本是建立在诗句之上的。唐代非常开放包容,连军队都掌握在外族统帅手中,西方面军由哥舒翰统领,东北方面军则由安禄山统领。
燕舞:比起经商有道、家务安排得当的父亲李客,李白婚后12年才“老来得女”,但他的长女平阳疑似16岁就早夭了,二儿子伯禽在盐场的工作还是后来友人李阳冰协助安排的,可见作为父亲的李白在履行家庭责任上其实是相当不称职甚至失败的。
李白兄弟众多,但从您的转述中我似乎只看到他云游中与一位弟弟有过接触,难道与其他兄弟们就没有交往?家道中落后,其他兄弟是否有人接济过李白?
哈金:资料有限,说不清他和其他兄弟的关系。他724年出蜀时得到了家里巨大的资助,但他726年春在金陵时家里出了状况,资助断了。后来,他就靠朋友和仰慕者们帮助了。李白的朋友元丹丘多次接济过他。
燕舞:李白是天纵之才,他的“干谒投书”集中于年轻在蜀中时期、隐居安陆到二入长安前期、晚年安史之乱前期到流放夜郎时期,从这三个时期的经历来看,他经常是在刻意献诗逢迎地方主官和士绅名流时又忍不住恃才傲物,这是否是情商不够高的表现?从他疑似编造和美化家谱,过于看重两任正式妻子许氏、宗氏相门之女的贵族身份等细节来看,李白还有虚荣、势利的一面?
哈金: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屡受挫折后就基本放弃了。后来在元丹丘和贺知章等人的帮助下,得到唐玄宗赏识,被招入宫。他的大起大落的人生也够精彩的。当然,这样说都是以他的诗歌来支撑的。没有他的伟大诗篇,他什么都不是。
若李白没有不朽的诗篇,
他什么都不是
燕舞: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领衔制作和出镜主持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 Fu:China``s Greatest Poet),2020年4月6日在BBC热播,有媒体人把它当作“中国文化新叙事”(New Narrative of Chinese Culture)。该片当然也讲到了李白、杜甫的交谊,我读尊著其实也是挑着从第16章“两位巨星的相遇”先开始的。千百年来后人对“李、杜友谊”津津乐道,但是,这是否跟一种求圆满的戏剧心理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俩先后进入了文学史,而谈论两个大诗人的交往总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文学史花絮?
在杜甫与李白相识的744年,杜甫彼时并未获得长他11岁的李白那样巨大的现世影响力,杜甫要到宋朝以后才逐渐获得“诗圣”美名。诚如您所言,“李白——可能部分归因于他的道家心态——在对杜甫的感情中更为低调”,“这段友谊对李白的影响没有对杜甫那么深;似乎两人一分手,李白就不再想到杜甫”,尤其是考虑到您另外提及的数据——比如,李白754年与忠实崇拜者魏颢在广陵(扬州)相识后,为这位忘年交写了一首长达120行的《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且将所有诗文手稿托付给他。这么说来,杜甫在与李白的“隔代”友谊中其实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之于李白的重要性还不及魏颢?
哈金:杜甫只是李白的一位朋友。唐代诗人中,李白是少有的独行者。魏颢不一样,他是李白的信徒,跋涉三千里追寻李白。李白熟谙面相,相信魏颢将来会做官,后来应验了。他也需要魏颢,告诉他将来发达后别忘了自己和儿子明月奴。
Du Fu:China’s Greatest Poet海报
燕舞:李白曾经将所有诗文手稿托付给魏颢,那761年年底托付给李阳冰的“所有的诗歌手稿”是另一批么?
除了孙子、屈原、庄子、鲁仲连、司马相如、诸葛亮、陶渊明、谢朓、骆宾王、陈子昂等古代或大致同代的“偶像”外,在李白的同时代,贺知章、孟浩然这样长一两辈的文友之外,他还有没有像元丹丘这样能平等相处的好友?在前述一众古代或同代“偶像”中,对李白诗歌写作技艺影响较大的有没有?
哈金:魏颢和李阳冰手中的李白手稿是不同的两批,它们构成了现存的李白诗文的主要部分。孟浩然是李白的好友,但早逝了。元丹丘是他始终如一的朋友和教友,没有第二人像他那样跟李白情同手足。
燕舞:BBC这次新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其名称来源于旅美华人学者洪业先生1952年出版的同名专著Du Fu:China`s Greatest Poet并以之为讲述蓝本——副标题“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后并没有加“之一”,倒也符合“诗圣”的提法;同样是在1952年,诗人冯至在北大西语系主任任上出版《杜甫传》,他也独独推崇杜甫,追问“为什么与杜甫同时代且同享盛名的李白与王维就不能这样替我们说话(就像一个朋友替我们陈述痛苦一般),他们不是同样经过天宝之乱吗?”
但是,今人习惯将李、杜并称,诗人西川在《唐诗的读法》(北京出版社,2018年4月)中论及中唐诗人元稹“可能是较早比较李杜诗风与诗歌成就的人”时,提到“宋人抑李扬杜”;您援引过的《李白与杜甫》,其作者郭沫若被一些当代读者和批评家质疑为以“贬杜扬李”来“迎合”推崇当时“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潮流。
虽然理性提醒我们,应该警惕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可是,“李杜优劣论”还真是一个学术问题,国内以解读金庸而走红的“80后”作家、《给孩子的唐诗课》(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作者“六神磊磊”去年底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就推送了一篇演讲,讲题非常直白——“李白和杜甫到底谁更厉害?”……如果非要在李白和杜甫之间做一番综合性的比较,您如何评价从“抑李扬杜”到“贬杜扬李”再到“李杜并称”的观念变迁?
哈金:我认为那种比较没有意义,文学圣堂中有的是座位,他俩各有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杜甫更深沉些,而李白多了一个宗教的层次,有其复杂的一面。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燕舞:像您说的那样,盛唐进士殷璠编纂的《河岳英灵集》“提供了唐人如何看唐诗的角度”——二十四位入选者中,李白诗作当时入选了十三首,杜甫为零——这个考察时段再延续至清人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入选的杜诗又多出李白好几首。
哈金:到了《唐诗三百首》,李、杜已经成为汉诗的顶峰。但我写的是唐代,要考虑什么信息应该收入,要有节制,不能罗列,不能让叙述的张力松弛下来,所以《唐诗三百首》根本不必提及。这个选本对英语读者来说没有意义。
燕舞:李白在世时就获得了巨大声誉,杜甫的经典化过程迟至宋朝以后才逐步完成,您自己出道三十年来已经先后夺得海明威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您会觉得自己幸运么?
记得2008年10月号《印刻文学生活杂志》早就做过一期您的封面专辑“雪飞的国度——哈金的两个大陆”。个人著述在当代就完成了某种程度的经典化,您如何克服“成名”带来的弊端?
哈金:不能这样比。文学成就跟奖项没有关系,还有,奖项都是眼下的,靠不住的。经典化需要时间来定夺,我们很难预测。不过,写李白传的过程让我看清,如果他没有不朽的诗篇,那他什么都不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做的只是努力把作品做好,做得更好。
燕舞:《北京文学》去年9月号就率先推出了尊著的8万字精选版,“国内读者较为熟悉的李白诗歌和情节稍有删节”,这精简的部分反而应该就是您着重向欧美普通读者介绍的吧?饮酒之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意义、入赘的婚姻形式等,感觉都是您特别提醒海外读者注意的“文化中国”背景,还有哪些方面您写作时比较注重向欧美读者解释和强调的?
哈金:师力斌编辑两年前就与我约稿了,但后来传记太长,《北京文学》从来没发过超过8万字的作品,所以就出了个删节版。我并没有介入这个过程,取舍都是他们做的,我让他们酌情处理。
燕舞:您在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部执教多年,这个教学机构的特点是不是相对比较淡化文学理论?“传记”的写作应该并不包括在“小说写作”课中?
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初结集出版了哥大东亚系商伟教授的讲义《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对您在新书第5章里写到的李白对《黄鹤楼》作者崔颢的“嫉妒”也有涉及,商著研究的“诗歌文本的互文关系”等我感觉比较学理化,北美大学东亚系的学生们本来就文言文基础相对薄弱,阅读这类诗学专著是否较为困难?
哈金:商伟这几年在做唐诗研究,唐诗是他的本行。我们一起修过宇文所安的汉诗课。
我们的创意写作部没有非虚构类,写这本传记完全是我自己的工作。我们学校的非虚构写作在传媒学院里,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至于文学理论,我们不强调,但我们是英文系的一部分,所以学生必须修文学课,自然要涉及文学理论。跟美国其他创意写作项目比,我们比较强调文学性。
燕舞:在李白广泛的人际交往中,他和生卒年几近一致的王维“没有任何记录表示他们曾有过交往”——尽管他们有孟浩然、杜甫这些共同的师友,这个谜团吸引着包括宇文所安在内的不少中外学者,您给出的一种猜测是,“除了诗歌上的竞争外,两人也有可能因为都被玉真公主欣赏而关系微妙。这种竞争也许能大到让他们一生疏远,彼此形同陌路”,是否还应该从两位同龄诗人的性情、气质和精神结构以及各自在长安诗坛的话语权、流派倾向等更多方面来尝试解析?
哈金:李白确实渴望能得到玉真公主的青睐,但她更喜欢王维,尽力帮助他。这应该是李白的一个心结,当然我也提到两位大诗人的诗风、秉性、宗教、仕途都迥异,所以他们很难交往。王维虽然为官,但他是佛教徒,不是飞扬跋扈之人,所以我认为玉真公主才是两人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
燕舞:李白的同代诗人及宋代诗人在诗作中书写歌女、舞姬等女性形象的情形并不少见,但您认为他的独特点之一是“写了大量女性口吻的诗歌”,这一点跟笔下多女性意象还不是一回事?
哈金:不是一回事。比如,王昌龄也写女性经验,但不以女人的口吻说话。李白则给了许多女性自己的声音。从诗艺上讲,诗人和说话者是不同的人,这样就给了诗歌更大的容量和空间。
通过写作和作品来融入伟大的事务中
燕舞:新书中您比较多地强调李白作为“道家徒”的一面——“李白的家园实际上永远是在途中,诗人生命的本质存在于无尽的漫游中,好像他在这个世界上注定只是一个过客”,“几十年来,李白在两个世界之间撕扯着——代表世俗政治最高层次的朝廷和代表精神领域的道教——但李白在两个地方都无法久留”……可是,多次干谒受挫之后他还一再谋求入仕,甚至晚年还希望能参军,这不就是再典型不过的儒家思维和行事方式么?只是他头脑中的道家思想在与儒家思想的竞争中占了上风?
林语堂认为苏东坡“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是一纯然道家”,并“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李白也是一种“混合的人生观”吗?
哈金:李白既想成仙,又想入仕,最终两者都不可及。他的确非常执迷于仕途,但每当受挫,就退回到道家的天地。此外,道教是唐朝的国教,所以他看不起儒教。到了宋朝,儒教已经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林语堂用儒教来解释苏东坡入世的一面,完全说得通,儒教确实只关心此生此世。
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大量使用月亮意象的第一人,他不断赞美月亮的高洁、纯粹与永恒。他想象月亮是一方神仙居住的祥瑞净土,到处是神兽仙草和仙人们的私人宠物。中国古代信仰不太分离神性与人性,人们想象中的天堂似乎只是人间的升级版:风景、建筑、人物都类似,只是更神奇。任何人只要修炼得当,并假以时日与诚心,最后都可能得道成仙——中国很多庙宇里至今都供奉着这些地方神祇。他们本属人间,后来成为不朽,升到了天上,拥有神奇的法力,有点像西方的超人。
燕舞:新书中第1章在谈及屈原之于李白的影响时,您就大跨度地做了一个中西方诗歌的比较,称“与西方诗歌不同,中国诗歌的性质总体上是更世俗的,倾向于关注人间的疾苦与体验。中国诗歌不太召唤神明的帮助”,您1993年在布兰代斯大学的博士论文涉及奥登、庞德、艾略特、叶芝等几位英语现代诗人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素材,那李白最适合类比的同时代西方诗人您认为是谁?能否简要列举您特别推崇的几位中西方诗人?
哈金:李白跟西方的诗人不一样。汉文化中没有缪斯这个艺术之神,所以文艺不具备神的佑助。但李白确实有一个神灵的层次。汉诗中我喜欢杜甫、李白、白居易、辛弃疾、李煜。西方诗人我喜欢的比较杂些:荷马、乔治·赫伯特、弥尔顿、惠特曼、叶芝、哈代、艾略特、奥顿、布莱希特、博尔赫斯。
燕舞:《通天之路:李白传》之后,您最新的写作计划是?
哈金:我的下一部长篇《放歌》明年春天将由神殿出版社出版,现在正忙着修改和编辑。
燕舞:12年前《印刻文学生活杂志》的封面专辑“雪飞的国度——哈金的两个大陆”,可以认为是对您写作成就的一个及时判断与命名,纽约的《巴黎评论》也做过您的专访。海内外媒体对您的专访不在少数了,未来若干年间还可能有关于您的传记问世,可是,如果眼睁睁看着这些访问记或传记写不出您的复杂性和立体性,作为一个创作者您会不会很沮丧和气馁?
哈金:我不想看见自己的传记。我深受薇拉·凯瑟的影响:“真正的幸福是融入伟大的事物中。”这种融入,只能通过写作和作品来完成。这才是我渴望能做到的。
(全文参见《文学》2019年第1期,第99-11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