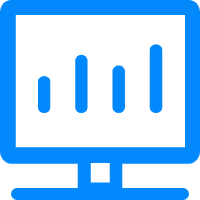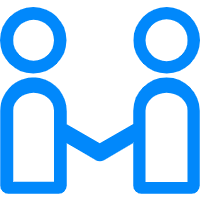文/陈威敬
离婚时索要“工资”,合理吗?司法实践中,这一问题回应的是家务补偿请求权。在全国政协委员黄绮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做家务不是天经地义的。法律层面上,这一答案也毋庸置疑。但自相关条款制定的20多年时间,实践中却出现了操作困难的情况。
全国两会期间,与家务补偿制度有关的提案和建议引发热议。2021年,在《民法典》新规的助持下,曾因其适用条件遭诟病的家务补偿制度被“唤醒”。
但一年多的实践以来,举证难、补偿金额低等问题仍不尽如人意。黄绮建议,应完善健全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比如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目的能否实现、家务劳动价值究竟如何评价事关妇女权益保障,也关乎家庭的稳定”。
全国政协委员韦震玲则进一步建议让家庭主妇或家庭煮夫成合法职业,从而使家务“工资化”,进而也可以享受工龄累计及劳动社会保障等相关权利待遇。
在鼓励生育的当下,家务劳动的价值无疑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在家的一方,应怎样得到认可?观念上的改变又该如何推进?
从“无偿”到“有偿”
传统意义上,家务并不被视为一种“劳动”。在日常生活中,家务只是家庭生活中的一种分工,不属于社会生产劳动。但事实上,家务劳动从法律层面被赋予经济价值早有年头。
200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0条即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但此款规定仅局限适用于分别财产制。而这种财产制度,并不广泛见于我国的“家情”,这也导致该条款最终罕有实际应用。
直到2021年《民法典》的正式施行,才打破了这一僵局,其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顾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此后,离婚经济补偿请求权的行使不再受财产制的限制,适用余地明显加大。
2021年2月4日,北京法院网报道了北京房山审结的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该案中,全职太太王某诉讼中称,因承担大部分家务,故提出要求家务补偿。最终,法院判决其与丈夫陈某离婚;除了双方平均分割共同财产10余万元外,陈某还需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5万元。
该案是《民法典》适用后,家务补偿的第一案,正式标志着家务劳动从“无偿”到“有偿”。首案无疑具有较大的示范案例意义。“全职太太离婚获5万家务补偿”当时引发媒体广泛讨论。
一些网友认为,5万元的补偿金额过低,与女性对家庭的付出不匹配,尤其在北京地区,即使比起正常的家政人员收入也相去甚远,“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一方在外赚钱、一方在家劳动,属于正常的家庭分工,都是为家庭奉献。
该案主审法官、副庭长冯淼回应表示,家务劳动可能形成的是无形的财产价值,比如说配偶另一方个人能力的提高,个人学历的增长。
冯淼还表示,在《民法典》大框架下,金额的定量主要是由法官合理合情合法地行使自由裁量权。5万元的经济补偿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因素:双方婚后共同生活的时间;女方在家务劳动中具体付出的情况;男方个人的经济收入;当地一般的生活水平。
怎么补偿?
显然,若以家政人员的收入作为对比标准,该条款实际的适用中可能会出现别的问题,比如应得收入多于家庭总资产。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看来,家务劳动也不是纯粹的雇佣关系,还有感情因素。
此次全国两会上,黄绮提出了《关于完善健全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建议》。
黄绮称,通过法律裁判文书的检索发现,司法实务中对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仍然比较谨慎保守。判决支持补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不多,金额也不高。
中国新闻周刊以“家务补偿”为关键词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在仅有的10例相关判决中,最终支持补偿请求的仅1例,其他大多因证据不足被驳回。
黄绮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其中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家务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社会观念上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度并不高,认为为家人做家务是天经地义的。
其次,家务劳动与共有财产制的关系有待厘清。法官在处理离婚经济补偿请求时十分慎重,多采取析产时酌情照顾的方式,数额一般不高,“有的认为不应该得到经济补偿,那么就不判”。
再者,家务劳动价值本身难以量化。家务劳动属于家庭事务,外人很难知晓其中究竟谁的贡献更大。此外,对一方因家庭整体利益考量而作出了对自己个人职业发展不利的选择,在司法实务中一般不予考量。
资深家事律师,公益机构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莹也认为,家务劳动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仅要证明自己做了家务,还要证明做得比对方多,“对于大多数结婚不是为了离婚的人来说,很难积极地去保留证据”。
这也导致实际的应用中,一般仅考虑家庭主妇/家庭主夫的诉请,“双薪”家庭很难得到支持。李莹说,其去年代理的十五六起离婚案,均属“双薪”家庭的情况,家务补偿请求无一得到支持。而根据规定,仅有离婚时,才能适用家务补偿请求权。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就此提出,建议让家庭主妇或家庭煮夫成合法职业,推行特殊家庭特殊时期家庭全职服务工作职业化。让家庭主妇、家庭主夫获得相应的劳务补偿,并享受工龄累计及劳动社会保障等相关权利待遇。
李莹也认为,对于一些特殊的家庭情况,比如全职照顾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失能老人等,即使在双方未离婚的情况下,也应准许提请家务补偿。
黄绮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首先,完善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规定。在离婚经济补偿因素的基础上,还应将因此牺牲了自身的发展机遇作为考虑因素之一。“比如是不是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事业,放弃了自己在事业上或者学业上能够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或者另一方是否得到更多事业上的前进的余地,财产积累的可能。”
此外,应该增加“夫妻财产知情权”条款,让夫妻之间持夫妻关系有效证明查询对方财产成为可能。
其次,应出台指导意见统一适法。基层法院有“适用难、不适用”的现象,建议最高院开展综合研究,明确判决情况下离婚经济补偿应考虑的因素。黄绮举例说,比如《民法典》里适用“离婚”的情形,其评判“感情破裂”的原则,也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最后是优化程序性、制度化规定。建议离婚诉讼中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补偿请求权。因经济补偿请求权需当事人一方主动提起,法院不得主动适用;且经济补偿请求权只能在离婚时提起,离婚后不能单独提起。同时,建议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预留家务补偿份额,再进行共有财产的分割,避免执行困难和重复诉讼。
认可来自判例
一直以来,围绕着该话题的争议点实际上在于,家务劳动是否有价值,又该如何体现?
黄绮说,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以及男女两性固有的生理差异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女性更容易成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但传统观念中将家务劳动视为对家庭成员的爱与情感的具体表现。因此,社会观念上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度并不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我国男性家务劳动时间对比女性占比不到30%。
“在我们以往接触的案子中,家务补偿很少被提出,甚至当事人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在李莹看来,《民法典》对于家务补偿制度的“解绑”,以及首案的释法,无疑从法律的角度认可了家务劳动的客观价值。
李莹说,社会上一些观念仍认为从事家务的一方是从属性质的,没有真正认识到家务也是一份工作,在有些国家是作为一份职业来看待的。
在黄绮看来,家务劳动同样有社会功能。如果一方不把家庭打理得好一些,那么在外的一方也会受很大影响。但到了离婚的时候,在家的一方转变为社会独立生存时更为弱势。这也是尽管已经分割了共有财产,仍需要提出补偿的应有之意。
近期,通过判决补偿金额较高的一起是今年1月份由厦门某法院披露的再婚夫妻离婚案,金额达到了20万元。据法院披露,60多岁的老陈早年丧偶,第一任妻子因病去世,留下6个未成年的孩子。1987年老陈与阿红再婚,组成新家庭。婚后,老陈与阿红又生了两个儿子。
婚后很长时间,老陈主要在省外做生意,阿红在老家,双方聚少离多,直到1998年,他在厦门买了第一套房,才把阿红接到厦门生活,但他和阿红的感情变淡了。如今两人都有离婚的念头,但是因财产分割的问题激化矛盾,无法调解。
阿红认为自己承担起照顾孩子和老人、操持家务的重任,在30多年的婚姻中尽心尽力。男方对千万家产分割意见不大,对家务补偿金却强烈反对。
最终,法院酌情认定老陈还应向阿红支付家务劳动补偿金20万元。
另据北京日报报道,林先生与谭女士2010年结婚,婚后不久,2011年林先生便考研读博,直到2016年博士毕业。2020年,林先生向法院起诉离婚。谭女士同意离婚,但她提出,林先生在考研读博的5年时间里,自己用婚前积蓄及工资养育女儿、负担家庭日常开支,并承担家庭衣食住行等所有家务劳动,故谭女士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10万元的要求,并获支持。
从已公开的判例和相关报道来看,最终补偿的数额差别较大,6位数以上的不常见。也有一些判例引发争议,去年,浙江台州某地审结的家务补偿首案,结婚3年的全职妈妈要求家务补偿19万,最终仅获支持1.5万元。
“实际上这种意识上的认可和肯定更多的其实来自于司法的判例”,黄绮说,法律在司法实践当中被运用了,就会在社会上逐渐被认可和重视。
李莹也认为,应有一定的强制性的法律政策去进行归置,“不能指望着一方的良心发现”。她表示,尽管全职主妇更常见,但实践中,也有全职丈夫诉请补偿获支持。但在一些观念下,社会包括其自身对“全职丈夫”仍持有一些偏见,这也使得一些男性难以接受这样的身份甚至主动放弃相关的权利。
李莹介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时,她也曾提出包括男性育儿假等问题,希望能推动男女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家务劳动价值关于家庭的稳定,在鼓励二胎、三胎的当下,这一问题尤其应得到重视”,李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