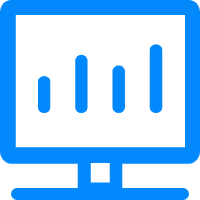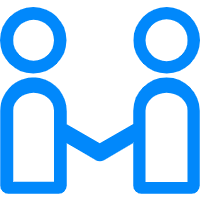刘建宾,1988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民盟浙江省华夏书画学会台州分会副会长、温岭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大展并获奖:
1991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西子杯”全国书画大赛获优秀奖,并和著名画家宋忠元、童中焘、卢坤峰、吴山明、何水法等进行了交流。
1993年5月,作品入选全国第三届体育美展,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观看了此次展出。
1993年10月,作品入选全国首届山水画展,并荣获铜奖。
1994年12月,作品入选全国第八届美展。
1997年6月,作品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97第三届‘枫叶奖’国际水墨展”,并获优秀奖。
1997年10月,作品参加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中国首届艺术大展”,并获优秀奖。此次展览还在欧洲各国进行了巡展。
1999年5月,作品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中国新时代‘巴黎铁塔杯’书画大赛”,并获优秀奖。
2000年5月,作品参加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澳洲中国美术馆藏品展”,并收藏。
2002年5月,作品入选《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0周年》全国美展。
2014年10月,作品入围《全国第三届现代山水画展》
2015年8月,作品入选全国第二届教师美展。
作品还多次应国内外多家专业机构之邀参展、拍卖和受聘。并应邀在人民日报全媒体接受了专访,全国各大网站也进行了推介。
刘建宾专访:肌理就是我作品的“符号”
浙江在线5月22日讯(记者 金子琳 赵静)刘建宾在温岭中学实验初中任美术老师,记者来时,他刚好下了课,就引着记者来到他的工作室。
清泉漱石,花木扶疏,和煦的阳光洒落在玄关处,迎面而来一股清新幽静的气息,这是刘建宾在喧嚣闹市中辟出的清雅一隅。就是在这里,刘建宾创作画作,经营生活。
天赋使然,爱之弥深
天赋就是兴趣。儿时的兴趣往往能在事业上造就其一生。少时,刘建宾爱极了那些斑斓缤纷的色彩。他笑言:“那时别的小孩子都是在玩泥巴、玩弹弓、翻跟头,只有我‘特立独行’,爱四处乱涂乱画。自己家里的墙壁画了不过瘾,还画到别人的家里去了,反正到处都留下了我的‘大作’。父母说我,我当时应下可回头就忘了,而且屡教不改,为此真没少挨骂。”
那个特殊的年代,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柴米油盐,或者围绕着柴米油盐。孔子都说:富之而后才教之,填不饱肚子何谈艺术。屈从于困顿的生活,刘建宾当年只得止步于涂鸦,将画画的热情深埋于心……
1984年,由于工作调动的关系,刘建宾离开家乡,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
契机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建宾踏足南京文化馆。当时一个业余美术班正在这里上课,他站在窗外观望,不禁流露出羡慕渴望之色。当时授课的也就是后来成了刘建宾启蒙老师的南京艺术学院冯一鸣教授。
‘我能在这里学画画吗?’,没想到冯老师一口就答应了。”至此,刘建宾从原先的小打小闹、信手涂鸦走上了正规学习美术的道路。
冯老师专攻工笔人物画,刘建宾就跟随着老师开始学习工笔画,临摹、写生……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根基。之后,在老师的建议和鼓励下,刘建宾开始备考大学。十年文化大革命,让早早踏入社会工作的刘建宾经历了一段文化的空白期,重新拿起课本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课的几分之差,刘建宾和当时的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失之交臂,被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录取,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两年的大学学习经历,时间虽不长,但让刘建宾收获颇丰。虽然在学校学的都是最为基础的,画画也从最基本的素描开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是学校老师的创作理念和美术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他,分别是得到了范保文、范扬、徐培成和陈传席等颇有威望的导师的悉心指导,让刘建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坚实的理论基础,成熟的创作理念,加上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1991年,刘建宾收到了美术带给他的第一份荣誉。他创作的《制棋教子图》在杭州举行的“1991‘西子杯’全国书画大赛”上获得优秀奖,这也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得到业界的认可。
毕业之后,刘建宾的画作屡屡入展,多次获奖。在1993年,他的二幅作品《初到凤凰》《龙舟竞渡》分别入选“全国第三届体育美展”和“全国首届山水画展”。特别是在“全国首届山水画展”上还获得了铜奖,并且得到了美术界前辈的肯定。如:前中国美协党组书记雷正民在此展总结性的文章《凌跨新境界》中提到刘建宾创作的《初到凤凰》:“……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众多作者钟情于民族民间艺术的挖掘与发挥。……从色彩处理到画面构成都饶有新意。”,这给了刘建宾极大的信心和创作热情,也更加坚定了他将画笔杆子拿到底的。
肌理是我作品的“符号”
“一个学生曾说,您的作品都是自带‘标签’,不看名字就知道哪幅是您画的。”对于学生的评价,刘建宾显然乐于接受。
受学院派的影响,初期的刘建宾一直在模仿名家的画风,人物画的风格也都非常写实。但是,刘建宾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这个框架内。慢慢地,他开始加入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将原来传统的工笔表现技法转变为淡雅朦胧的风格,在造型方面为了强化人物的个性和主题,对一些器官略加变形,以此表现出不同类型的人物特点。而后又加入民间艺术的一些元素,也让刘建宾的作品中的造型更加夸张,风格更加独特。
“他们那靠着平时积攒的生活经验,直觉的主观判断,粗狂质朴的线条和夸张变形的‘神气’造型,‘俗’得不得不让我动心。也使我这时期的人物造型更加夸张,线条更加稚拙粗犷。”
与“肌理”的结缘,源于一次西北采风。
细看刘建宾的画作,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画中都有刘建宾钟情的“秘密武器”------肌理。
“初到敦煌,敦煌石窟的宏伟气势使我倾倒,窟内那艳丽色彩和精湛的技艺的壁画让我心动,但真正令我震撼的是它那经过千百年洗礼而成的极具斑驳迷离神秘感的肌理之美。离了这点,我觉得敦煌壁画只是一件记载历史佛事的工艺品罢了。”
受此启发,刘建宾便尝试着将民间的稚拙造型和敦煌壁画的色彩与肌理美进行有机结合。1991年获奖的《制棋教子图》便是他出成绩的第一个“试验品”。
《制棋教子图》是以叙事的形式创作的。汲取了夸张的民间绘画式的人物造型,敦煌壁画的自然的肌理和古代岩画及竹简的一些元素,一场生动的围棋教学跃然纸上。
之后创作的《初到凤凰》、《龙舟竞渡》、《呆儿看店》以及近年来创作的《桥系列》都是刘建宾在肌理作画过程中的成功尝试。
“我一直觉得创作出自己的作品并不止于口头,一定要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符号来表达自己的东西才更为贴切。”毫无疑问,肌理已经成为刘建宾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艺术符号。
缘浅缘深,恣意生活
2001年,刘建宾来到台州温岭,这个后来被他称之为“第二故乡”的海滨城市。他在这儿一呆就是13年,从事着从小梦想的职业——教师。虽然是不受重视的副科美术,但是刘建宾还是自得其乐,用心教书,随心作画。
聊到创作计划,刘建宾说之前一直想为这个“第二故乡”留下点什么,于是便有了创作《即逝的家园》之温岭石塘系列画的想法。
“咱们温岭是个物产和精神文明都非常富有的地方,而石塘那些特别天然的东西更是弥足珍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财富都在慢慢消失,我要再不把它们以绘画的形式下来,恐怕我们的后代就再也看不到了。”
从儿时小打小闹的涂鸦,到迫于生活压力的放弃,最后重拾画笔,并画出了自己的人生。从工人,学生,艺术家,老师的角色变换,怕是刘建宾自己都没想到与画的“缘”竟然如此之深。
“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画画,说什么都不会放下,它已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无法割舍。”说到美术在他心中的份量,刘建宾眼神中流露出的坚定给了我们答案。
原标题:刘建宾专访:肌理就是我作品的“符号”
稿源:浙江在线
作者:记者 金子琳 赵静
编辑:金子琳
我用肌理作画的理由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众多作者钟情于民族民间艺术的挖掘与发挥。《初到凤凰》(刘建宾)……从色彩处理到画面构成都饶有新意。”(《美术》1993.第10期)
“刘建宾的作品《初到凤凰》运用了敦煌壁画浓重的色彩和民间剪纸粗犷的线条,使作品带有强烈的形式美。在这次展览中独树一帜。”(《江西日报》1993.10)
以上这两条评语,分别是由前中国美协党组书记雷正民和时任江西省美协秘书长马宏道在各自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他们虽然对我的这幅在1993年“全国首届中国山水画展览”上荣获铜奖作品的艺术特色给予了较准确的评价,但有一点没提到,那就是运用肌理的美来表现凤凰古城的遗韵,这才是我的作品在此次展览中的独到之处。因为当时没看到有哪一位画家用肌理来作画,在创作这幅作品之前,我也并没有研究过肌理美对艺术作品的价值,只是很喜欢像敦煌壁画这一类带有令人叫绝的肌理美的艺术作品。我想其实敦煌壁画只是用绘画的形式来记录佛事,当然,其中也不乏艺术精湛的作品。但如果没有经过千百年来的蜕变而形成的残缺斑驳的肌理美,这些壁画大多也仅仅是有着历史研究价值的工艺品罢了。大概也就是因为敦煌壁画有着那千百年来天工雕饰的肌理美,才成为令中外艺术家们对她魂牵梦绕、心驰神往并为其“艺术”魅力所折服的原因吧!
记得那还是上世纪90年,我就曾用高丽纸临摹过敦煌壁画,试图体会出其肌理的表现方法,但总不满意,于是一气之下把画揉成一团,可又觉得弃之可惜,于是又打开,这时神奇出现了,可能是由于刚才的揉搓,画面上呈现出了不规则的肌理纹。后来我又试着临摹了几张,并进一步丰富了肌理的表现方法。不久,我用肌理的方法创作出的第一幅作品《制棋教子图》在当年就荣获了在杭州举行的“1991‘西子杯’全国书画大赛”优秀奖,(我猜想当时的浙美教师唐勇力可能就是在我这幅画的启发下,制作出了敦煌系列作品,只不过方法比我更高明罢了。因为他当时和我一起获奖的作品并没有肌理的运用,有当时的获奖作品集为证)。这样就增强了我用肌理来表现作品的信心和决心。1993年我又有二幅作品分别入选“全国第三届体育美展”和“全国首届山水画展”并获奖。目前看来以肌理美去创造艺术作品的趋势已进入了方兴未艾的时代,而且无论是肌理的制作方法还是制作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也一直想就此方面写一篇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搁置了。偶尔在今年第四期的《国画家》杂志上我看到了韩玉婷的一篇《浅析当代中国人物画出现肌理表现的原因》一文,便又勾起了我想写此文的意愿。下面我想就用肌理表现作品的原因谈一谈我粗浅的看法。
我以为韩玉婷在这篇文章中所谈及的问题有一定的见地,但我也觉得作者对肌理的理解面似乎有些狭窄了。其实肌理的问题,自古以来一直伴随着中国画的始终,只不过是词汇的表达不同而已。中国画所讲究的线条笔墨都属于“笔触”、“笔痕”,而这些笔触、笔痕如“屋漏痕”、“锥画沙”笔墨的干湿、浓淡、生涩润泽都恰恰呈现出了某些肌理的效果,正是这种笔触、笔痕肌理丰富了中国画艺术的表现力,才使其有着艺术的感召力。
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就论及到“笔有四垫:谓筋、肉、骨、气。笔绝而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迹画不败谓之气。”虽然中国古代尚未有“肌理”一词,但中国画历来重视线与墨的表现力。一根线要“一波三折”,一块墨要“墨分五色”。中国古代的画家们已用自己的实践证实了点、线、面中的肌理特点。
“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唐、王维《山水诀》)在此以前中国画都依附于“重彩”,至唐宋开始,“水墨画”已经成了中国画的代名词。既然“水墨画”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中国画家们不仅力求创造水墨画的视觉审美效果(既在单纯的水与墨之间创造出无限的润与涩、黑与白、干与湿的各种水墨润画的肌理变化),同时还力求在精神审美空间中创造出“身与迹化”的艺术境界。中国画家们的这种努力,不仅时时表现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同时也表现在历代的画论中。
在历代画论中阐述得最精辟的也许要算自然肌理与中国笔墨之间的关系了,“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质也。得笔墨之法者,山川之饰也”(清·朱若极《石涛画语录·山川章第八》)。这里的“乾坤之理”、“山川之质”应是大自然的各种表面肌理无疑,而中国画的笔墨之法却又是来源于这些自然肌理的“山川之饰”。“画之理、笔之法不过天地之质与饰也”(同上)中国画家们在描绘这些“天地之质与饰”的自然肌理时,逐渐总结出了它们的造型规律,并把这些自然肌理作了类比与概括。如山水画的各种皴法、人物画中的十八描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以上所述中国画技法“并非古人杜撰、游戏笔墨”而已,它实际是“按形求法。”可以这么说:中国画概念化的肌理,以程式化的形式用类比的手法来表现自然,一方面,这种概念化、程式化、类比化和意象化的技法越来越成熟,以至于发展到清朝“四王”时,它已背离了原来的“乾坤之理”、“山川之质”,而变成为一种纯技巧性的笔画游戏;另一方面,这种程式化了的技法又制约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使其越来越窄,只能在传统题材中找出路。那么怎么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只有在表现形式、制作手法和工具材料上作新的尝试,才有可能出现新题材、新意境。其实古人们也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了一段宋迪的画论:作画时“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景皆天就,不类为人,是谓活笔。”斑驳残缺的败墙促发了画家的神思,使画家在这自然肌理中“心存目想”出了“景皆天就”的高山峡谷这一“神会”的自然并非真山真水,无需用传统的、程式的皴法去表现,只需“随意命笔”,但求“活笔”、“不类人为”。而唐代王恰为求“非画史之笔墨所能到也”的水墨润染的肌理而“以墨泼图嶂之上,乃因似其形象,或为石,或为林,或为泉者,自然天成,倏若造化”(《宣和画谱》)。
由此可见,自唐以来,中国画家们从未放弃过对新形势、新技巧和新意境的探索。传统程式化的笔墨技巧,也一直受到各种挑战,而清代画家高其佩更是对传统工具形式进行了彻底的革命,创造了指画,即以手指、掌作为工具,蘸色墨进行创作。虽然这些尝试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非正统”(包括王洽的泼墨及吹云弹雪法)但在今天不也都成了我们的传统吗?试问:倘若当时没有这些“狂妄之徒”的大胆探索,能有今天如此绚丽丰富而独特的中国艺术吗?但这里强调的是:古人有关“肌理”的论述,实际上都是主观肌理,它与客观的自然肌理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画家用笔“制作”这些肌理,都是经过画家们主观化了的纹理,它起着能艺术化、意象化地再现自然物象的作用,以使自己的作品富有艺术感染力。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着。我们就理应与时俱进,学习高其佩等先辈们坚持打破“笔是唯一绘画工具”的传统观念,在留有中国画基本元素的基础上,善于吸取外来艺术和其它画种有益成份,大胆尝试使用各种材料、工具和技法来丰富提高我国这一艺术瑰宝——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让她散发出更强的艺术魅力和新意境。
最后我想用俄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的一段话结束这篇文章:“当我们陶醉了沙特尔教堂中风雨剥蚀的塑像时,我们情不自禁的把这些塑像的斑驳铜锈和娴熟的塑造手法同样地当作审美价值。但是这种价值与客观的或艺术的价值毫无关系。前者含蓄的暗示了光线和色彩的特殊作用所引起的感官快感与对‘古香古色’、‘扑拙’产生的情绪,后者只是塑像作者的创作意图所在,对哥特石刻家来说,年代引起的损坏不仅仅是不相宜,而且令人恼怒——他们就曾为塑像设色以图保护。但如果它们真的被保存的完好无缺,我们的审美快感也许要受到很严重的破坏。”我喜欢用肌理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