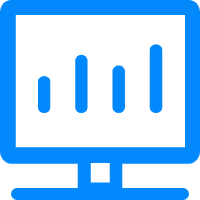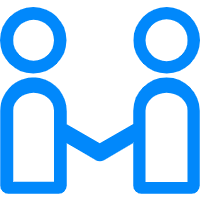田永秀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铁路史。
刘雨丝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摘 要:边疆研究是考察近代中国由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领域,而近代铁路因其与边疆危机的关系紧密正逐步成为边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19世纪后四十年,中国的边疆危机愈演愈烈。清廷按照“由腹达边”的原则修筑了一批国防铁路干线,以期支援边防、拱卫中央,通过军事固边使边疆成为维护内地安全的屏障。进入民国后,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现代边政学的兴起,国人意识到开发治理边疆、促进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是缓解边疆危机、巩固国家统一的长远之计和根本途径,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筑路实践。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代国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时对铁路的认识变化及实践,厘清铁路在近代边疆危机中的功能演进。
关键词:近代铁路;边疆危机;铁路功能;固边治边
近代中国铁路与国防关系密切,学界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把近代国防发展贯穿于铁路发展史的进程之中。如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李占才《中国铁路史(1876-1949)》等,阐明了近代中国铁路起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防止西方列强对边疆的入侵。二是把铁路的筹备与实践放入近代国防史、军事史的背景来探讨。如程清舫《非常时期之国防建设》阐述了军事训练、部署和集中等都仰仗铁路的运输;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则指出近代海防塞防并重方针的确立开启了边疆铁路的建设。第三类是直接针对该专题的研究。如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详述了铁路短缺给抗战时期军事运输带来的困难和教训;方举《中国铁路史论稿(1881-2000)》,设“铁路与国防实践”专题,对晚清边防危机及抗日战争中的铁路进行了研究,认为西北是国防的重点,腹地铁路应向西北纵深配置;易丙兰《奉系与东北铁路》、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以路治边’政策研究”专栏等,对奉系东北铁路的固边价值进行了专门探讨。以上学者的研究已经把铁路史与国防、边疆学联系起来,并从铁路角度对国防建设和边疆治理作了一定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这些研究主要是静态、特定的,重点是针对近代边疆危机和战争中铁路作用的分析,缺乏对铁路与边疆关系的动态、集中的思考。本文试图立足于上述研究,尽力明晰两个问题:一是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时对铁路的认识变化及实践,即铁路在近代边疆危机中的功能演进;二是探究这一变化与近代治边观念变化的联系,深化对近代边政思想的理解。
一、巩固疆圉:近代兴办铁路的重要原因
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边疆危机愈演愈烈。西方列强加剧殖民扩张,已开始取代边疆地方势力而成为威胁中国边疆安全稳定的最大来源,传统“夷夏之防”变为“中外之防”。在这场中西较量中,西方国家将铁路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不仅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铺设铁路,还不断要求中国对其开放边疆地区的探路权和筑路权,以此蚕食中国主权。作为回应,清廷萌生了自筑铁路的念头,于19世纪九十年代将大规模修筑铁路定为国策。
(一)铁路成为西方列强侵略边疆的工具
从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将其触角伸入东南、北部海疆,以及东北、北部、西北、西南陆疆,逐渐形成了包围中国之势,以领土掠夺、经济侵略和寻求政治特权等作为其主要目标。东南沿海藩篱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均被突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海路北上,在天津北塘登陆攻陷北京,北部海防漏洞暴露无遗。而美国一直在打台湾的主意,于1867年两次武装登岛。自19世纪中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后,沙俄便将目光放回亚洲,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打开中国北方边防大门;还在西北与英国争夺在新疆通商、驻使、置地等权益。英法于19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开始对中国西南周边部分国家进行殖民统治,而后便借助地缘优势意欲将势力范围渗入中国云南、广西和西藏。日本也逐渐活跃,不仅与沙俄争夺本属于中国的朝鲜宗主权,还在美国支持下于1874年登陆台湾。
多年经营铁路的经验使西方国家对铁路的基本和附属价值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正如列宁所揭示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铁路)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因此,为掠取资源、占领市场、侵略主权,自19世纪下半叶起,通过铁路进行扩张成为列强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一环,铁路也自然成为列强侵略中国边疆的战略工具。他们不仅在中国周边国家规划和铺设铁路,还通过外交施压甚至是战争等方式不断要求中国对其开放边疆地区的探路权和筑路权。
1858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Muravioff)提议,为加强沙俄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开发西伯利亚,应修建一条从莫斯科通向太平洋的铁路,连接莫斯科和中国黑龙江地区。这一建议受到俄廷赞同,但因财政拮据而被搁置。之后,类似的计划被一再提出,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19世纪八十年代起,沙俄铁路计划开始付诸实践。1885年,一条从叶卡捷琳堡到秋明的短途铁路建成通车。这条铁路虽然不长,却跨越了亚欧分界线乌拉尔山脉到达西西伯利亚平原,是沙俄铁路东进第一步。之后,俄国工程师阿斯特罗夫斯基(Ostrofski)提议将该铁路东延并修筑三条支线,以便于开发西伯利亚,进而侵略中国。1886年,这一计划变得更为明确。沙俄开始筹划修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由西部的车里雅宾斯克一直修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旦通车,俄国便可用最快速度将武装力量运达中国西北及东北边疆地区。
1858年,英国退休军官斯不莱(R. Sprye)提出,为方便对华贸易、提升英国在华商业竞争能力,应修筑一条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由于当时英国还在全力迫使清廷进一步开放东南沿海,官方未对这一建议进行有效回应。1862年,英属印度又提出修筑一条由仰光沿伊洛瓦底江,通过缅甸八莫到达云南的铁路,这一计划在英国国内受到大力支持。1875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向清廷施压,最终与中国签订《烟台条约》,获得入侵云南的特权——清廷允许英国在1877-1882年间派驻官员在云南察看通商情形,并保留由英属印度派员赴云南之权。除了考虑从缅甸出发,英国也在寻找从英属印度出发到达云南的路径,于1878年规划了一条从印度阿萨密省出发到达云南怒江的铁路,还派人到中国进行实地勘测。不仅如此,在与清廷签订的《烟台条约》中,英国还设法增加了一条西藏专条,允许英国派探路队由北京经甘肃、青海或四川等地进入西藏,或由印度进藏,为英国势力深入西藏探路提供了合法依据。之后英国便频繁派人进出西藏。1881年,英国选择印度铁路干线东孟加拉铁路线上的西里古里作为起点,修筑了一条通往位于喜马拉雅山区大吉岭的铁路。借助这条铁路,英国人能够在一周内从加尔各答到达西藏边境。而法国的筑路战略则更加明确。19世纪中后期,为掠夺矿产等资源,法国一直在筹划修建一条从法属印度支那通往云南的铁路。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通过《中法和约》取得了在越南北部修筑铁路的权力,之后又谋划继续将越南铁路接至中国云南。
(二)国人对列强筑路动态的评析
国人对于列强在中国周边的筑路动向十分关注。19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申报》刊载了多篇有关铁路的文章,及时报道了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沙俄的铁路建设动态,并分析其动机。1879年,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马建忠在《铁道论》中对列强在中国周边的筑路动向有着清晰的描述:“环中国之疆宇无非铁道也。英由印度北行,且逾廓尔喀而抵克什弥尔矣。俄越乌拉山岁造二三百墨里,行且至代什干而逼敖罕矣。法肆并吞安南之谋,已侦谍洮江、富良江之源,而直入滇省规为铁道之图矣。英人复由披楞之东,行且与缅甸接壤矣。倭人力效西法,新旧二都已绵亘铁道而睥睨东溟矣。俄人踞图们江口立电报,由恰克图以径达俄都,行且筑铁道于黑龙江滨以通挽输矣。”并感叹如果中国和列强发生战争,列强军队到达中国边疆地区的速度将大大快于中国:“将不数年,各国之铁道已成,一旦与国失和,乘间窃发,而吾则警报未至,征调未齐,推毂未行,彼已凭陵我边陲,挖扼我腹心,绝我粮饷,断我接济。”
国人对列强的筑路动机也有十分理性的分析。认为一在于经济侵略,二在于政治侵略。经济侵略以掠夺资源以及倾销商品为主要目标,而政治侵略则以军事扩张以及武力殖民为主要目标。在时人看来,经工业革命迅速崛起的英国和法国,其筑路目的更多在于经济侵略,看重的是云南和西藏的丰富资源和商品市场。1880年4月,《申报》报道了法国的铁路计划,认为其主要目标在于贸易:“昨阅香港报知法国……又拟在通商之处建设火车铁路以便往来。其路西则通至暹罗,北则通至云南。总期有利于贸易。”作者认为法国通商云南的计划由来已久,“盖法人久欲通商于中国云南省,惟因道途崎岖转运不便,故隐忍以伺”,并且担心“若中国更许其建筑车路,以达于两粤滇黔,则贸易从此可期日增月盛,此尤法人之素志而思”,并感叹“一旦如愿以偿者也,呜呼,时事如此,我中国得毋有鞭长莫及之嗟乎?”
然而,对于沙俄而言,他们规划的线路大多途径的是人迹罕至的地区,在铁路运营初期的经济收入并不多。因此,军事侵略才是沙俄的主要目的。1879年1月,《申报》在分析俄国规划铁路的意图时,认为从1854年到1877年间,俄国铁路总长度从2250里增至32000里,与西方其他国家发展铁路以“首重便商,次则利国”不一样,“揣其用意所在,专为调兵运粮计。”这是因为俄国在1854年“与英法土三国战争,以铁路无多,转运延缓,遂至兵挫地失。于是筹贷国债于二十三年中添造铁路三万余里,今已无往不利矣。”并提出中国应当预防俄国,“俄国铁路若达中国西北境,中国必当预为筹备,如期不然,一旦兵衅或开,必受其敌。”
(三)自筑铁路可以巩固边陲
在这种形势下,尽管在19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考虑到铁路具有破坏传统以及“资敌”之嫌,国人在总体上对修筑铁路的事宜持反对态度,但也有部分国人意识到铁路在军事国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开始转变对铁路的反对态度,认为铁路可以起到固边的作用,将自筑铁路视为缓解边疆危机的有效手段。这部分国人主要由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以汉人督抚为主的洋务派官员以及开明舆论媒体人士构成。
那么,在他们看来,铁路是如何起到固边作用的呢?首先,铁路便于转运部队和军饷。1879年1月,《申报》对这一作用阐述得十分到位:“而于用兵之际其用尤大,不捷而速军行若神,使敌国几疑兵卒从天而下。如遇一方有事,则三方之兵可以咸集。轮车之利,不其薄哉?”。并且,铁路可以避免士兵因长时间赶路而损耗,还能够保证军队漕粮、军火的补给。“调兵赴援则兵丁已属疲敝,以敌之逸来我之劳,我即士精器利,而当其时已仅存十之五六。有铁路则朝发夕至,师不劳顿,而行途迅捷,壮气自必加倍。”其次,铁路有助于建立防务体系,不仅有利于边防,还利于海防。“倘海疆有事,传电线以报,邻省用火车以运救援,千里之远,数日可到,何至如中国向来之濡滞千里之隔,至速亦须一月也。”1874年,清廷在台湾与日本不战而败。当清廷花费很大力气将军队运到台湾时,战争早已结束,这使李鸿章意识到军事调遣迟缓是中国海防的巨大缺陷,在《筹议海防折》中主张修筑铁路配合海防:“有事之际……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海边),闻警弛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除了直接防御,铁路的修筑还可以间接起到遏制列强野心的作用。这是因为铁路能够带动国家的采矿业发展,并提升沿线经济水平,有利于军工和商业的发展,从而提升综合国力,最终达到威慑列强的效果。1872年10月,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提及边疆形势严峻,“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认为解决的办法就在于壮大自身,“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最终,在多种原因和力量的共同推动下,1895年7月19日,光绪帝发出上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此应及时举办。”至此,清廷官方终将大规模自筑铁路定为国策。
二、军事固边:国防铁路的基本功能
将大规模修筑铁路定为国策后,晚清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筑路高潮。由清廷修筑的国有铁路4955.9多公里,其中不少是依据“由腹达边”原则——即从中心腹地到边疆地区的国防铁路干线。除去干线,部分疆臣也在筹划修建边疆区域内部的边陲铁路,但几乎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去客观条件制约,晚清国防铁路实践还受到以“守中治边”为代表的传统治边经略的影响。
(一)“由腹达边”的干路
先修筑由腹地通往边疆的铁路干线,是晚清铁路支持者们的共识。1880年,刘铭传在《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中规划了三条主干线,其中一条北路即为“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1889年,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在《复陈议办铁路折》中提出,应先修筑东西两条国防铁路干线:东线自天津出山海关至黑龙江,复修支线至吉林宁古塔;西线自陕西、甘肃、至伊犁,复修支线至南疆喀什。1907年,邮传部奏《筹画全国铁路轨线折》更是明确了这一原则:“就今筹之,当首定京城为轨枢,而区分海内诸轨为东西南北四大干。四干既定,循而求枝”。
东北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是其最为看重的边疆地区,却受到了沙俄和日本的双重威胁。1889年,为防御沙俄正在规划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清廷决定移缓就急,暂缓卢汉铁路、先办“能控制海防、兼顾边防,于大局深有裨益”的关东铁路,将唐津铁路向山海关外延伸。1911年,关东铁路北京至沈阳段全线通车,并更名为京奉铁路,干线全长843.1公里。其中,北京—山海关段也构成了北洋海陆联防体系的东段。京奉铁路是晚清联通关内外最重要的铁路,与诸多国有干线相通,途径华北和东北地区几大城市。遗憾的是,京奉铁路虽为国有,却因借英款修筑而丧失了部分管理、会计、运营等权力。并且,由于日本干涉,京奉铁路没修筑到原计划的靠近东北边境的珲春,减弱了其固边价值。
在北京的西北方向,沙俄对蒙古地区也虎视眈眈,并且于1891年动工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途经靠近西北边疆的七河地区。为此,清廷计划修建两条干线通往西北边疆。一条干线为纵干线,自北京通往西北边疆的必经之地——塞上重镇张家口起,经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赛尔乌苏、库伦(今乌兰巴托)至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一条干线为横干线,由洛阳经西安、固原、兰州、甘凉、嘉峪关而达新疆。1909年9月,纵线第一段的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通车,全长273公里。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条完全自建自办的铁路,京张铁路的路权完全属于中国,其建成通车后大大带动了沿线贸易的发展以及华北人口向西北的流动,但由于其仅仅处于西北国防干线的第一段,因此其在晚清的御边价值也不甚明显。其后,在京张铁路北延线的线路选择上,邮传部最终选择了张绥铁路(张家口—归绥)。1909年10月,张绥线开工,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断,通车至距离张家口125公里的阳高。鉴于铁路汴洛铁路(开封—洛阳)已于1904年动工,1907年,清廷批准民间集资接修汴洛铁路至潼关。1909年,汴洛铁路竣工,全长183.8公里;1910年,洛潼铁路开工,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修至新安县铁门段。
(二)边陲铁路筹划的失败
除去“由腹达边”的铁路干线,晚清部分疆臣也主张修筑边陲铁路,即边疆地区区域内部的铁路。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曾从稳固广西边防角度提出在广西自筑铁路的必要性——“故在往昔,但得一能办匪驭兵之员,已胜边防之任,而在今日,则非能练兵、能交外而又明于铁路建筑之学者,则不能先事以防觊觎,后事以收利权”,并举荐郑孝胥来负责广西边防及预筹将来造路事宜。1908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在《广西边防关系重要应行筹办大端折》中论述了桂邕铁路(桂林—南宁)在广西边防中的重要地位,提出“非亟筑铁路不可”。1906年,四川总督锡良与驻藏大臣有泰向清廷提出修建川藏铁路,认为此路既可以开发西藏的商业利益,还可以杜绝英人的侵略企图,受到后来新驻藏大臣联豫、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等人的支持。同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在《江省创修铁路藉固边防折》中提出,为抵抗俄人所筑东清铁路以及振兴商务,奏请清廷修筑黑省铁路,达到“商务之起色可翘足而待,即经营边防易措手矣!”。之后便着手修筑自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昂昂溪的齐昂轻便铁路。这条长度为28公里的短距铁路于1909年竣工,但由于是设备较为简陋的轻便窄轨,在运输条件、运价、运量等方面均受限制,因此发挥作用有限。1909到1911年,锡良在管理东北三省事务期间,一直在筹划锦瑷铁路(锦州—瑷珲),认为该路可以达到兴地利的效果,并且认为实边与守土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提出“非实边不能守土,非兴垦不能实边,非移民不能兴垦,非保安不能移民。”
然而,除去齐昂轻便铁路,他们的计划几乎均以失败告终。客观来讲,铁路的修筑受到资金、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限制。在铁路建设的起步阶段,暂缓边陲铁路的建设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并且,大部分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当时铁路技术的水平也限制了当地的铁路发展。在回应建设川藏铁路请求时,邮政部提出:“此路绵延甚长,工程险隘,不惟巨款难筹,且道途阻隔,筹办完全铁路甚难急切图功”,并建议“暂行敷设军用轻便铁路,以期简而易行”。当然,这个轻便铁路的计划最后也因种种原因未能施行。最重要的是,除却边防目标外,边陲铁路也要考虑经济上的需求,而此时边疆地区内部的经济条件还没有发展到对铁路有极大需求的程度,若贸然在边地修筑铁路,不仅投资大,收益也慢。况且,筑路经费也十分有限。在具体操作层面,晚清最终选择了“择要而图”“逐渐兴办”的思路,也是符合铁路发展一般规律的。因此,在晚清国防铁路筑路实践中,“由腹达边”的铁路干线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1889年1月,李鸿章在反驳翁同龢等人“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边地有运兵之利、无扰民之害”的观点时曾说道,“所贵铁路者,贵其由腹之边耳;若将铁路设于边地,其腹地之兵与饷仍望尘不及。”从经费造价来考虑,“铁路设于腹地”,可“运兵”,可“贸迁”,还可拯救“水旱遍灾”,便于“移民移粟”,其经济收益较边地铁路更为丰富。因此,“是铁路不仅边地用兵之利也。”1911年,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在《复陈铁路明定干路枝路办法折》中明确了清廷官方对于边陲铁路的态度:“近年以来,边防日亟,疆臣辄以筹造边陲铁路为救国第一策。然欲修边路,必先通腹路;若不有腹路征调之神速,何以固边路之防护,不有腹路营业之进款,何以供边路之修养?今我置内地干路为不急之务,而欲侈谈国防,是何异建高楼而不平其地,浚百川而不探其源也。”可见,在筑路的顺序上,干路一定是先于边路的,这一考量具有现实合理性。
(三)传统治边经略对晚清筑路的影响
除了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晚清修筑国防铁路的原则和实践,也受到了传统“守中治边”经略的影响。那么,应如何理解这一影响呢?
自古以来,边疆地区都被视为王朝国家的外部防御区,而位于政治和经济中心区域的腹地才是核心拱卫区。传统治边经略奉行“守中治边”原则。重中心,轻边陲。通过中心的安全繁荣,对边陲恩威并施,实现边陲的稳定,边陲拱卫中心,最终实现“天下一体”。显然,这是一种以军事固边为主要目标的治边观念,强调的是边陲政治稳定对于中心安全的意义,而非边陲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这种观念反映在在铁路上,修筑铁路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腹地的安全,特别是京师的安全,因为“外夷不守,防守将移在内地而费益不赀”。1880年12月,李鸿章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明确说明铁路便于京师:“京师为天下根本”“若铁路既开,万里之遥,如在户庭;百万之众,克期征调。四方得拱卫之势,国家有磐石之安,则有警时易于救援矣。”1881年1月,《申报》谈及铁路的规划问题时,也强调应高度重视政治原则:“就拱卫畿辅之形势与布政行令之重大言之,凡省会与省会,近省与京都相通之地,似宜各有铁路一道。”边疆地区是维护内地安全的重要屏障,为了保证战争远离核心拱卫区,就必须要将敌人控制在外围,从而达到“御敌于千里之外”的效果。因此,国人最为重视的是铁路转运兵力、漕粮、军火的运输功能。一旦别国从边境进攻,腹地兵力可快速支援边防,而后续支援和补给也可以及时送达。1907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上《铁路亟应统筹全局预划轨线折》,其中就明确说明边陲铁路的主要价值在于军事:“用路有军国、商家之别,造路即有计画、建筑之分,揣度情形,大抵繁盛之都,便于商家,而见利较速;荒遐之野,便于军国,而见利较迟。”并且,为了避免外敌从边地长驱直入的“资敌”之嫌,清廷对待边陲铁路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1911年,在讨论由法国提出的龙州铁路事宜时,广西巡抚沈秉堃致函外务部,认为“查铁路办法,宜由腹达边,桂路未经兴修,先成龙州,徒利外人,于我无益,且恐有损。”
晚清之所以对边地开发不甚重视,也没有将边地开发与抵御列强结合起来考虑,仍然延续了清朝一直推行的“以弱求安”的治边战略,是其“内重外轻”固有观念的延续。这一点可以在1880年刘铭传《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中得到印证。19世纪80年代初期,刘铭传作为倡导筑路的先锋,在呼吁清廷筑路时,曾列出如下一则理由:“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由此可见,这样“不为疆臣所牵制矣”的“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确实是当时清廷最看重的。在清朝前期,为维持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做强,清廷明确限制了东北和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开发,并且禁止流民通往边疆。
在这种“以弱求安”的治边理念的影响下,他们很难意识到随着“夷夏之防”变为“中外之防”,薄弱的边地根本无法抵御列强,而只有促进边疆发展,才是强边固防的长远之计。当然,晚清在边地管理上也在尝试改变,开发边地的观念也在逐渐萌芽。从1880年开始,清廷实行部分开禁,在蒙古、东北等边地开展“兴边利”实践,推行移民垦荒政策,加速了人口向边地流动。然而,清廷“兴边利”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真正实边,而是侧重于收取租粮、敛财济困,从而减轻治理各藩部的压力,因而没有得到边疆积极响应,收效甚微。可以说,晚清在解决边疆危机时,主要还是把军事固边放在首位,没更多地关注边疆地区的发展。
三、治理兴边:铁路应对边疆危机的新途径
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西方列强依靠铁路划分势力范围,导致边疆危机愈演愈烈。东北边疆地区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分别被沙俄(后为苏俄)和日本控制,西南边疆的滇越铁路也被法国控制。而从晚清就开始萌芽的治理兴边理念,在民国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形成在当时社会讨论度颇高的思潮,时人一致明确边疆开发对国家发展意义重大,而铁路的铺设,不仅具有军事固边的功能,而且具有治理兴边的功能。于是,国人将治理兴边作为铁路抵御列强侵略和稳定边疆的另一途径,开始了新一轮的筑路实践。
(一)通路后的边疆形势
20世纪初,铁路的贯通给部分边疆地区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可谓转机与危机并存。一方面,尽管晚清修筑铁路干线的主要目的为提升国家军事实力,却在实际上增长了边地的人口数量,带动了边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铁路仍是西方列强对华扩张的战略工具。他们继续在中国周边铺设铁路网,并且还掠夺了部分边疆地区的铁路路权,特别是在东北和西南边疆,这一情况变得尤为严重。
人口是边疆繁荣稳定的基础。20世纪初,京奉铁路和中东铁路的逐段通车为关内人口“闯关东”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来自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人口“闯关东”不再受气候的限制,东北地区人口激增。据统计,1886年,奉天、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人口总数为1200万,1912年达到了1974万。为鼓励人民前往东北和西北,交通部门在津浦、北宁、平汉、平绥等国有铁路都有减价优惠,人流多时还开行专列运输。支线也有减免优惠,例如1908年《黑龙江沿边招民垦荒章程》规定“来江垦户……其由……昂昂溪至齐齐哈尔之官办铁路均一律征收半价,其随带眷口概免收费”。在西南边疆,法属滇越铁路通车后也使滇东南区域的常驻人口成倍增长,许多旧的城镇变大,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城镇。例如,滇越铁路线上的碧色寨站原本只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却因为铁路的通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流量极大的城镇。铁路也带动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增长。已通车的铁路不仅带动了沿线经济发展,而且依靠自身盈利为继续筑路提供资金,形成以路养路的良性循环。以京奉铁路为例,奉系在接管京奉铁路的山海关—奉天段时,每年收入至少在500万元以上,这笔资金成为后来东北铁路发展的启动资金。在西南边疆,法属滇越铁路的修建也在客观上使云南出口贸易额连年攀升,仅1912年一年的出口贸易额就达到2200多万关两。
然而,在同一时期,列强并没有停止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通过控制边疆区域的铁路掠夺了中国大量的资源和财富。沙俄在1896年通过《中俄密约》获得了租借辽东半岛以及在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的权利后,于1897-1903年修筑了一条与京奉铁路平行的东北大动脉——东清铁路(1920年后名为中东铁路)。利用该路,沙俄掠夺了东北地区大批林业及矿产资源,并且通过过境转售农副产品、倾销纺织品等方式获得了大额利润。1904年,日本因不满沙俄势力扩张而发起日俄战争,获得了东清铁路南段的路权,将其改名为南满铁路。之后,日本又于1908年取得了吉长铁路(吉林—长春)的管理权和会计权。1909-1912年,日本擅自将其在日俄战争期间修筑的临时窄轨铁路安奉铁路(安东—沈阳)换成标准轨,与朝鲜境内铁路相连,形成一条以釜山为起点的亚欧大铁路。除了通过经营铁路大量揽财,日本还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置铁路附属地,不仅对当地居民强制征税,还大量掠夺了当地矿产、森林、农业等资源。在西南边疆,中法战争后,法国于1910年完成了滇越铁路(越南海防港—中国昆明)的铺设,经过河口、碧色寨、开远、昆明等站点。法国不仅对经铁路进出口的货物收取高额运输费及关税,还不断向云南倾销洋货,导致云南的棉纺织工业与小手工业大量破产。为掠夺更多利益,法国破坏了云南传统种植结构,诱导当地农民放弃粮食种植,改种烤烟和罂粟等经济作物,导致当地鸦片泛滥,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安定。
(二)兴边亦可固边陲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晚清就开始萌芽的治理兴边理念,在民国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形成在当时社会讨论度颇高的思潮。从1912年开始,一些致力于移民实边、开荒拓殖、普及教育的民间社团组织纷纷成立,例如黄兴等人创办的“中华民族大同会”,黎光薰等人发起的“五大民族生计会”等。治理兴边的理念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从1914年开始,北洋政府与掌管边疆当地的军阀就在不断推进内蒙古、东三省、直隶、西康、青海、新疆等地的垦务进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将开发边疆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之中,还成立了蒙藏委员会、西北建设委员会等来专门负责相关事务。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开发边疆的计划和政策,例如1929年《关于蒙藏之决议案》、1930年《开发康藏交通邮电计划案》等。
随着东北边疆形势的逐渐严峻,开发治理尚未被列强过度染指的西南和西北边疆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达到高潮。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通过《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生计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针案》,明确说明“边地开发屯垦与移民实边,为发展国民经济之重要方针。”特别是对西北边疆的开发,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一度成为了南京政府的重要战略,他们还有“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打算,并相继推出了1932年《开发西北案》与1935年《西北国防之经济建设案》。
之所以如此强调治理兴边,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国人已经在反思传统的“重防卫轻开发”的边疆经略,认识到除了传统的运兵应援,开发和治理边疆也可以达到稳固边疆、保卫腹地的政治效果,是巩固国防的另一途径。而且,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也必须建立稳定的后方基地。大西南、大西北因此而成为开发建设的重点区域。1937年,学者方秋苇在《非常时期之边务》中对国防性质进行了分类,一类为“文化的国防、产业的国防、精神的国防”;一类为“军事国防”。不难看出,此时国人已经明确认识到治边只是与军事国防相对应的另一种国防方式。1941年,蒙藏委员会理事周昆田专门撰写《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角度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边原则进行了阐释,将边疆开发的内涵锁定在政治、经济、文化开发三个层面。1943年国民党行政院在讨论边疆开发计划时曾提出,边疆开发意义在于“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即政治建设应先从经济着手发展经济事业,并以商业方式运作”。这说明国人已经意识到,只有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真正地发展起来了,国家才会更加团结、民族才能更好融合,国防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抗战大后方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至于如何开发边疆?交通建设自然成了有识之士的重要目标。而无论是通往边疆的交通建设,还是边疆内部的交通建设,都与铁路建设息息相关。1912年,孙中山初步提出了修建通向边疆的铁路规划。“从上海至伊犁,将敷设干线一条。另一条由广州至喀什噶尔。又另一条由广州至西藏,取道云南。”1919年,他又在《建国方案》中详细地提出了修建东北、西北、西南、高原铁路系统的铁路蓝图。在他看来,开发边疆的富源,必须先修铁路。边疆开发与交通建设是紧密结合的。“殖民蒙古、新疆,实为铁路计划之补助,盖彼此互相依倚,以为发达者也”。在孙中山之后,交通建设也一直是国民政府促进边疆开发的重要目标。1929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孙科提出要完成陇海线、粤滇线、包宁线;1931年,国民政府制定的铁路“五年建设计划”,就西北线路网和西南线路网进行了规划。1937年,国民政府还制定了《琼崖铁路计划书》,计划在海南岛内修筑一条长约450公里的铁路(那大—榆林港)。
不但要把铁路修到边疆,时人也有进一步与周边国家的铁路接轨的主张,例如孙中山曾提出要在主权平等基础上开放铁路市场和进行铁路国际合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打通西南、西北国际交通线,接受国际战略物质援助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因此,国民政府为因应国防需要,计划将铁路延伸到其他国家。例如,1935年国民党五大通过的《西北国防之经济建设案》中规划了“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提出“湘桂路告成后,可由粤汉路经镇南关而通至安南。川滇路告成后,可以四川物产经由昆明而向安南输出。西北铁路如能经由新疆以通中亚,亦甚有裨益”。从长远目标看,战后国家建设也需要我国边疆铁路与邻近国家的铁路对接,使边疆地区成为国际合作的桥梁。从外交上看,面对日本、德国的侵略战争,世界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高涨。在中华民国与苏俄复交之后,一些知识分子提出建设新亚洲的设想,主张以铁路为纽带加强亚洲国际合作。例如1940年,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在《新陪都之重庆》一文中指出:“大亚细亚主义之真正意义,即在中国、苏联、印度、土耳其四国之圆满合作,而其先决条件,尤在大陆国际路线之开通与充实。”
(三)铁路治理兴边的实践
在铁路治理兴边的具体实践上,率先行动的是边疆区域内的官民。清朝覆灭后,北洋政府的控制力变弱,地方军阀在政治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经济上也变得更加自给自足,这就为边疆地区的官民自主筑路创造了条件。在他们看来,铁路的功用不只在于运兵应援,更在于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从而在根本上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御力量,达到抵御列强的效果。从20世纪十到三十年代,面对列强不断在边地筑路、侵犯中国主权和利权,边疆地区的官民转变了以往 “破坏”他路的方式,转向了一种理性的、经济的手段,开始以国营、省营、民营等各种方式自建自营边疆区域内的铁路,希望以此打破列强垄断当地铁路建设和运营格局、避免铁路利权继续外溢。其中,西南和东北边疆的成绩较为突出。
法属滇越铁路通车后,滇省人民不断声张路权。1915年,面对滇越铁路公司的苛待与加价,以及为了阻止法国人接造滇越铁路支线,并解决个旧大锡出口的内地段运输线问题,蒙自、个旧、建水、石屏的士绅商贾们上书政府,强烈要求自筹资金修筑一条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人的铁路——个碧石铁路。在云南都督蔡锷的支持下,个碧石铁路于1914年动工。1921年,个旧—碧色寨段完工,成为滇越铁路的延线。1936年,全线117公里完工,将滇南个旧、建水、石屏等城市连成一线。
面对日俄,特别是日本在东北的扩张,经营东北的奉系政府决定自建自营铁路来开发东北,并制定了以路治边的治理战略,将修建铁路作为增强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主要手段。从1923年到1927年,在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东北地区以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方式修筑了奉海、吉海、呼海、大通四条干路以及数条支路,建设铁路总长度约1800公里,形成了大规模的自主铁路网。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持东北大局,以葫芦岛海港为中心建筑了三条铁路干路和数条支路,共计660多公里。
边地铁路的兴边效果显著。个碧石铁路运营上以货运为重点,收入连年以几何倍数增长。并且以出口个旧大锡带动了个旧矿冶业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个旧矿冶业步入现代化生产,并带动了整个滇南区域的发展,在收回铁路利权方面成绩斐然。奉系铁路运营上选择了干线联运、客货联运、降低运价等经营方式,收入剧增,给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经济效益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边疆地区官民应对列强挑战的能力,在与列强的对抗中也能保持较为强硬的态度。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奉系在建筑铁路问题上基本持强硬态度。在修筑打通铁路(打虎山—通辽)等路线时,日本曾多次抗议和干扰,对此,奉系政府基本上呈消极回应的态度,并运用传统的“以夷制夷”方式,利用日俄关系为自身寻找空间。
南京国民政府在边疆铁路的修筑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西北地区,展筑了陇海铁路,并开始修筑甘新铁路、天成铁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撤到重庆后更是加紧了西南地区铁路的修筑,完成了湘桂铁路、黔桂铁路的铺设,并开始修筑滇缅铁路、叙昆铁路。然而遗憾的是,受现实制约,修筑这些铁路主要是为了备战和抗战,对于战时运输、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较大作用,客观上对于开发边疆至少在当时并未展现出太多的功效,而南京国民政府在边疆开发上主要还是依靠更为便利的公路建设。
结语
通过梳理近代国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时对铁路的认识变化及实践,可以发现,铁路在晚清阶段主要以单纯的军事固边为主,而在民国时期则受到现代治边观念的影响,增加了治理兴边的功能。19世纪末,在“中外之防”的大背景下,通过铁路来运兵应援、拱卫中央,以此缓解近代边疆危机,是晚清政府决定修筑铁路的重要动因。20世纪初,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筑路高潮中,国人所修的国防铁路干线给边疆安全带来了转机,不但促进了边疆地区人口增长,还拉动了沿线经济发展。然而,受“守中治边”“以弱求安”等传统治边原则的影响,清廷最为重视的还是铁路转运兵力、漕粮、军火的运输功能,把军事固边放在首位,没有更多地关注边疆地区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这一僵化保守思维和态度,除去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部分疆臣在边疆内部修筑铁路的筹划一再落空。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西方列强的铁路也延伸到了中国边疆地区,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和挑战。进入民国后,面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局势,并受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国人开始总结和反思传统“重防卫轻开发”的治边经略,逐渐产生了治理兴边的意识,将开发建设边疆视为缓解边疆危机、巩固国家统一的长远之计和根本途径,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系列边疆铁路发展规划,开启了新一轮筑路实践。为此,边疆官民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修建了一批边疆或由内地通往边疆的铁路,对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较大作用,总体上对边疆地区工农业发展也有所促进,对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增强防御能力大有裨益。通过对近代边疆危机背景下铁路功能演进的梳理,既有助于厘清近代铁路发展规律,也可透过铁路深化对近代边政思想的理解,对当今铁路发展和边疆治理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民族学刊》2021年第1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