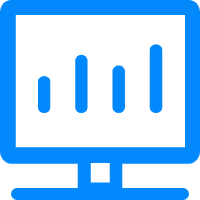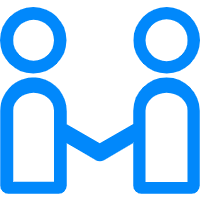王元崇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by Nianshen So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320pp
宋念申博士的《在近代东亚制造边界:图们江划界,1881-1919》一书(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以下简称《制造边界》),以中国的晚清到民国初期中韩日三国围绕图们江北岸新垦土地和移民的归属问题而展开的划界活动为中心,利用中、韩、日、英等多语言档案资料和实地调查报告,展现了近代东亚世界在多重因素之内动态地制造、界定和再界定国土、国家与国民之边界,揭示了这种围绕边界的流动的历史与东亚世界中传统的宗藩秩序、近代日俄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地域和全球资本主义、近现代东亚主权国家形成之间的密切联系。
《制造边界》不仅是目前为止英文学术界中唯一一部探讨近现代中朝图们江划界历史问题的专著,更是中外学界第一部以中朝划界为个案来多维度审视近现代东亚地区的国土、国家和国民深刻演变的优秀作品。《制造边界》自出版以来,备受学界瞩目与好评,饱含赞誉之英文书评见诸《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专业旗舰学刊,目前韩文版亦在翻译之中。唯中文学界,尚乏细致的介绍与评论,故本文之作,非为踵事增华,实系抛砖引玉。(注:本文“中朝”的“中”,英文中只是China一词,下文视具体语言环境分别指代清代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朝”字系英文中的Korea一词,本文中亦分别指代朝鲜王朝、日据时期朝鲜半岛、二战后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韩”字之使用亦同“朝”字,惟有时泛指朝鲜半岛或朝鲜民族。)
一、《制造边界》概要
《制造边界》一书除前言、结论和后记之外,正文凡六章。第一章“越界:图们江地区的社会生态”(Crossing the Boundary: The Socioecology of the Tumen Reiver Region),分析了为何图们江北岸成了跨界移民的首选目标,以及这一地区缘何迅速成为当时代东亚世界纠葛的中心之一。第二章“王朝地理:作为修辞之划界”(Dynastic Geography: Demarcation as Rhetoric),展现了中朝两国自康熙穆克登查边到光绪年间共同勘界期间,彼此运用宗藩术语维系自身的立场,呈现了这种“王朝地理”在宗藩框架之内的双刃剑一般的张力,并与同时期发生的中俄重新勘界与中越重新勘界做了横向的对比。第三章“制造‘间岛’:跨界社会之流动性”(Making “Kando”: The Mobility of a Cross-Border Society),从微观史的角度考察了图们江北岸的跨界社会在土地开垦和租让、租客身份与民族关系、多边贸易、盗匪与社会治安等多个角度的面向,展示了一个正在形成中的边疆社区的流动性质。“间岛”一词是1880年代左右朝鲜移民潮的过程中,移民对图们江北岸中国领土的称谓,中方并没有这种叫法。第四章“驯服边疆:治国术与国际法”(Taming the Frontier: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Law),中、俄、朝、日四国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初针对图们江北岸地区进行管理的,多国政治力量的介入对边地形成了一种“去边疆化”(de-frontierization)的过程,同时却又是“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重新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双重动态进程。第五章“重塑之界:一种多层竞争”(Boundary Redefined: A Multilayered Competition),呈现了一种1910年代前后多重力量对边界的激烈塑造之中,围绕“国家角色”或曰官方因素和“非国家角色”即非官方因素对边界的界定,展示了中国的边务督办公署和吴禄贞的努力,日本政府的殖民主义策略,分析了中日在国家层面、行省层面以及当地社会层面的诸多冲突。第六章“重塑之民:延边的认同政治”(People Redefined: Identity Politics in Yanbian),从土地的角度转到人的角度,分析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在延边的朝鲜人面临的史无前例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背后的政治。《制造边界》一书的故事,始自1881年朝鲜流民大批越江到达图们江北岸,终于1919年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三十八年看似短暂,却是近现代东亚世界在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之前激烈角逐的时期。正如结论部分中所提到的那样,“吾土”(our land)与“吾民”(our people)在这一期间被不断地重塑(264页)。
中日韩学界对《制造边界》所探讨的议题已有诸多先行研究,例如张存武、杨昭全、权赫秀、李花子、(韩)金明基、(韩)金衡钟、(韩)金宣旼、(韩)殷丁泰、(日)名和悦子等同仁的著述,都对清代到民初的中朝查边、共同勘界和中日“间岛问题”谈判,做过十分详细的文献考证、实地考察与多边角度的论述。其中,杨昭全的《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陈慧的《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中央编译社,2011年)、李花子的《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朝清国境问题硏究》(集文堂,2008年)(韩文)、《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年)以及相关的考察日本“间岛问题”的论文等等,既有从历史文书中钩沉掘隐,又有配以实地的勘察,将这一中朝边界问题的研究在二十多年之间推到了一个学术高潮,且不限于清代和民国时期,而是上溯到了明代及之前。最近刁书仁的《中朝疆界与民族:以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末为中心》(秀威资讯科技,2018年)以及刁氏与王崇时之《古代中朝宗藩关系与中朝疆界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可为此种趋势之代表。当代韩国学界的很多学者也对图们江勘界问题持有绝大的兴趣,首尔大学金衡钟博士的《1880年代朝鲜—清国境会谈相关资料选译》(1880년대 조선—청 국경회담 관련 자료 선역,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2014年)(收录了二百二十份档案,多达一千一百六十三页)及其《1880年代朝清共同勘界及国境会谈研究》(1880 년대 조선 청 공동감계와 국경회담의 연구)一书(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2018年),以及高丽大学金宣旼博士的英文专著《人参与边土:清鲜之领土边界和政治关系,1636–1912》(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1636–1912,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均系这方面的代表作。
当此研究背景,《制造边界》并不是要用英文去重复在中日韩学界业已十分清晰之历史线索,而是在每一部分内都深入讨论多重边界在多重力量作用之下的塑成。就此而言,《制造边界》呈现了与包括中日韩美学界在内的既有学界研究非常不同的理路,任何一位阅读《制造边界》的读者,并不会因为前贤之研究而感到重复或枯燥。《制造边界》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它不是要通过某种先入为主或者固定化的立场去表达某种为特定国家或者民族所偏好的、单一的声音,而是多角度地呈现了围绕图们江划界之事上的多种力量和多种声音,表现了一个多重面相交织在一起的流动的历史,很多从微观到宏观的观察都贯穿全书,不少章节内皆有会通地域史和全球史的分析。
二、作为多重边界的图们江北岸地区
《制造边界》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图们江北岸新垦地区,即中国的延边地区。朝鲜移民和后来的日本殖民势力称之为“垦岛”“间岛”,因近现代日本殖民主义势力殖民朝鲜半岛并深入中国东北的缘故,曾以所谓“间岛问题”而闻于世人,因此梳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是澄清此段外交公案的关键。
中朝两国自朝鲜王朝(1392-1910)建立的明朝初期开始,在接壤地区即以天然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二江皆发源于长白山地区,自天池周围开始,鸭绿江流向西南方向,入中国黄海,图们江流向东北方向,入朝鲜东海(即所谓“日本海”)。江源地带的边界划分则不甚清晰,这一地区又多系数百年荒无人烟之地,故长期以来并未有多少纠纷。两国之间很早就建立起了宗藩关系,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天朝、上国,朝鲜是诸侯所在的外藩、属国,此种关系也灵活调节着边务事宜。清代满洲政权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早在入关之前的1637年初就同朝鲜王朝建立了宗藩关系。1644年清政权入关以后,清室对“龙兴之地”的满洲以及长白山一带日渐重视,到康熙时期趋于顶峰,开始以祭祀五岳之礼祭祀长白山。为了彻底查明鸭绿江和图们江在长白山江源一带的情况,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一桩中朝越界案件为由头,派内务府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前往长白山查边,但因朝鲜方面不愿配合而未竟。
次年(1712年),康熙皇帝下令朝鲜配合穆克登查边,于是国王奉旨派出接伴使朴权与咸镜道观察使李善溥,连同译官金庆门等人,一起与穆克登前往长白山查看。穆克登一行兵分两路,穆克登自己在率领金庆门等人从南坡登上长白山天池,然后从南坡下山察查鸭绿江水源。鸭绿江源头距离天池较近,双方确认了胭脂川为鸭绿江源头。图们江源头则距离天池较远,双方经过一番察看后,穆克登接受了朝鲜方面的有关图们江自天池发源以后伏地百里而再出的说法,认定胭脂川以东的一条水沟(即日后的“黑石沟”)为图们江地下伏流所在地。穆克登等人首先主观认定了一处地方为“分水岭”,然后试图确定水源,最后指认距离天池正东方向几十里处的一条水流为图们江江源,这条水流就是日后所谓的“红土山水”,当年并没有“红土山水”之名来指代此水。穆克登等人在距离他们认定的分水岭不远的地方勒石树碑,碑文横书“大清”二大字,竖书正文曰:“乌拉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穆克登碑
穆克登查边立碑以后,朝鲜方面按照要求派员前来建设栅栏。然而,朝方官员发现穆克登所选的水流是不对的,因为这支水流往北流入松花江,而非图们江。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内部辩论之后,朝鲜方面决定不以此等小事烦扰上国(即中国),负责建栅的官员自行决定将木栅与南面一支水流连接起来,所以清朝方面自始至终对此事是完全不知情的(4-6页)。与此同时,在清朝查边的刺激之下,朝鲜开始重塑长白山在朝鲜本国历史中的地位,赋予之不同的意蕴(62-65页)。
(朝鲜王朝)金正浩1861年所绘制的《东舆图》之局部,上标有天池、定界碑(即穆克登碑)、分水岭、胭脂峰、水堆、木栅等地方。该图反映了十八世纪朝鲜方面的认识。
百年以后,连接图们江上游的木栅栏已腐朽无存,而更多的故事也由此开始。光绪七年(1881年),吉林地方官发现大批朝鲜流民越过图们江到北岸地区开垦种植,这里曾是皇家南荒围场,解禁后准备招揽汉人移民以为实边,但朝鲜人越边开垦者与日俱增,而且大多携有朝鲜咸镜道所颁执照。中朝双方遂围绕此事展开交涉,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一事被迅速挖掘出来,成为重中之重。当时,中国方面用“图们江”、朝鲜方面用“豆满江”来指代图们江(或写为“土门江”),而朝鲜方面的某些官员却声称,穆克登碑中所谓的“东为土门”的“土门”是指的是松花江的上游,不是指“图们”或“豆满”;换言之,朝鲜方面认为“土门”与“图们”/“豆满”实系二江,因此朝民越江开垦依旧在朝鲜属土之内,并非进入中国境内。实际上,“土门”“图们”皆系满文音译,与朝方所谓“豆满”,皆指一江,所谓“土门”另指他江者实系错谬(38-39页)。纠纷不决之下,两国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与十三年(1887年)进行了两次共同勘界。在第一次勘界过程中,朝方代表李重夏在树林之中发现了当年木栅与黑石沟相连的痕迹,二江说不攻自破,但他没有告诉完全没有发现痕迹的清方代表,而是秘密汇报给了汉城朝廷(74-75页)。朝鲜方面立即抛弃二江说,改口承认以图们江/豆满江为界河。第一次勘界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中方主张以江定界,朝方主张以碑定界,彼此不能说服对方,遂进行了第二次勘界。
第二次勘界声势颇大,集中在江源一带的具体边界认定,最大的成绩和最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于朝方确认了图们江系中朝两国的边界,确认了北岸地方属于中国领土,双方也都以安接流民为急务,在宗藩框架内未进一步纠缠。与此同时,朝鲜移民依旧大量涌入图们江北岸,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流民将这片土地称之为“间岛”“垦岛”,例如咸镜道茂山对面的图们江以北的垦区被称为“茂山间岛”,如此等等,创造了“间岛”这一后来被日本殖民主义大为利用并升格的术语。1902年,趁着俄国深入中国东北之际,朝鲜方面指派李范允为“间岛观察使”,后改为“间岛管理使”,侵入北岸地区,解散了清政府在当地任命的乡约,试图控制当地,但很快被清朝方面驱赶离境(140-141页)。清政府迅速在当地设立延吉厅,管理当地事务,但朝鲜也不依不饶地利用自身机构管理移民,双方的地方势力也出现了分化,彼此斗争不断。延吉厅在1909年为了应对日本的殖民侵入快速升格为延吉府,1914年升延吉道,使得中国内省的行政体系开始全面进入边界地区,这也就是《制造边界》中所谈到的“内地化”,以及针对朝鲜移民所采取的归化政策(129-137页)。
1905年,日本将朝鲜变为保护国,设立驻朝统监府,很快紧锣密鼓地任命相关人员调查“间岛”问题,并于1907年设立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直接介入“间岛”事务。斋藤季治郎以及篠田治策,是日本间岛政策的核心干将。篠田治策作为国际法专家更试图将间岛树立为“无人地带”(拉丁语之terra ius,意即no-man's land),进而瓦解中方的主权领土主张(159-170页)。在经过两年的调查和与中国政府代表的谈判以后,日本方面找不到可以否定中方主权领土主张的任何依据,“无人地带”之论亦未能得逞,最后不得不秉承1887年中朝图们江勘界的遗产,承认图们江属于中朝界江以及北岸之地系中国领土的事实,于1909年与中国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所谓中日《间岛协议》,承认了中国领土,却也同时攫取了在延吉地区的大量外交和经济权益,为其嗣后继续北进侵略东三省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时期,日本黑龙会和玄洋社等非官方势力(nonstate actors)也大范围渗透到了延吉地区,俄国也卷入其中,多边力量角逐变得错综复杂,移民群体的社会、民族和国家认同及其“边界”不断地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中发生变化(177-190页)。当此之时,中日韩三国很多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投到延吉和相关问题上来,从不同的角度和目的,报以对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关心,从日本的内藤湖南,到中国的吴禄贞和宋教仁,再到韩国的申采浩,都做出了自己的解读(201-218页)。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大量朝鲜人口在日本殖民政策下失去了土地,纷纷移民到延吉地区,人数迅速上升到了三十万之众。当此之时,“延边”作为一个指代这一地域的名词开始出现,“延”指延吉,“边”则指边地(221-226页)。朝鲜大量的宗教团体和人士,以及抗日救亡的“义兵”与独立派志士,都将延边作为活动根据地,延边成了那些已经丧失了祖国的朝鲜人(或曰“无国之人”,即stateless people)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空间所在(250-250页)。
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不少独立人士都与延边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年3月13日,不少拥护独立的朝鲜移民在延边的龙井集会,遭到镇压(251-255页)。在延边的独立志士也从此开始了在东北地区的抗日和复国的运动,日本方面则步步紧逼。在日本的殖民政策之下,“间岛”的地理边界不断扩大。1931年7月,穆克登碑不翼而飞,两个月后爆发了日本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此后日本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并在延边地区设立所谓“间岛省”,一直到二战结束。1952年中国政府建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三年以后改为自治州。1964年3月20日,北京与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议定书》,精确划分了天池一带的边界。
中朝两国之间,自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到光绪年间会堪图们江界,然后一直到1910年朝鲜为日本所强迫吞并,都脱离不了清初双方建立的宗藩关系的影响。《制造边界》一书在第一章与第二章内将这种状态做了完美的呈现,并且在其余章节内也适时探讨此种传统关系在当代政治中的遗产。《制造边界》亦将中朝勘界同1886年同时发生在东北地区的中俄勘界和西南地区的中越勘界做了横向对比。在中朝、中俄、中越三个划界案例中,北京及其地方官的外交策略是很灵活的,其王朝地理原则针对不同情形有不同的表现(79-84页)。《制造边界》一书展示了横向与纵向的对比考察,且不失微观上的辨析,足为学者探析近现代中国的其他边界案例提供一个研究典范。
光绪皇帝朱批铭安与吴大澂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2辑,243页
纵观《制造边界》一书,其中的“边界”(borders)不仅是指地理学意义上的对中朝两国而言的图们江边界,更重要的是从抽象的学理层面涵盖了一种多重的、互动的“边界”,这包括中朝传统宗藩话语的张力所至、王朝地理的运用界限、对欧洲国际法话语的诠释与挪用、跨边界移民的身份认同、日本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拓展、官方与非官方力量的互动、中朝日俄四国在交界地区的多边策略等等方面在内。概论之,前者的边界是地理的因素,后者的边界系人文的因素,此二者于时间与空间上的互动,使得现代东亚国家的主权领土日益清晰、国民归属日益单一、民族认同日益提升,以及多边国际秩序日益渗透和作用于边界地区。这一作为多重边界而存在的图们江北岸地区,充当了一扇历史的窗口,展现了一部近现代东亚地区风云变幻的世界史。正如作者所言,《制造边界》所讨论的对象,既是一种“多边性的当地”(multilateral local),也是一种“地域性的当地”(regional local),更是一种“全球性的当地”(global local),三者相辅相成,一以贯之(10-15页)。因之,该书切入主旨讨论的路数,完全不是单一的和线性的,而是多维的和立体的(267-269页)。到目前为止,中外学界中探讨近现代图们江勘界问题的论著,大多集中于康熙时期穆克登查边与树碑的经过、中朝日近代勘界谈判的经过以及中日“间岛”交涉的来龙去脉,也就是集中于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界纷争,而《制造边界》则完全突破了这种平面的框架,展现了从地理、政治、外交到国际法、移民、民族认同、国家构建等多重面相的立体交织。就此而言,《制造边界》将图们江划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认识论的层面,不仅仅对中朝边界地区的研究有重要的贡献,对近现代中国在西南、西北等地方的边界问题的研究,也有着相当扎实的参考意义。
三、中日纠葛之中的图们江:国际法下的吾国、吾土与吾民
图们江界务问题本是中朝两国之事,但因为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强势殖民的推进,自1905年日本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protectorate)并控制朝鲜的外交等事务以后,中朝图们江界务随之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外交事宜,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更完全演变为中日之争。日方所谓“间岛问题”的大范围地进入东亚舆论视野,也恰是在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从朝鲜半岛向北推进到东北地区的表现之一。《制造边界》一书在第四章之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从1905年到1909年之间日本方面是如何试图通过欧美国际法话语瓦解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张,并开始大肆扩展所谓“间岛”地域的。就此而言,图们江界务问题之所以变得复杂起来,主要是日本殖民主义浸染的结果。
众所周知,日本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兴起了大亚洲主义(pan-Asianism)的思想,1901年成立的黑龙会(名字沿袭“黑龙江”)也都公开鼓召此种泛亚主义,并且主张日本进军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地区。黑龙会头子内田良平亲自前往东北和西伯利亚考察,为其组织的扩张主义张本。1904年,毕业于德国的地质学家小藤文次郎,在其发表的论文中用“中立地带”指代所谓“间岛”地区。1906年日本参谋本部的守田利远所编的《满洲地志》内也声称这一地区是“化外区域”之一,而且他所指代的“间岛”是从图们江到以北的海兰河这块南北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长、东西二百五十至三百公里宽的大片土地,远远超过了朝鲜移民所谓之“间岛”地域(145-146页)。此时正值日本变朝鲜为其保护国以及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成立之时,日本军部、外务省和伊藤博文为首的朝鲜统监府等势力开始大举探察“间岛”情形,其中包括深入东北考察的记者内藤虎次郎(即内藤湖南)、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与国际法专家篠田治策,后两者是渲染“间岛问题”的干将,担任过日本设立的“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之所长与总务课长。
篠田治策(1872–1946)
篠田治策作为国际法专家,其最重要的路数是利用国际法中的“无人之地”的概念来将延吉地区或者“间岛”地区中立化,妄图以此否定中国领土主权,合理化和合法化朝鲜移民占土以及日本的殖民事业。“无人之地”这一概念,本是指国际法中的terra ius,它本质上并非是指无人居住或者少人居住的地带,而是指尚未有主权主张的土地,可以说是“无主之地”之意。篠田治策从1909年到1930年在阐述其对“间岛”的定位过程中,将这一词汇的日语汉字翻译从最初的“间旷地带”最终明确化为“无人地带”,以期证明日本完全有合法的依据占领这一地区。为了从历史中寻找支持,篠田治策引用了十八世纪的法国汉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一书中的相关描述,杜赫德作为耶稣会士,毕生未曾踏进中国一步,他对中国的了解全是依靠在清代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同仁们的书信和汇报,而有关中朝边境方面,他依靠的是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的回忆录。雷孝思是参与康熙后期大地测量的主要耶稣会士之一,曾经亲自抵达过辽东的凤凰城。凤凰城外是柳条边栅门,柳条边到鸭绿江边有大约一百多里的土地是禁止住人的,这是自清初建立柳条边以来就开始的封禁政策。雷孝思作为外国人,不能前往朝鲜属国,所以滞留在凤凰城,在他看来,出了城就是朝鲜的西界了,而且认为在柳条边和朝鲜边界之间有一块“无人居住的空间”。篠田治策首先认为雷孝思所言系真,然后证明这块“无人居住的空间”就是国际法所言的“无人地带”,则根据先占先得的原则,这块土地属于日本方面而非中国方面。这是篠田治策使用“无人地带”的逻辑。
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第四卷于1741年在伦敦出版;左面人物插图系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然而,《制造边界》敏锐指出篠田治策对雷孝思的记录是断章取义的(160-166页)。虽然1907年内藤湖南在其《间岛问题调查书》内也照样参考过雷孝思的记录,且内藤湖南认为这种中朝之间的“闲荒状态”的土地仍旧是在中国边境之内,然而篠田治策却刻意将此歪曲,以便同国际法上的“无人地带”衔接起来。如上所述,篠田治策的“无人地带”之论最终未能得逞。此种殖民主义在国际法的层面,同欧洲殖民主义直接发生了纵向的联系,成为日本近现代殖民建设中论证自身合法性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素。这一地区成为日本殖民主义策略的一个试验场,与其后来的“大东亚共荣”之策略的出台亦有着颇深的渊源(258页)。
中国学界对此问题一直都有关注和研究,但《制造边界》一书并无意重复梳理史实本身;相反,《制造边界》援引麦克·康纳尔(Michael Connor)、安德鲁·菲兹莫瑞思(Andrew Fitzmaurice)、劳伦·本腾(Lauren Benten)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指出terra ius实则是近代之发明,这个词汇最初是在1888年由德国学者费迪南德·冯·马提兹(Ferdinand von Martitz)以“territorium ius”的形式提出来的,马提兹将其定义为“任何不被组成国际法共同体的主权国或保护国有效管治的地域,不论其是否有人居住”,目的是为了确保德国对其非洲殖民地的统治(162页)。在实际的操作中,terra ius一词很少出现,但是背后的逻辑则从十六世纪以来作为自然法传统被欧洲殖民者普遍采用来合理化他们对原住民土地的攫取,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俨然已经成为殖民主义为自身背书的法理依据(162、164页)。《制造边界》一书中对中日图们江界务谈判的考察则不仅仅停留在“间岛问题”的个案之上,而是更进一层地从国际法层面对这一个案进行了世界史框架内的解读,它的意义也因之远远超过了图们江界务本身。
四、大国阴影里的图们江:想象中的吾国、吾土与吾民
在很大程度上,《制造边界》也是一部近现代中国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艰难形成曲折发展与历史,展示了朝鲜流民从被迫到异国他乡耕垦的移民到中华民族之一部分(即中国朝鲜族)的动态的历史。然而,也恰恰是延边的朝鲜人群体,映衬出了近现代历史上的大国外交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力量的沉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日本殖民朝鲜时期,朝鲜人群体作为失去祖国的族群,只能营造一个想象中的朝鲜民族的国家、国土和国民,而这一点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二战结束以后的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以及相关人群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
《制造边界》一书有两章是专门描绘“吾民”及其生存于其中的本地社会的,“人”的因素因之贯穿全书。在第三章之内,作者以微观的手法,细腻地呈现了一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延边移民群体的社会生活状态;在第六章之内,作者以不同的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再次梳理了朝鲜被日本吞并之后延边社区的朝鲜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纠葛与矛盾。第六章之内探讨的移民身份认同尤其深刻:究竟是作为“日本臣民”而非日本公民,还是加入中国国籍归化为中国公民,抑或与生活在中国领土之上的同胞维系一种共同的朝鲜民族认同?(226-251页)这成为朝鲜移民社会夹在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中必须面对的艰难选择,而每一个选择又都与移民社会赖以为生的土地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这些活动本身,又要面临当地不同官方机构的管理、马贼盗匪的骚扰、黑龙会等非官方组织的渗入、日本东拓会社等金融资本的渗透、中朝土地租赁关系的表里、朝鲜本土的天道教和大倧教等宗教团体与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等宗教团体的明争暗斗、朝鲜民族主义团体的动员及其政治立场的演变等等,于是又不得不回到第三章所谈到的众多日常生活层面的问题中去,而这也恰恰是1880年代朝鲜移民挑起的二江说的社会生态上的根源。延边朝鲜群体在从1880年代到1950年代长达七十年左右的过程中,其有关吾国、吾土与吾民的认同,在与中国、朝鲜、日本、俄国等方面因素的接触或对抗之中,不断地被定义(defined)和再定义(redefined)。这种动态的边界塑造和再塑造,一直到延边自治州建立之后才逐步尘埃落定,但它身上所承载的多边的、多重的历史,却并未因之而同步消失。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院成员合影,1919年10月11日,上海。该临时政府于4月13日在上海成立。照片上的人物,后排从左至右:金澈(1886–1934)、尹显振(1892–1921)、崔昌植(1892–1957)、李春塾(1889–1935);前排从左至右:申翼熙(1892–1956)、安昌浩(1878–1938)、玄楯(1880–1968)。
在讨论中朝上层外交交涉之时,《制造边界》从分析咸镜道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遭受的自然灾害以及当地人口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入手,揭示了朝民越江背后的社会生态因素和朝鲜本国的人口与政治因素,也恰恰是这一非常迫切的生存原因,让这些流民采取了看上去“不循政教,滋事两边”的策略,而他们的这种策略直接造成了两国外交上的纠纷。正如第三章和第六章所分析的那样,这种生存的危机一直笼罩着图们江越界移民群体社会,乃至于到了日本殖民时期,在东洋拓殖这样的日本金融殖民势力深入延边地区的时候,那些在朝鲜半岛曾经被东拓霸占了田产而流亡到延边的朝鲜人,也不得不在延边与东拓再次发生经济上的关系,不啻是一个时代悲剧。(229-230页)
五、余论:流动的历史
《制造边界》一书从历史、地理、制图、文化人类、社会、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交叉的角度,描绘了一部多个国家与多种力量相互交织的跨边界的历史,也描绘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图们江北岸移民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这两者的结合,使得跨边境移民社区、国土和国民都处在一种动态过程之中,既有上下内外的融合,也有上下内外的撕裂。传统的宗藩体系日渐无法调试这种动态,国际法上非常精确的非此即彼的国界法则也不能规范这种动态,而近现代殖民主义的强势渗入更不能固化此种动态。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人物围绕图们江划界问题的交叉,是一个当时代全球的大国外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民族独立革命相互交叉的缩影,既是个人的、当地的历史体验,又是群体的、地域性的和全球性的呈现。《制造边界》展现了这样一批近现代历史中的人物,揭示了其中每个人都在苦苦追寻国家、国土与国民的边界和认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态环境中,“吾国”“吾土”与“吾民”一直在被各种力量所塑造和重塑,而且并不是相互脱离的,而是互相纠缠甚至捆绑在一起的。这一流动中的历史,不仅仅在图们江流域如此,也不仅仅在东北亚地区的中朝日俄四国的交流史上如此。然而,究竟是否有明晰的“边界”(borders),以及如果有的话又如何能够追逐并实现此种“边界”,则又是《制造边界》一书留给我们的一大思考。《制造边界》是一部力透纸背的著作,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该书将在清代以降之中朝关系史、近现代东北亚边疆史以及近现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等领域内持续产生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