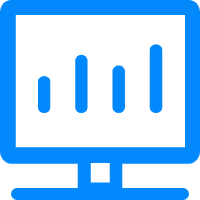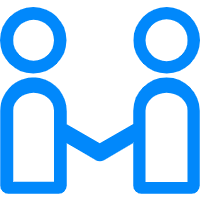生物学对脊椎动物外形的描述,有一个关键词,“左右对称”。
这个词很好理解,假若以脊椎为中轴线折叠,这一半应是另一半照镜子般的模样。左眼、右眼,左手、右手,就算是一只鼻子、一条尾巴,也能被均匀分成两半。飞鸟与鱼,人或猫狗,都是如此。
这是自然规律,而打破规律的,称之为意外。
20岁,卢敏还在读大学,意外怀孕。男友家急着给这对年轻人办了喜事。当她临盆时,意外再一次到来。
“婆婆瞧了一眼,转头就走。”卢敏回忆,“我妈说,看看你自己生了个啥子。”
刚刚诞生的小女孩,只有一只完整的耳朵。在原本应该是右耳的位置上,只存在着一点小小的肉瓣,没有耳孔和耳廓。
这是先天性小耳畸形的典型特征,俗称“小耳症”。中国每年大约有2500个这样的孩子出生,其中十分之一是双侧均有畸形,严重的会影响听力。
耳朵是不可再生的器官,弥补缺陷需要人工再造。一种通行的方式是,取出患者的部分肋软骨,做成外耳形状,再植入患处皮下。7-11岁被医学界认为是人类肋软骨再植的“黄金年龄”。
卢敏等了7年,2022年,女儿7岁了,进入“最佳手术年龄区间”。为了给新耳朵安家,小女孩又忍耐了7个月的皮肤扩张术。
“我一天都不想再等了。”卢敏说。
可意外再次找上了这对母女。
必须尽快手术的117人,绝大多数是孩子
关键时刻,董跃平不愿掉转车头。
他从山西临汾出发,连续驾驶5个多小时,马上就要抵达陕西西安。但打来电话的人坚持说,返回吧,来了也没有意义。
“您先停下车,我用视频通话跟您解释!”
“我在高速(公路)上!怎么停车?!”董跃平对着手机吼道。
他结束通话,看了一眼儿子,17岁的男孩也看着父亲。在男孩头颅右侧,鼓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球状包块。那是手术埋入皮下的水袋,每天一两毫升的注水进行了数月,水袋逐渐膨胀,皮肤受到张力,随之生长,新生的皮肤将用来覆盖肋软骨制成的耳朵框架。
按照原计划,两天后,“水球”将消失,一只右耳将在那里诞生。但此刻,董跃平不知如何开口对儿子说,耳朵做不了了。
那是2022年1月13日,西安卫健委发布通告,对“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的西安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作出“停业整顿3个月”的处罚。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就是董跃平和儿子的目的地。在这家医院的整形外科,他们已经完成了外耳再造的第一期手术,即埋入皮肤扩张器。就在如约赶赴第二期手术的路上,他们被医院通知返回。
此时,四川的卢敏早就买好车票,女儿脑袋边上的“水球”已经挂了7个月。得知医院“停诊”后,卢敏不得不把水杯、毛巾等生活用品一件件从行李箱掏出来,为这个“意外”继续等待。
那两天,像这样的电话,朱冰打了很多。
“约了门诊的有100多人,约了第一期(手术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有400多人,约了第二期(手术)的有117人。”朱冰回忆,“得一一通知。”作为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医院的院长助理,她和同事一刻不停地打电话,他们优先通知约定近期来院的患者,尤其是已经“带球”数月、必须尽快进行二期手术的117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不满10岁的孩子。
“我太理解他们的心情了。”朱冰回忆,有患者家属骂医院,骂她和医生,她忍着,让他们宣泄,“假也请了,票也定了,甚至有人都到西安了,宁愿隔离14天,加上疫情给人的压力,所以情绪不好。”
根据朱冰了解到的情况,一批患者第二天就要办理入院手续了;还有患者为了等手术,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有人到西安后,受疫情影响,只能住在亲戚家,实在不好意思再打扰下去;有人在路上,和她通话时周围有火车车厢的服务广播声。大部分患者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手术需要花费七八万元,这一折腾,又增加了他们就医的成本。
“是不是别人靠关系插队了?”董跃平怀疑过,最终他还是带儿子回了临汾,最近的时候,他距离西安只有20公里。
实际上,除已入院患者,执行“停诊”措施后,西安国际医学中心的多个科室,没有新接诊一人、新登记一台手术。
我没想过发微博的后果,我只想过不做手术的后果
1月12日夜里11点,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外科医院院长、那些“耳朵”的制作者郭树忠急了。
“孩子们‘带球’带了几个月,不能再拖了。”他担心,“皮肤扩张器的注水管暴露在外,体表有开放性创口,再拖下去,患者感染的风险会显著上升。”此外,很多正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趁寒假来做手术,如果继续“带球”,开学时他们很可能无法重返校园。
郭树忠自称,有人修车,他是“修人”。他年近60岁,曾任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全军整形外科研究所所长。他主刀过世界第二例、中国首例换脸术,完成过中国首例前臂耳再造手术,无论国际国内,“修耳朵”这个领域,他是顶级专家。他用肋软骨雕刻、组装的耳朵,成品逼真。
“地球上能把这个活儿干好的,不超过10个人。”他自信地表示,“我们是拿刀的艺术家。”
许多小耳症患者的父母从全国各地而来。郭树忠说,有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前,通过超声检查看到了耳部缺陷,就联系他预约面诊和手术的时间。也有老人把小耳朵视作一生的缺憾,想把手术做了,“完完整整”地离开人世。
在郭树忠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块占据半面墙壁的大白板,白板上密密麻麻标注着每一只皮肤扩张器进入患者头皮下的日期,还有已预约的二期手术数量。从前,这个数字始终一边减少,一边增加。
“我不能停下,不能倒下,未来估计还有1万多台手术在等着我。”郭树忠说。
最要紧的,是眼前的117名患者。他们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时间足够长了,因为其间郭树忠身体抱恙,手术已经被推迟了几个月,眼看又要再次推迟。
“我今天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我感觉非常对不住这些患者”,1月13日晚,郭树忠用个人账号公开发表一条微博,讲述不能手术的焦虑心情。在他附上的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患者照片中,孩子们的头部一侧,突兀地鼓着大包块,显著发红,管道穿过皮肤,盘绕在一旁。郭树忠发出警示:“无论如何都该做二期手术了,否则风险会增加。”
师俊莉是郭树忠的学生,也是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外科主任,给患者埋入皮肤扩张器的一期手术,主要由她完成。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埋了35个。
她会在患者的新耳朵选址处上方开一个口,用手术剪刀剖开皮下组织,形成中空的囊袋,再将折叠成小块的扩张器塞入、展开,将管道留在体外,最后缝合伤口。这项操作中,剪刀要穿过皮下组织的不同层面,对医生手感的要求很高。
这位女外科医生用修长的两根指头模拟剪刀,冷静而精确地形容着刀刃在皮下剪开组织的触感,“阻力变大了,这是有(毛)发区和无(毛)发区的交界处,刀尖要微微转向了”。
回忆“停诊”时,这个调侃自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女人”显得有些激动。
“我把‘球球’埋进去时,就开始牵挂他们。”师俊莉说。她遇到过,有农村孩子缺少监护,夏天会跳到村子的池塘里游泳,造成伤口感染。有人运动或与人玩闹时被扯到管道或碰伤表皮,绝大多数人几个月间只能朝着一个方向睡觉。
董跃平的儿子,已经很久没有上过体育课了。卢敏的女儿刚到学龄,接受一期手术后,“球”越鼓越大,紧绷的皮肤闪闪发亮,有一种轻触就会破损的脆弱感。这个年纪的孩子活泼好动,老师担心她遭遇磕碰,建议她不要到校。7个月来,每晚入睡后,卢敏都会爬起来三四次,“看我女儿的‘球球’还好不好”。另一些细心的母亲,会缝制中空的环状枕头,以便孩子翻身时,“‘大包’可以好好地放进去”。
“多等一天,我和他们就多揪心一天。”师俊莉说,她没想到,“教授会发那条微博,还在网络上引起轰动了。”
“当时我一点都没想过发微博有啥后果。”郭树忠摆了摆手说,“我只想过不给他们做手术的后果。”
“心上的病比身上的病更重”
卢敏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女儿出生的那一天,没有受到家人的欢迎。她年轻的丈夫听说了那个意外,拒绝探望这对母女。公婆沉默着离开了医院。母亲照顾她们,却直白地推测着“原因”。
“新房甲醛”“没吃叶酸”“孕期感冒”……都被考虑到了,但实际上,即使是针对这种先天疾病最前沿的医学研究,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环境污染、基因缺陷都是备选因素。郭树忠和师俊莉接触过一个家庭,总共少了16只耳朵,“应该是遗传造成的”。也有些工业发达的地方,土壤和地下水长期受到污染,“小耳”病例多。但总的来说,这个意外降临时,不挑地域,不挑贫富,唯独在性别上,男性比例高。
较低的概率也让卢敏赶上了。女儿刚满月,她就四处求医,郭树忠团队给出了让她满意的方案,除了“7年后再来”。
小女孩长大的过程中,祖母从不愿带她出门玩耍。外祖母提醒她少看电子屏幕,保护眼睛,“没耳朵连眼镜都戴不了”。有小伙伴好奇,伸手揪她仅存的那一点“小耳朵”,她学会了反击。
董跃平是从产检医生那里,第一次听说孩子的缺陷。医生问,“少个耳朵,打掉(人工流产)吗”,他毫不犹豫,“五六个月,是个人了,就因为一只耳朵,怎么可能不要”。
儿子出生那天,他亲眼看见了那个缺陷,“初为人父太高兴了,却又有说不出来的难受”。
这位父亲去过很多地方求医,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方案。男孩小时候并不在意耳朵,但当他进入青春期后,性格变得愈发敏感、内向。他每天都戴着帽子去上学,不喜欢外出。比起和同龄人玩,他更愿意一个人画画。
想起那种“不舒服”的感觉,24岁的李达至今还会激动。
他出生在内蒙古一座小镇,小时候的外号叫“托尔多”。他介绍,在当地方言里,这是“没耳朵”的意思。
“托尔多,一起玩!”他想起儿童时代小伙伴的呼唤,想起另一个少了一只耳朵的小学同学,和他一起被老师叫去拍照“留念”,几乎没有反感。然而,李达上初中时,心理随身体开始剧变。
同桌和他吵架,骂他“没耳朵就是不行,递不进去人话”,他气到现在。走在县城的商场,他会被“好奇的小镇居民”围住,打听他怎么丢了耳朵。他越来越焦虑,频繁地洗脸、照镜子,问自己“为什么比别人少了一样”。他越来越在意外表,学习成绩也受到了影响。他还一直留着能盖住耳朵的发型。
“天下的父母好像都有这种默契,给孩子留的发型差不多。”朱冰回想多年以来见过的数以千计的小耳症患者,“大多都有能盖住缺陷的发型”。一些男孩从未剪过短发,手术前要剃发,有的人新奇、兴奋,有的人难舍、大哭。
根据朱冰的观察,小耳症患者的智力、体能一般没问题。年龄越小,他们所受的心理困扰也越少,“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孩子”。听力受损不严重的,和人沟通非常顺畅。其中还有一些,因为缺陷得到了家人格外的怜爱,同理心很强。董跃平就不忍心凶儿子,他的父母、岳父母都把这个孩子视若珍宝。他后来又得了个“一点问题没有”的闺女,妹妹懂事,从小就知道不提哥哥的耳朵,不和哥哥争抢。
比起带给幼小心灵的影响,那些令人意外的耳朵,对患者的父母伤害更深。
卢敏常被人问起,你怀孕时干什么了,把孩子生成这样。在怀上第二个孩子后,卢敏对影像学检查很执着,做B超的次数远高于产检需要。她反反复复地问医生,耳朵有吗,嘴唇呢,手指呢。
董跃平一到家庭聚会,就得硬着头皮去听亲朋好友的“好心建议”。他做报废车生意,收入无论多少,都大方投入两个孩子的教育。他不是有钱人,因为一度没筹到给儿子做耳朵的费用,他感到无比愧疚。
常有母亲向医生提出,“取我的肋骨给孩子做耳朵”,但异体组织移植容易引发排异,朱冰不得不解释、回绝。她记得一个10岁的小患者,全家人都认为“女孩就没必要花这钱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坚定地“非做不可”。外耳再造术不在医保的报销范围内,朱冰也理解那些因经济困难放弃手术的家庭。
李达回忆,祖父母瞧不起他的母亲,认为孩子有缺陷就是当妈的错。班里开家长会,一群母亲拉着他母亲,关切地询问“你怎么把孩子耳朵烫没的”,责备她“太不小心”,然后提醒她“孩子以后不好找对象”。一家人曾去北京看耳朵,被骗去大额药费。“说吃了他的中药,耳朵就能长出来,说我吃完发烧是因为耳朵在膨胀。”
李达的父亲做泥瓦匠,母亲打点小工,他们一直在为儿子的耳朵攒钱。
“有时我写作业,她盯着我,然后就哭了。”李达回忆,他还问母亲,“我写错啥了?”
再次筹够儿子的“耳朵钱”时,这位母亲查出了胃间质瘤。她悄悄藏起CT片,不想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直到已经上高中的李达发现了母亲的病情,逼她接受治疗。
这位母亲后来陷入抑郁,长期服用药物,她总是对儿子哭诉:“对不起,对不起,我答应给你做耳朵的。”在李达看来,自己的耳朵是母亲的心病,比她身上的病沉重多了。
“终于把教授关回手术室了”
因为心疼母亲,李达试着接受那只耳朵的遗憾,“不做又能怎么样”。
读大学时,他用尽全力读书、社交。他身材高大,相貌端正,成绩也好,是校园里的人气之星。在一次活动中,他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同学。收获爱情让李达更加自信,“其实我并没有比别人少什么”。
如果不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李达已经不打算种耳朵了。他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奶厂担任车间管理人员。他和女友关系稳定,除了偶尔“和她父母视频通话会藏起半边”、考驾照被考官质疑“听力”以外,他对生活没什么不满意。他留极短的寸头,登上公司年会舞台,还在抖音平台发布直接暴露缺陷的视频。“我们的感情也很平等,她是个善良的女孩,但对我不是同情,是爱情,这一点我非常确定。”
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奶厂要求全体员工,戴口罩进入办公区。
“没有耳朵怎么戴口罩?”李达回忆,他把特仑苏牛奶箱的塑料提手拆下来,固定口罩两侧的皮筋。“我平时都是精精神神的,这样一戴人都塌了!”一位奶车司机劝他,“做个耳朵吧,方便些,以后也不会有人问小孩,你爸爸怎么没有耳朵”。
“为了我母亲的心病,也为了我未来的家人。”李达很快就向单位请了假,到北京多家医院问诊,租住在地下室里。“网上无意间看到郭教授,我坐了趟绿皮火车,连夜赶到西安。”
那是2020年年底的事,朱冰印象很深,“小伙子的故事很曲折,但两期手术都很顺利”。李达则模模糊糊地记得,术后,麻醉剂的作用还未消散,他便问母亲,有镜子吗,有耳朵吗,母亲依然在哭,“可能是所有的心病终于发泄出来了”。
2022年初,由于医院停诊,卢敏还得继续与“心病”共存。她想好了,女儿的缺陷治不好,干脆不要嫁人,一辈子跟着她;自己被人瞧不起,干脆也不要受婆家的气,也一辈子跟着母亲——三代女人一起过。
1月14日,郭树忠发微博的第二天,医院接到市卫健委的通知,117个已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患者可以做二期手术,暂时不允许“新增”。
“感谢上级领导能够体谅到孩子们的疾苦。”郭树忠又发了一条微博,在他看来,医院应该吸取教训,坚持“生命至上”。
朱冰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再一次拨通那组号码。这回,她听到的是“现在买票”“马上出发”“听您安排”和各式各样的感谢之辞。她记得,有患者家属赶到医院后,冲上来拥抱她。准备二期手术的孩子们剃去了头发,“大球带小球”的脑袋在病区里到处晃悠。
董跃平儿子和卢敏女儿都在那份名单内,两人的手术被排在同一天,2月9日。虽然还要再等上大半个月,但对他们来说,即将到来的春节,真的有“辞旧迎新”的意味了。
郭树忠再一次拿起了手术刀——11号刀片、德国制造、雕刻软骨专用。一只、两只、三只……117只耳朵,开始一只一只诞生。每一次进行术前家属谈话时,他都郑重地道歉:“对不住,因为我的身体原因,耽误了这么久。”
回归手术室的第一天,郭树忠做了3只耳朵,他们都属于孩子,两个7岁,一个12岁。看到郭树忠,麻醉科医生也很激动,笑着说“终于把教授关回手术室了”。朱冰描述,在病房里,孩子们会互相交流“耳朵”,“带球”的摸摸已经“对称”的,“对称”的鼓励“带球”的——“你的肯定比我的好”。
“给孩子们做手术是一件幸福的事。”那一天,郭树忠“在手术换台的间隙”发微博,“做了一辈子外科医生,我总是觉得,病人的幸福,就是医生的幸福。”
“我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以假乱真”
2月9日一早,卢敏忍住眼泪,笑着和女儿道别。
“别害怕,妈妈就在外面。”她说。
“我是来种耳朵的!”躺在手术转运床上小女孩咧嘴一笑,露出还没长全的门牙说,“我才不怕呢!等我出来的时候,就有耳朵了。”
手术开始进行。只用了一分半钟,负压泵就将小女孩皮下鼓胀的水袋抽空了,新长出的皮肤瘪瘪地褶皱起来。
郭树忠用一把钢尺,仔细度量了小女孩完好的左耳,比照着,在右侧皮肤表面“以对称为标准”画下线路。另一位医生接过手术刀,沿郭树忠画好的线做了一个直角切口,护士迅速清理了刀口的血液,透明的皮肤扩张器暴露出来,旋即被一手术剪夹出。
在无影灯下,被3把剪刀包围的切口,出血量很小,视野清晰,这是注射的肾上腺素的作用。与此同时,师俊莉带领的另一手术团队在小女孩的左胸下方,切开一道小小的口子,准备取肋软骨。
“就像剥洋葱一样剥开骨膜。”郭树忠曾比喻,“啃过排骨吧,那些半透明的脆骨就是肋软骨。”
师俊莉解释,做耳朵,用到的软骨主要在第6号、第7号和第8号肋骨上。如果量不够,可能还要取第9号的。它们的长度、硬度、弹性、厚度都相对合适。做左耳要用右侧的肋软骨,反之同理,这是为了利用软骨天然的弧度。
7号条件最好,会被用来做耳朵的主支架,6号做底座,8号、9号做耳轮和对耳轮。人的外耳天生沟壑纵横,重建时如果追求仿真,要将所有细节构建出来。师俊莉说,太小的孩子,肋软骨量不够,长大了又会钙化、变硬,60岁以上“就成了豆沙雪糕,酥掉了”。
有人耳朵大,用料多,有人耳朵贴头皮,用料少。但每个人的耳朵都拥有独特的形态,“医学需求的外耳再造,追求的不是美,而是‘像’。”师俊莉说,参照物就是对侧那只耳朵。
郭树忠自称“赝品制造大师”,他把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请来给团队授课,让学生练习雕萝卜、芥菜、羊和猪的排骨,自己也去美院刻木头、捏陶土。
此刻,他接过小女孩的第一段肋软骨,放置在一块巴掌见方的白色操作台上。
孩子的软骨是粉白色的,看上去非常纯净,郭树忠用手术剪刀轻轻修去上面残留的组织,拿起一份1:1制作的小女孩左耳的透明模版,比对着那段软骨,画下轮廓。
11号刀片登场了,它削过骨面,白色碎屑随之掉落,软骨开始显露出优美的弧线,那是在模拟耳轮的外缘。
手术室里,心电监护仪发出均匀而响亮的滴声,背景音则是交替播放的情歌、古典乐和春节序曲。郭树忠一边雕刻着骨头,一边讲起整形外科的历史——一战时,不少士兵遭受近距离枪伤,面部损毁严重,“孤悬于身体之外的耳朵格外容易被打掉”。
“有的军医治腿、有的治肚子,还有一个大夫,专做修修补补的工作。”郭树忠提到的人,名叫哈罗德·吉利斯,是一位新西兰耳鼻喉科医生。1916年,他在英国一家诊所工作,说服主管,为从战场归来的“鬼脸”战士修复面部。他解剖过不少战地遗骸,发现肋软骨适合用来再造器官。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份礼物。”郭树忠说,使用自身的肋软骨再造器官,能有效避免排异反应;少了几段肋软骨,对人影响也不大。
吉利斯被称为“整形外科之父”,但其后几十年,全世界医生做出的外耳,都还只是一个“肉板板”。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一位医生才第一次用肋软骨做出“类似耳朵的形状”。之后,另一位热爱艺术、喜欢雕石头的美国医生,在肋软骨上雕出了耳朵的细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位医生主导着全世界耳再造领域,“所有的教科书,权威信息都来自他,所有的学术会议,都是他主持”。
“1995年我在美国参加他的培训班,他不太搭理我,但我听得非常仔细。”郭树忠笑着回忆,仿佛回到了虚心求学的时代,随即他恢复了“大佬”的气势,严肃地表示,“到今天,他的方法已经被淘汰,我们做耳朵的效果早就远远超过他了。”他会去义诊,也找来基金会,给经济实在困难的患者免费做手术。
郭树忠将雕好的软骨部件组合起来,用钛丝缝合、固定,在他手中,出现了一只边缘圆润的、很像耳朵的东西。
“耳朵是三维立体结构。”他解释,“雕和塑是两件事,要边雕刻边塑形。”更多的肋软骨被取出、送到他手边,11号刀片继续游走,微小的白色碎屑散落在深绿和浅蓝的操作台盖布上。郭树忠珍惜这些材料,尽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1小时后,卢敏女儿的右耳已经具备雏形。郭树忠捏着模版比了比,开始修整耳朵的细节,增加“亚结构”——调整对耳轮的“三角窝”、增加耳屏、留出耳甲腔。他将已成型的结构放入小女孩脑袋右侧的切口,与左耳再三比对,又进行了几次调整。
当负压泵最终抽走皮肤下的空气时,几乎在一瞬间,表皮贴紧软骨,软骨卡住颅骨,一只粉红色的右耳出现了。恢复了血供,这些软骨将继续存活。
“我们这一行,追求的最高境界叫以假乱真。”郭树忠说,数年前,他尝试使用人工材料,工业化地做耳朵,效果一直不理想,“最后还是回到手上来。”
拿手术刀的心理医生
5天后的下午,卢敏追着女儿,穿过病房长长的走廊。
“慢一点!”她叮嘱,她不敢再面对任何意外了。
除了光头上顶着一根引流管,小女孩看上去很正常,右耳开始消肿,和左耳一样圆乎乎的。她眼睛大,特别爱笑,随身带着一只“小马宝莉”玩具。做完手术的当晚,她还疼得“哎、哎”直叫,但现在,她一会儿跑,一会儿跳,一会儿蹲,一会儿捶家属休息区的人型发泄靶,看得卢敏心慌。她已经把女儿新耳朵的照片、视频发给家人看,“好长时间憋着一口气,喘出来了”。她还总是忍不住问女儿,“你的耳朵漂亮吗”,然后等着那声“漂——亮——”。
再有一晚,这对母女就能出院回家了。
此时,西安已经连续20多天无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行程码早就“摘星”,城市运转正常。
走在医院里,郭树忠会遇到其他科室“拿刀”的同行。“真羡慕你,老郭!”有外科专家对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做手术,忽然不让做了,都不知道生命用来干啥!”
郭树忠知道那种感受。作为外科医生,他切过发炎的阑尾,也摘过恶性肿瘤。他给双腿受伤、心跳骤停的工人师傅做手术;给被驴咬掉下巴、父母背着家当寻医的孩子做手术;给渴望换一种性别生存的人群做手术。曾有一个年轻人,遭遇车祸,骨盆都压碎了,郭树忠忘不了他看着医生的眼神,“人都成那样了,眼睛里的求生欲还是那么旺盛”。
“还是把人修好更有成就感。”他说。
比起60后的老师,80后的师俊莉野心更大。她始终认为“没有一台手术是完美的”,流程、操作、医疗器械都可以优化、再优化。以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手术为例,她希望能做出一个“标准化流程”,精确到“这一刀切多少厘米”“这口子缝多少针”。
她的理由是,“不要让这种手术成为我的‘独门秘籍’,而是要让更多医生能学能做”——这样才能造福更多的患者。
董跃平的儿子出院时,拒绝戴上帽子。回到家,这个从前只在意“鞋子”的少年网购了一大堆“上衣”,穿上新衣,出门见同学。
“内心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我一度觉得外表缺陷没那么重要了。”李达回忆,“但当我真正拥有正常的外表以后,内心还是不一样了。”
他出院、上班后,遇见每一个同事,都会指着新耳朵给对方看。他第一次把社交媒体账号头像换成了自己的照片,他不再“特别恐惧失去爱人”。不久前,他被升职为“总经理秘书”,跟随领导出入各种公开场合。“以前有活动我也挺积极的,但被选中的时候少。回过头来看,我理解领导的想法。”
他不敢剧烈运动,“大酒”也不敢喝了,小心地保护着耳朵。
“我的手术刀能触及患者的内心,让他们更自信,更快乐,我是个拿刀的心理医生。”在“拿刀的艺术家”之后,郭树忠又给自己想出了一个头衔。
李达总会想起带着两只耳朵出院的那一天。他走出医院大门,走到街道上,和路人不断擦肩而过,但没有任何人看他一眼——那就是他最想要的平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卢敏、董跃平、李达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