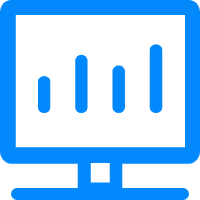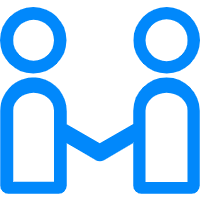李欣:清代中国海疆经略对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启示
作者:李欣关键词排名服务找大将军2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微信平台编辑:周悦【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清朝将“天下”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具体实践之中,对包括内洋、外洋、大洋和海上周边关系在内的多重要素进行总体考量,建立起较为成型、完备的海疆安全治理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三部进行海域管理。对内洋和外洋,通过行政建制和水师巡查,实现日常的、具体的海上管辖关键词排名服务找大将军21;对于大洋,则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以不治治之”原则应用到海上。二是以制度建设保障各地水师开展海上巡视、缉盗、护送、救助等任务,有效维护了东亚海上的安全秩序。三是以宗藩制度经营与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了东亚海上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晚清政府以主权原则强化对海岛、海域的管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立约保藩”的外部层面却遭遇失败。探讨清代海疆安全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具有历史中国观、总体安全观和国家主体观三方面的重要启示。【关键词】 中国清代;天下安全;海疆经略;中国周边;海上安全秩序一 引言所谓“经营天下,略有四海”。中国古代王朝具有长期经营、管理海疆的历史,尤以明、清两代的治海体系最为完备、治海能力最为突出。其中,明代底定中国古代海疆经略的基本框架,开创了对外海上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高峰。清代承袭明制,并进一步发展完善,但至晚清遭遇内外困境,开启古代王朝国家海疆“经略”向近现代主权国家海疆“治理”的嬗变进程。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史学研究本身特点所限,学界有关清代海疆经略、海疆治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较为具体、细化的选题上,一般是关于某段时期、 某个沿海地区或海区、 某一治策领域以及以上两大或三大限定关键词集成的专业化研究成果。除此以外,也有在通史著作中体现的有关清代的朝代时段、地区海区和专题领域的海疆治理、治策研究成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吕一燃主编的《中国海疆史研究》、 张炜、方堃主编的《中国海疆通史》、 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 等。可以说,学术界有关清代海疆治理的史学研究成果是较为丰富的,但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关于有清一代海疆经略、海疆治理的长时段、整体性、发展性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在面向理论升华和指导实践的知古鉴今研究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着力推进和深化。二 “天下”与清代中国安全观“天下”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范围、最高等级、最为理想的政治世界。一般认为,“天下”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诗经》。前者提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后者则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它们均是通过建立天命、国土、人民等要素与“天下”之间的联系,间接阐述“天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历史上,“天下”曾有两种存在方式,一是夏商周之“三代”的方式。如在周代,“天下”是一个众“国”林立的“世界”,周王室是“天下之宗室”, “天下”之中央即为“中国”。按照当前的考古认识,此时的“中国”即为“何尊”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之“中国”,其所在之地局限于今河南西部的洛阳盆地。 随后,“中国”的概念逐步扩大,约在春秋时期已可指代整个中原地区,使“周天下”中有着宗亲关系和礼乐文化的众多诸侯国都包含在“中国”之内了,地理上涵盖了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及河北地区。“天下”的另一种方式是大一统中国的方式。秦灭六国而统一中国,以废封建、置郡县而“初并天下”,使“天下”在保留“世界”观念的同时,转化为赵汀阳所说的“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 汉代大儒董仲舒发展巩固了作为“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谊”的大一统思想,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国作为“天下国”的历史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以后,“大一统”与“天下无外”走向历史合流,“天下”观念不仅没有因“周天下”的消亡而在历史中销声匿迹,反而随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大势而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历唐、元、清三代,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国”不仅在地理疆域上大大扩展,而且在国家形态和治理之道上也充分发展了。这一历史趋势发展到清代达到了顶峰。早在清人入关以前,努尔哈赤就在给明万历皇帝的信中提出:“天地之间,上自人类下至昆虫,天生天养之也,是你南朝之养之乎?……普养万物之天至公无私,不以南朝为大国容情……自古以来,岂有一姓之中尝为帝王,一君之身寿延千万……天命归之,遂有天下。” 这段论述说明此时仍居于东北边疆之地的后金统治者已将儒家大一统思想内化于心,并开始为日后入主中原、建立“清国天下”筹建意识形态基础。改国号为“清”后,皇太极冲破“华夷之辨”的文化藩篱,提出“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 又举大辽、大金“为天子”例,说明夷人有德者也可有天命、得天下,以此论证清政权取代明王朝的合法性。可以说,“大清”从一开始就被有意识地建构为一个包纳满、蒙、汉地,融合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天下国”。具体来看,在疆域格局上,“清天下”不仅包括内地十八省和蒙古、新疆、西藏、台湾等边疆藩部及海疆地区,而且还与朝鲜、琉球、越南、苏禄等国家或部落建立了宗藩联系;在表现形态上,以上十八行省、边、海疆地区和藩属国,形成了内地与边疆为“中”、联系属国为“外”的“中外一家”“天下无外”的总体形式;在治理之道上,则以包纳行省制、军政制、八旗制、伯克制等“因俗而治”制度为一体,以灵活运用户籍、派官、驻军、税收为基本治策,实施“内—疆—外”式的治理模式。 正如雍正皇帝所言:“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 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天下”实现了其“中外一统之盛”的广域盛景,为我们今天所称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国家形态不仅界定着国家治理观念,也界定着国家安全观念。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包纳着内地、边海疆地区和属国的清代中国是一个可称为“清天下”的复杂系统,其安全治理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秩序”。具体来看,清代中国安全观具有三重属性。首先,“清天下”的安全具有总体性,是包含内地安全、边海疆安全和属国安全的“中外一体”的国家总体安全观。其次,“清天下”的安全具有层次性。清王朝对边疆藩部和周边属国均施用厚往薄来的封贡制度,不过是有层次、有区别的。对边疆藩部来说,清廷既有国家权力的渗透,又给予地方自治的权力,但总体来说是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推进;而对周边属国来说,清王朝对属国的需求是“奉我正朔”“誓不犯边”,只要属国安于宗藩关系,在清国缔造的“天下体系”之最外层“永作屏藩,恪守职贡”, 清王朝就不改“以不治治之”的基本原则,不会干涉属国内政,更不会以强力将其纳入版图。最后,“清天下”的安全具有内部性。与“清天下”自成一体的“世界”属性相联系,清代后期以前中国的安全关切基本均处于“天下体系”之内,清王朝只要处理好满、汉、蒙等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以及中外关系,就能基本维持“清天下”的安宁与稳定。而当这一内部性伴随“天下秩序”从最外层被渐次打破而变得日趋脆弱,“清天下”的国体形态与国家安全就因西方列强的长驱直入而面临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三 清代中国海疆经略的基本逻辑及其国家安全含义海疆治理是国家边疆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明代之前,中国虽然通过广袤的海洋与周边乃至世界诸多国家展开长期的贸易、文化交流,但由于没有显著的外向需求和海上敌患,国家对海疆的经略,特别是对海防安全的经营和管理并不关注,更没有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海疆防务体系。直至明代,为打击海上反明势力,解决海盗、倭寇等袭扰事端,海防建设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以沿海卫所制度和巡洋会哨制度为重点的海疆防务体系才逐步建立起来。1644年,清朝定鼎中原。由于明朝余部在相当长时间内依托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抗清斗争,特别是明朝将领郑成功在从荷兰侵略者手中夺回台湾之后,又据之为抗清基地,因此清朝对全国海疆地区的统一是在1683年,即康熙二十二年收复澎湖、台湾之后才完成的。 清朝在大体沿袭明代沿海防御和巡洋会哨制度的基础上,对海疆经略的重视较前代又有所提升,不仅进一步将以上两大海疆治策系统化、制度化,更重要的是将“清天下”的总体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的具体实践之中,建立起更加成型、完备的清代海疆经略体系。(一)清代海疆经略蕴含“天下观”下的总体安全思想“海疆”一词在清代是一个较为广义的概念,包括沿海地区及海岛、沿海水域和在当时认识水平下无边无际的远海“大洋”。而海疆之“经略”是一个比“海疆”更为广义的概念,即不仅包括对沿海地区及海岛、沿海水域的经营和管理,对海上安全秩序的维护,还包括在中华“天下体系”内对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周边海上藩属国关系的经营和调适。在对沿海地区及海岛、沿海水域的经略上,清朝按照以陆定海的基本原则,将沿海水域划归各省管辖,建立了由北向南的盛京、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七大海区。有关这七大地区和相应海区的军事安全管理,又分为陆防和海防两个方面。其中,陆防兵力部署于海岸和岛岸上,依托炮台、瞭望台等往来监视、巡逻;海防兵力则通过驾驶大小船只在相应海区开展巡洋、会哨。此即“设立炮台以为经,设立师船以为纬” 的清代海疆防务方式。陆防方面,清朝派驻八旗和绿营兵陆营、水师数十万人守卫在各沿海海口,以及台湾、澎湖、海南、崇明、定海等岛屿上。例如在“龙兴之地”盛京,清朝主要通过设立奉天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对北部海疆沿海地区实行军事管辖。三大将军统领的驻防八旗隆营,分别驻在牛庄(今辽宁营口)、盖州(今辽宁盖州)、盛京(今辽宁沈阳)、锦州、宁远(今辽宁兴城)、兴京(今辽宁新宾境)、辽阳、金州、旅顺、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境)、齐齐哈尔、珲春、瑷珲等61处。 此外,则通过设置府、州、厅、县等民政机构,来管理一些未入八旗的汉地、汉民。 又如在东南沿海防线上,八旗兵分别驻扎在杭州、福州和广州三座中心城市。其中杭州将军兼辖乍浦驻军,福州将军同时节制陆路绿营各镇协,广州将军同时节制绿营陆路各镇协。海防方面,清朝对各省区所辖海区的管辖范围、四至界限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根据王宏斌的研究,盛京管辖的海域包括辽东半岛三面,北以鸭绿江口与朝鲜比邻,西以天桥厂海面与直隶为界; 直隶管辖的海面,分别以天桥厂、大口河与盛京、山东为界;山东所辖海面西自大河口,东达成山外洋,南以莺游山与江南为界,北以隍城岛与铁山之间的中线与盛京为界;江南管辖崇明至尽山一带海域,北以莺游山,南以大衢山与山东、浙江为界;浙江所辖海面分别以大衢山、沙角山与江南、福建为界;福建管辖的海域包括福建沿海、台湾、澎湖岛屿周围海域,南以巴士海峡与菲律宾为邻,北以沙角山为标志与浙江分界,西南以南澳岛中线与广东为界;广东管辖的海域则包括本省大陆海岸和环琼州岛岸的所有海面。在此基础上,根据海域范围、巡洋任务等的不同,清朝在沿海地区先后设立了不同规模的水师。如东北地区设有奉天八旗水师营(驻旅顺)、吉林水师营(驻今吉林省吉林市)、黑龙江水师营(驻今黑龙江瑷珲)、齐齐哈尔水师营、墨尔根水师营(驻今黑龙江嫩江)、呼兰水师营; 直隶设天津八旗水师营; 山东先后设有登州、胶州水师营; 浙江有乍浦水师营、昌石水师营、镇海水师营等; 广东有广东水师提督所辖前、后、左、右、中五个水师营,等等。清王朝通过以上举措,以陆海统筹、军政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对广大海疆地区的政制和军事管辖。除此之外,清代海疆经略还包括对海上安全秩序的维护和对周边海上藩属国关系的调适, 反映出清朝在海疆经略上对内地、海上和海外属国关系的总体安全的考量。(二)清朝在海域管理上实施分区治理、有所治有所不治的原则中国古人把近海海域划分为内洋和外洋的萌芽至晚出现于宋代, 及至清时,这种认识与实践已经更加稳定、成熟,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准确、系统的划分方法。总体上,清朝是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或称深水洋、黑水洋)三部来认识和划分海域的,并对它们施以不同的经略措施。在晚清官员方濬师的时政笔记中,有一条重要的记录,“中外诸洋,以老万山为界。老万山以外汪洋无际,是为黑水洋,非中土所辖。老万山以内,如零丁、九洲等处洋面,是为外洋,系属广东辖境。其逼近内地州县者,方为内洋,如金星门其一也(道光十八年正月,广督邓迁桢奏折)”, 较为清晰地反映出清朝对内洋、外洋和大洋间界限的基本认识,并点明了洋面界限与管辖权之间的关系。首先,清朝对海域的管理是有“中外之别”的。老万山以内是为“中”,无论内洋或外洋,均属于清廷日常的、具体的管辖范围之内;老万山以外是为“外”,“非中土所辖”,不在日常的、具体的管辖范围之内。可以说,“中”以内的“内洋”与“外洋”的统一是确定的,而“中”与“外”之间“辖”或“不辖”的区别也是明确的。其次,清朝对于内洋与外洋之间区别的认识也是清晰的。清朝有关内、外洋的文字记载及相关舆图大多记录于沿海州县的地方志中。对于内、外洋划分的时间,当始于康熙朝晚期, 到乾隆时期,有关内洋、外洋的确定已经在当时编修的地方志中显示出来。 在这些沿海地区方志中,因内洋是“逼近内地州县者”,有关内洋的具体范围、四至界限及其图示等记载是较为详细、明确的,但对于外洋的相关记载,则存在“淼淼不胜书” 的客观困难。王宏斌的研究认为,内洋是靠近大陆海岸或岛岸的海区,由沿岸州县和水师官兵共同管辖;外洋是内洋之外、以距离大陆海岸或岛岸最远岛礁或航线为标志所形成的洋面,由于超出了行政文官的日常管理能力,交由水师官兵专责巡哨管辖。此即所谓“内洋失事,文武并参;外洋失事,专责官兵,文职免其参处”。在内洋的地位及其管辖权的界定上,清廷的观点和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即内洋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内水”,是不准许外国军舰兵船和非法商船进入的。例如,1814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在呈嘉庆帝的奏折中报告说:“近来英吉利国护货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竟敢驶至虎门,其诡诈情形,甚为叵测”,并奏请整顿水师,慎重海防。嘉庆帝为此谕令:“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 道光年间,清廷还专门制定出台了《防范贸易夷人酌增章程八条》,其中第一条即明确规定:“外夷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在内、外洋的军事管辖方面,清廷施行的水师官兵巡洋会哨制度是在继承明朝制度、发现新的问题、不断修订优化等一系列复杂过程中,历康熙至嘉庆百余年时间,逐步在不同海区推行并完善的。例如,1689年,“议准:水师总兵官不亲身出洋督率官兵巡哨,照规避例革职”。1704年,“议准:广东沿海地方派定千把总带兵会哨,副、参将每月巡察,每年春秋之际委令总兵统巡”。1801年,制定《核定巡洋章程》,“将粤洋区分东、中、西上、西下四路设立洋巡船只,就各镇协营所辖洋面地方,派拨镇将备弁等员,率带本管兵丁,每船三、四、五十名不等,配置炮火器械,定为统巡、总巡、分巡、会哨各名目,分别上、下两班,先将各员职名造册送部,遇有失事,即按照原报各职名题参疏防”。1836年,批准《闽浙二省巡洋弁兵处分酌改章程》,规定“洋面巡弁以千、把为专巡,外委为协巡,都、守为分巡,副、参、游击为总巡,总兵为统巡”,对负责巡洋任务的官职按照管辖范围、职位高低等,进行了明确划分;在此基础上,如“遇有失事,初参限满,不获,将专巡、协巡、分巡各官均降一级留任,贼犯限一年缉拿;二参,不获,各降一级调用,贼犯交接巡官照案缉拿”等, 详细规定了对以上官职官员处置海上失事等事件不力的相应惩处措施。清廷还根据季节的不同,规定了巡洋会哨的方法、时间和地点;同时为了限制水师官员逃避风险和责任,还规定水师高级官员必须亲自带领战船在内洋和外洋巡哨等,同样制订了严密、严格的问责条例。在水师巡洋路线方面,乾隆年间《泉州府志》详细记载了康熙末年广东水师副将吴陞巡海的情况:“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 反映了吴陞从今海口出发巡视南海的情况。道光年间,琼州知府明谊在其所修《琼州府志》中记载:“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西接儋州营洋面,东接海口营洋面”, 表明清朝水师至迟自此已巡洋至今南海南部海域一带。此外,《新修会典〈广东舆地图说〉》中也清晰划出了清朝水师巡视南海的巡洋路线:水师“每岁例有巡洋,东自南澳之东南南彭岛,而迄防城外海之大洲、小洲、老鼠山、九头山……皆粤境也。今之海界以琼南为断,其外则七洲洋,粤之水师自此还矣”, 可见水师巡视南海是年度定例。外洋之外,是无边无际的“大洋”,“非中土所辖”,是中国与周边隔海相望国家间的“共享之海”。在中外关系上,清代中国以儒家名教观教化天下,与周边海上国家,主要是北部朝鲜、东部琉球和南部越南,建立天朝—藩属关系。其宗藩制度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强推的宗主国—附属国政策有着本质差异。诚如李鸿章就中越宗藩关系所言:“西人公法,谓彼于所属藩邦,皆有大臣监守,中国于越南政事、外交一切不问,但受朝贡而已,与泰西属邦不同。” 在治海方略上,清朝与海上周边国家同属“中外一家”,共享“大洋”渔盐之利、舟楫之便,而不在于像内、外洋那样具体、实在的分区管辖行为,由此实现海疆经略中的“以不治治之”。但是,“共享”并不意味着“无序”。以“天下体系”下朝贡与回赐为重要内容的政治、经济秩序为基础,包括大洋在内的广阔海域上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海上安全秩序,其内容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为周边海上国家提供基本安全保障,周边国家“誓不犯边”,并在“天下体系”之外层扮演“屏藩”角色;二是中国水师负责维护海上航行安全,采取巡海、镇倭等行动,保障官方朝贡贸易和民间经济社会交往的正常秩序;三是“协和万邦”,一旦有事,中国可被邀请居间斡旋甚至直接介入藩属国间及其内部矛盾,重建地区和平与稳定。综上,从内洋、外洋到大洋,又从大洋到属邦,清朝前中期采取三部统分之法经略海疆,持续、有效地实现了对周边海域的经营和管辖,并与周边海上国家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基本实现了东亚海上的和平与稳定。(三)晚清政府以内外举措应对海疆安全危机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周边的琉球、越南、朝鲜等海上邻国渐次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中华“天下体系”的内部性被一举打破,遽然崩塌。从藩属到大洋,又从外洋到内洋,东、南海疆从此直接暴露在殖民主义列强面前,成为中国被迫卷入西方条约体系的前沿。唇亡而齿寒,面对紧迫的海疆安全危机,清政府采取了对内、对外两方面措施予以应对。对内措施方面,清政府以近代主权原则强化对海岛、海域的管理。面对列强非法勘测、侵扰渔民、侵占岛礁等举动,清廷特别是广东地方军政官员,及时学习并运用当时通行的国际法规则,采取了一系列彰显主权的海上管辖行动;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成功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东沙群岛主权,并向国际社会宣示对西沙群岛主权权利。1864年4月,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乘坐“羚羊号”军舰来到中国,声称“欲自津由水路进京”。在天津大沽口海面,李福斯遇到了当时正与普鲁士爆发领土冲突的丹麦的三艘商船,并迅速将它们扣留。对此,总理衙门向李福斯发出一系列照会和复照,坚持大沽口拦江沙外“乃系中国专辖之内洋”,“并非各国公共海洋”,且“中国所辖各洋,例有专条,各国和约内均明此例”,从国际法和双边条约两方面,有理有据地阐明了观点立场,最终迫使李福斯退让认错。这一维权举措,是“目前有案可查的、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后由中国政府自觉采用国际法原则处理中外交涉事件的第一回”, 在近代中国海疆维权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初,南海东沙岛上的丰富磷矿资源引起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的注意。经数年筹备之后,1907年,此人带领200余人侵入东沙岛,以武力赶走了岛上的中国渔船和渔民,并拆毁了岛上的天后庙,将岛上中国先人的“坟冢百余座用铁器掘开,取出各骸骨”“进行焚化,推入水中”, 企图彻底抹去中国渔民在东沙岛的生产生活痕迹。强占东沙岛后,西泽吉次擅自修建码头和铁路设施,大肆开采岛上磷矿资源,并源源不断运回日本。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激起清朝封疆大吏特别是广东官员们的强烈愤慨。为此,两广总督张人骏派人全面搜集关于东沙岛属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和图籍,并与日本领事展开多次谈判。日本本来妄图以所谓“无主荒地”之说无理狡辩,但在大量史料证据面前最终不得不承认东沙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在与日本领事交涉东沙岛主权的同时,张人骏为避免侵权之事重演,于1904年4月派遣副将吴敬荣等前往西沙群岛巡视勘察。关于此次勘察,张人骏在奏折中提出:“勘得该岛共有15处,内分西(东)七岛、东(西)八岛,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 为此,张人骏下令筹备西沙岛事务处,委派省内官员办理相关事务,并派遣水师提督李准、广东补用道李哲浚、署赤溪副将吴敬荣等再次巡视西沙。1909年5月19日,李准等率领官兵和测绘员、化验师、无线电工程师、军医、摄影人员、木工、泥水工等170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兵舰,从广州出发,于6月5日抵达西沙,考察了罗拔岛(甘泉岛)等大小15处岛屿。 李准巡海过程中,采取了包括立碑志记、鸣炮升旗、绘制岛图,以及归来之后重新命名西沙群岛等一系列行动,成为晚清中国主动运用现代主权武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宣示海疆主权的重要历史实践,至今具有深远影响。对外措施方面,晚清政府希冀以“西式法则”改造中外宗藩关系。清王朝虽然在西方列强的外部冲击下不得不学着适应西方国际社会的一些国际法通行规则,但在心态上还很难将自己视作地区国家中的普通一国。因此在处置自身与藩属国关系、应对藩属国与列强关系时,清廷仿佛一面急于表现“先进”,一面难以摆脱“落后”,其应对之道就是通过“西式”努力存续天朝—藩属体制。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力主下,晚清政府试图打造一个运用“条约体系”框架、本于“天下体系”实质的“中体西用”的“条规体系”, 最终不得不落得失败的下场。1871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修好条规》,在明确拒绝日本提出的“一体均沾”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内地通商权等要求的基础上,与其正式建立起近代外交关系。《条规》中,清朝试图以第一条款“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来保全琉球、朝鲜作为天朝藩属国的特殊地位,但这一设想很快就被日本用实际行动破坏了。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以强力推行所谓“琉球改制”,禁止琉球向清王朝朝贡,迫使琉球改用日本年号,并最终于1879年将琉球纳为日本“冲绳县”。中日两国围绕琉球归属权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和谈判,史称“球案”。在处置“球案”过程中,日本政府一直着眼的就是如何以“国际法”的名义取得琉球的“领土主权”;清王朝同样以“日本违反国际法”作为谈判筹码,但由于始终绕不开对琉球的“宗主权”,且对所谓“万国公法”的认识过于肤浅、幼稚,使“争与不争”均不得要领。例如在清政府关于“球案”的内部辩论中,驻日公使何如璋是主张对日强硬的,认为应明确“示日本必争”“示日本必救”;但另一方面,日本“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各国使臣与之评理”,其实质是将希望寄托于“国际公义”。 郭嵩焘同样提议:“准照万国公法存立小国之义,会同各国驻日公使议之,必能使之折服,既有抗拒,中国亦足以自解说,以无疚于心,而申大义于天下”。 李鸿章起初看轻了琉球的地位,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李鸿章也寄望于西方列强,并特别希望能够得到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居间斡旋。 因此,从辩论“争与不争”到1880年与日本草签《琉球条约拟稿》,再到因“俄事方殷”而提出所谓“延宕之法”, 晚清政府主要是从传统宗藩关系而不是现代主权原则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琉球问题,实际根本无心也无力真正保护琉球,只能眼见琉球终为日本所吞并。可以说,虽然清朝尝试“拥抱”“国际规则”,希望以此登上列强所赞赏的道德与法律高地,但这只是浮于“表”的层面;在“里”的层面,它对琉球地位的认识和观点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对于琉球是作为“大清国”的“邦土”, 还是为中日“两属”,抑或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晚清政府一直无法提出一套完整的、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在“蕞尔小国”日本和西方列强面前,晚清政府一方面无法彻底摆脱作为“天朝上国”的大国心态,另一方面却又深感理亏词穷,根本还无须辩论,就自认天朝体制落后于西式体制了。如此“大而弱”的矛盾处境,使晚清政府在处理琉球问题时竟“试图援引西方附属国或属国规范来维护王道政治体制,把中国传统宗藩观念中的‘存祀主义’与国际法糅合在一起”, 可谓传统东方“天下”秩序与近代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秩序碰撞、冲突的一个生动实例。“球案”只是中国所有属国被一个个割去的一个序幕。 自此以后,晚清政府愈发认识到,中华体系内的宗藩关系在日本这个深谙东亚体制的域内国家的破坏下,更加岌岌可危了。1876年2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其中第一条即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 正式迈出日本策划使朝鲜脱离中朝宗藩关系的第一步。1879年4月,日本“废琉置县”后,何如璋致函李鸿章,提出了“琉球既灭,行及朝鲜” 的问题。李鸿章此时也认识到,“若隐忍缄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将由琉球而及朝鲜,不如早遏其萌,使无觊觎。” 同年8月,福建巡抚丁日昌在《条陈海防事宜折》中,对处置朝日立约之事提出对策:“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 此观点得到了总理衙门的认可。在晚清政府的一系列运作下,朝鲜与美国于1882年5月订立《朝美通商条约》。不久,朝鲜即向美国发出照会称:“窃照朝鲜素为中国属邦,而内治外交,向来均由大朝鲜国君主自主。近大朝鲜、大美国彼此立约,俱属平行相待。大朝鲜国君主明允将约内各款,必按自主公例,认真照办。至大朝鲜国为中国属邦,其分内一应各节,均与大美国毫无干涉。” 以上经营,在晚清政府看来,是既攀住了美国,又让美国为朝鲜作为中国属邦进行了“担保”,是为应对日本侵朝的第一步。10月,在中国出兵助朝平息“壬午兵变”后,晚清政府又马上与朝鲜订立《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此《章程》开宗明义即讲:“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惟现在各国既由水路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其边界互市之例,亦因时量为变通。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 此《章程》的签订,标志着中朝宗藩关系首次以双边条约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先进”的条约体系的一部分,由此完成了清王朝所希冀的所谓“立约保藩”的第二步。然而在侵略者眼中,此条约、彼条约订了又订,根本一文不值。1894年,日本借口镇压朝鲜东学党起义,向入朝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由此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1895年4月,在军事和外交均已陷入被动的情况下,中国清朝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签订《马关新约》,其中第一款即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一举解除了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而中朝宗藩关系的废绝,也标志着存续千年的东亚“天下体系”的彻底坍塌。至此,晚清政府为应对近代海疆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对外措施全部失败了。四 清代中国海疆经略的当代启示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奠定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基础,实现了包括内地、边海疆在内的主权大统一和清廷主导下的“天下体系”秩序的大一统。 以“海”观“天下”,清代既代表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也目睹了中国与周边海上国家从封闭自足的“天下体系”向近代“开放海”视域下主权体系转型的历史。这段既蕴含结构又彰显进程的历史叙事,对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具有从国家观到治理观再到主体观的三重启示。(一)历史中国观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 这一重要论述提示我们,若以大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与周边关系问题,那么深刻把握中国与东亚发展大势,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由此,构建从历史叙事到理论总结再到实践创新的一以贯之的海疆治理理论体系,首要之事是形成基于本土经验的历史叙事。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的研究表明,清代中国海疆治理体系有其独特的系统结构和历史变迁逻辑,挖掘并提炼好其结构和逻辑,正是清代海疆治理研究为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提供的历史观、特别是中国史观的意义所在。一直以来,对于历史中国的国家形态及国家史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即使是在一些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学者那里,也都是“成问题的”,即历史中国是不是一个“国家”成了问题。如梁启超在其《爱国论》里就曾提出:“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氏之称禹域也。谓之‘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深受梁启超影响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同样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断定“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 白鲁恂(Lucian Pye)则更形象地说中国“将一种文明硬塞进一个民族国家框架”。 以上种种观点,正如当代学者姚大力所言,“好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居然一直不存在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 实际上,历史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国家形态及其国家史观,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只不过它不是所谓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态,而是生发于中华大地、在民族国家产生前很久就已经存在的“天下”形态。如果为便于探讨一定要使用“国家”来指称这一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天下国”;如果更进一步,要与西方国家理论建立可通约的社会科学沟通路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世界国家”。梁启超、列文森等关于“中国不是国家”的论断,不过全都是以西方标准看待历史中国罢了。本文认为,中国的历史国家,如“大清”或“中华”,与西方主权体系下的民族国家具有本质的不同。如梁漱溟所言:“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之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 这一超国家类型不是一蹴而就地设计、建构出来的,而是“在王朝有生有灭、新旧相替、疆域不断伸缩变化的时空中,逐渐突现出来的一个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层面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 至清中叶,同时将历世性和历界性 发挥至鼎盛的清代“天下国”,至大程度地造就了一个愈发接近现代的东亚“世界”,这个世界具有由内地和边海疆地区构成的广大疆域版图,具有与地缘邻近国家密切联系的开阔周边视域。此所谓“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历史中国的“国家观”天然地具有“世界观”含义,随着历史沙漏渗透至今,不能不影响当代中国对东亚世界,包括对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认识。因此按照从国家观到治理观的逻辑推演,一个“世界国家”必然具备着“世界治理”的眼界与胸怀。在安全治理的视域中,其表现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二)总体安全观的启示以“天下国家”形态为观照,清代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包纳内地安全、边海疆安全、属国安全乃至天下安全的总体安全治理观。这一安全理念既有整体性又有层次性,并凸显出东方文化崇尚的联系的特征。当它们被运用到海疆安全的治理之道上,就表现为对包括内洋、外洋、大洋和海上周边关系在内的多重要素及其关系的考量。这种从“天下国家”到总体安全观再到海疆经略的基本逻辑,对当代中国海疆治理,特别是对推动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中国是一个位于太平洋西岸、拥有数千年持续文明史的东亚大国,天然地与海上周边国家及地区形成了紧密的地缘关系。正是通过广袤的海洋,中国古代先民以探索与智慧克服重重险阻,造就了东亚海上“使臣不绝、商贾便之”的繁荣景象。一方面,在“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的天下之内,中国与朝鲜、琉球、 越南等周边国家建立宗藩关系,希冀以“王者无外”的一元理念,内守四裔,外立藩屏,共享“天下大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内洋还是外洋,中国对沿海岛屿及有关海域的认识和实际管辖(包括行政管辖和军事管辖)是明确的、有据的。对于大洋(或称深水洋、黑水洋),亦言明“非中土所辖”,说明“中”“外”诸洋的洋面与管辖界限之间的关系, 至少在中国方面看来,也是清晰的。在东亚海相对封闭的历史时期内,清代将海疆经略与中外关系作统筹考虑,实现了“中外一家”与“中外有别”的统一。基于以上的总体安全思想传统,当代中国高度重视包括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在内的周边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曲折发展中逐步得以重建,直至20世纪90年代,终于全部实现了正常化,东亚地区形势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近年来,中国与周边海上国家关系受到海洋权益争端问题的一些干扰,也因域外势力的干涉和介入面临一些困难。但总体来看,各方都在努力克服双边和多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大部分国家已认识到排除域外势力干扰对东亚海上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意义。特别是由于东盟多边平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一直发挥着积极、正面的作用,双方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道路上正朝着纵深方向发展。数十年来,中国看重与周边国家间“山川相连”“唇齿相依”的近邻关系,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在争端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随着自身能力的提升主动发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共建共享倡议。这些在当代中国周边外交话语体系中不断出现且历久弥新的原则、提法和倡议,正是“中外一家”总体安全观给予东亚海上世界的宝贵政治文化遗产。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为推进中国周边海上安全秩序指明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与路径。(三)国家主体观的启示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陆海兼备、邻国众多的国家,具备“世界国家”的理想、总体安全的视野和主动作为的动能,是正常、理性和可预期的发展结果。其一,中国长期是自己所知之“天下”内最强大的国家,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看待外部世界。汉代以来,中国将继承于先秦时代、用于处理“五服”“九服”关系的封贡制度施用于周边属国,建立起天下体系内的华夷秩序。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应中国内部的统一或分裂、强大或孱弱,“天下”在范围上有盈缩,在成色上有足缺,但中国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是宗藩关系中的“天朝”和“上国”, 是“天下”政治文化的提供者和施动者。其二,中国理性地以“和而不同”调和“天下一家”可能带来的模糊性,对于周边属国,“不问其国内之政,不问其境外之交”, 可以说对属国领土从无兼并侵略之心,对属国纳贡施以厚往薄来之意,对属国内政恪守自主自愿之道。可以想象,在中国治下的天下体系内,中国在物质、文化、制度上多处于先进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产品的提供者,这样使周边国家产生慕强、追随、“搭便车”或“凑热闹”的心理和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历史也反复证明,一个强大、自信的中国,会贡献于一个较为整合且总体处于上升水平的东亚。因此,虽然天下体系在表面上具有华与夷、上与下之间的不平等性,但中国作为体系内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与周边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中心—边缘态势,更多地表现为大国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不是小国的客体性和被动性。这也是当代中国一再主动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道路的历史底蕴所在。当然,中国不是只有经验,没有教训。恰恰相反,正是主要在海上,中国的历史经历了遽然转折。进入近代以后,东亚地区多数国家被西方殖民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也有个别国家为“维新自强”“脱亚入欧”而蜕变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邻国视作殖民侵略的对象。自此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历史性剧变,曾在东亚占据主导地位的宗藩关系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地区秩序消失殆尽。在脱下天下“宽袍”、穿上主权“紧身衣”的过程中,中国既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重大历史性改进,如建置台湾省、宣示岛礁主权、划定南海断续线等,也有试图在天下体系内补救与琉球、越南、朝鲜关系上的一系列失败;而最令人扼腕的,是由于东方“天下体系”从根本上受到西方“条约体系”的强大冲击,使得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国家”抱负与视野在所谓先进的“主权国家”面前彻底自绝。晚清以来乃至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外交的主体性部分或绝大部分地丧失了,给近代中国的国家命运带来巨大危害。这一历史进程的扭转,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型独立外交的建立,才逐步得以实现。大国之大,“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 经过七十余年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正在增加,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仍不时冲击国际稳定。以上态势突出地投射到仍不存在基本安全框架的全球海洋领域, 而东亚海域正是各大海上力量关注的焦点。美国主导的霸权主义海权联盟、中俄等新兴海洋大国的崛起和海权竞争意识日益增长的系列海上中等力量,使东亚海域面临着落入海洋地缘政治竞争陷阱的局面。作为东亚海域“前体系”的缔造者、“后体系”的被动接受者,当代中国需客观认识自己当前在世界格局和东亚格局中的角色、地位及未来走势,积极承担起“现体系”的推动者、改造者和引导者的责任。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将周边外交工作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妥善处理海洋权益争端,推动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周边海洋秩序,是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题中应有之意。而构建基于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对周边地区的一个全新认识。 在海洋安全秩序领域,中国的认识与选择至少要受到现行海洋权力格局、国际海上规则体系和复杂海洋争端形势的三重制约和考验。对此,提出三点思考与建议。其一,用共同发展缔造共同安全。发展是东亚国家的第一要务。对周边国家来说,中国要在强调构建共同安全的地区海上秩序的同时,持续提供推动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与开放平台,为地区经济增长和各国共同繁荣担负起大国责任。其二,以战略包容推进战略平衡。在早已“对外开放”的东亚海上,如今再度走向强大的中国是“后来者”,即“后来的利益参与者”。“后来者”受到既得利益者及攸关方的遏制或打压,在西方政治传统看来是理性决策的产物。对此,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应对。长期来看,中国需以战略包容的心态与策略,回应美国及其海上盟友在东亚海上的存在与实力,在对话和管控中实现积极或消极的和平的共存,直至实现战略平衡。其三,在“中外一家”与“中外有别”之间探索一般稳定状态。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间存在的海洋争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产物,不可短期或一蹴而就地简单化解决。在排除域外干扰的基础上,无论是争议的岛礁、海域或资源,实际都在东亚海域范围之内。在主权归属暂行搁置的前提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应将对东亚海域的目光投向有利于共同发展与共同安全的低敏感领域,或探索在非争议“共享之海”之上的共同治理与开发。中国在东亚海域及其周边地区的目标应是以我为主,探索一种和平、包容、均衡的海上安全秩序,最终朝着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而努力。这既需要中国的气度、智慧与意志,也需要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和理解;既是中国的主体选择,也将是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抉择。五 结论清代既是中国古代“天下国”发展至历史最高和最后阶段的产物,也是现当代以来中国与周边海上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安全关系的起点。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清代将总体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的具体实践之中,在对沿海防御和巡洋会哨制度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完备的海疆安全治理体系。在海域管理上,清朝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三部来具体划分。其中,对内洋和外洋,通过行政建制和水师巡查,实现日常的、具体的海上管辖。对于外洋之外的大洋,则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以不治治之”原则应用到海上。清朝制订了较为系统、严密的层级管理条例,以保障各地水师海上巡视、缉盗、护送、救助,以及海上经贸和朝贡安全等任务的顺利完成,有效地维护了东亚海上的安全秩序。以“天下”安全观为视野,清代海疆经略还包括以宗藩制度经营与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了东亚海上的长期和平与稳定。近代中国由强转衰,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东亚海域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及其三个最重要的周边藩属国琉球、朝鲜和越南相继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为应对海疆安全危机,晚清政府采取了内、外两方面措施。其成功之处,是迅速学习、接受了西方近代主权思想,及时强化、固化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及有关权益。但在处置传统宗藩关系等对外措施方面,清政府对时代主题的界定、对地区形势的判断、对西方列强的认识和对国际法的看法,总体来看是较为肤浅、幼稚的。这与其说是源于某些重要决策参与者的错误,军事、器物层面的落后或王朝政治体制的问题,不如说是历世历界的天下体系的失败。再伟大的人物、再精致的制度、再完善的系统,也无法超越由其自身营造的结构与进程。当“世界”变了,别无他法,只能直面接受,探索新生。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而知今,我们既要总结经验,也要吸取教训。透过清代海疆经略的体系结构和历史变迁逻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天下”思想及其现实表象的至高状态和遽然坍塌。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中国观、总体安全观和国家主体观的启示,应成为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地区海上安全秩序的重要参考。【收稿日期:2021-02-06】
【修回日期:2021-03-28】
【责任编辑:齐 琳】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数字经济智库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