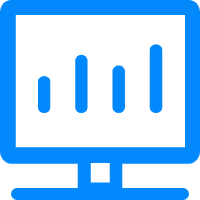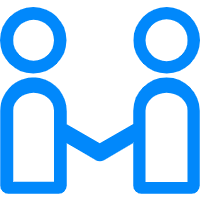冬至将至。冬至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冬至”命名的本意,如同一个温柔的提示,告诉我们真正的冬天才刚刚开始。冬至这一天,画八十一瓣素梅,而后日染一瓣,待素梅尽染,数九寒天也就过完,就又是春天。
要知道,春天可不是那时候才来的。自冬至起,大地阳气已经发动,春天已潜行在赴约的路上。
从前的冬至,记忆中的冬至,虽寒冷却很热闹。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全家团聚过小年,祭祖饮宴,为逝去的亲人上坟,俗称“送冬衣”。
从前是什么时候?记忆中的冬至,残剩的民间,已和上世纪一样遥远。节气时令,风土民情,在隔断地气的城市生活中,渐稀渐薄,终于成了画卷中的远山淡影。
撰文 | 三书
北半球最长的夜晚
《邯郸冬至夜思家》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设想冬至夜,在北方某个小城,某家简陋的客栈,一个旅人独坐灯前。外面飘不飘雪,他都没心思看,这个夜晚对于他,都是漫长而黑暗的。
这个夜晚不知有唐代,无论宋元明清抑或现代。夜晚只是夜晚,原始而永恒。所谓那朝代这时代,对于夜晚,都不过是梦幻泡影。但因为那位旅人,因为他留下的诗,本来只存在于空间的夜晚,便获得了一个时间的维度。于是我们说,那是某年某月某夜,诗人白居易在邯郸。
读诗不妨非理性,不妨放任文字带我们做做梦。此诗题目《邯郸冬至夜思家》,每个词,词与词组合在一起,已给人无限遐思。邯郸,这个地名不仅指地理上在北方的一个城,在时间意义上更是一个古代的城。而对于今天的我们,“邯郸”更是一个典故中的城,一个战国诸子寓言中的城。
如果把邯郸换成保定,“保定冬至夜思家”,我们立刻会觉得诗味被去魅了。虽然白居易当时的确在邯郸,并非为了美感而故意把保定说成邯郸,但对于诗的阅读,这却是个美丽的偶然。李白的《长相思》其一起句曰“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这首乐府诗纯属虚构,李白所代言的妇人未必在长安,可以在也可以不在,但写在诗里却是“长安”最好。如果换成“长相思,在广州”,别说广州了,就是换成今天的西安,诗句的色香味也将丧失过半。
古典诗歌对于我们的意义,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像“邯郸”、“长安”、“络纬”这些古典的命名方式,唤起我们的审美想象是不一样的。
较之命名与审美,古典诗歌传达的经验相对偏于简单,远不如现代诗的繁复和立体。这是古典诗和现代诗最重要的一个差异。游子独在异乡,逢佳节而思亲,白居易在这首诗中的体验,即使今天的读者不曾亲历,也能一读即懂,并且觉得很“熟悉”。因为在古典诗歌中,此类体验已被书写了太多遍,乃至已范式化套路化。
若从本质进行洞察,其实问题并不在经验本身。所谓“阳光底下无新鲜事”,古犹今也,但我们把这句话多读几遍,就会若有所悟地发现,所罗门真正的意思是阳光下新鲜的不是事。是什么?是对事的观照视角和介入方式。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都是差不多的,成为诗的那部分不是经验,是对经验独特的观照和审视。
白居易此诗并不独特,能够流传下来靠的如果不是他的名气,应该就是表达上亲切的家常感。“抱影灯前影伴身”,看似孤单寂寥,但因为能静静地思家,因为知道家人此时也在念着自己,那么这个最长的夜晚,也就不再是阻隔而成为紧密的连接了。
白居易还有一首写于冬至夜的《冬至夜宿杨梅馆》:“十一月中长至夜,三千里外远行人。若为独宿杨梅馆,冷枕单床一病身。”同样的口语感,同样的处境,只是地点从邯郸换到了杨梅馆,人从抱影灯前挪到了冷枕单床。这个夜晚离家更远,更冷,或因生病的缘故,似乎家人也渺茫了。
另有一首《冬至夜》,不妨一并来读:“老去襟怀常濩落,病来须鬓转苍浪。心灰不及炉中火, 鬓雪多于砌下霜。三峡南宾城最远,一年冬至夜偏长。今宵始觉房栊冷,坐索寒衣托孟光。”叹老嗟病,也无多少实质内容。
大概因冬至夜既冷且长,加之本应是家人团聚的佳节,故而羁旅他乡的诗人此夜更起乡思,更动诗情。写写诗心里也就感觉好些了,哪怕今年的诗仍是去年的诗,写诗这件事已在某种程度上救了自己。
《乌桕文禽图》
在最冷的冬天歌唱春天
《小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
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
杜甫这首诗写于冬至前一天(即“小至”)。诗中并没有什么“忧国忧民”,也没有什么“沉郁忠厚”,就算硬扯也未必能扯进“诗史”。我们应始终警惕,意识形态对生活的绑架,对现实的泛伦理化,都将遮蔽乃至扼杀一首诗。
什么是诗?有人已经在问。诗的定义千千万,正如人的定义。可以说诗就是人,有灵魂的人。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与其回答诗是什么,不如回答诗不是什么。诗不是政治,不是历史,不是社会学,不是心理学,不是等等等等。诗关乎生命的本意,诗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
在这首诗中,杜甫有的只是生活的细节:五纹、弱线、六管、飞灰、岸柳、山梅、云物、酒杯……从这些细微的事物中,杜甫写出了他在小至这一天,对阴阳运行季节变迁的敏感,以及在天地万物之中,在世界的残酷与命运的无常中,人如何获得生活的可能。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真诚,对他人真诚,那么他就会承认,生活的可能并不在于宏大的历史或时代,而是在于他与簇拥着他的所有日常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于他对所有细节的敏锐捕捉与丰富想象。
杜甫写诗的功力正在于他能从这些细节发现生活,并能从中揭示出人的存在。他如果活在另一个时代,可能会写不一样的诗,但诗永远是诗,因为他写的不是时代,而是人的存在。
我们对此诗稍加点醒。“天时人事日相催”,第一句真好。杜甫要求自己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也经常说到做到了,他的诗中总有惊人的句子。一般人但觉流光容易把人抛,即天时催人。杜甫在这里一并道出“人事”,对此我们现代人应该更有切肤之感,往往今年还没过完,明年的日程已经给你排好了。人对时间的体验原本是永恒的,就像小孩子,无所谓日月年这些概念,是天时和人事创造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时间”。在此二者的相催之下,人在衰老之前,心理上首先因焦虑而感觉老了。古人虽然生活节奏慢,但或因寿命短,他们对于衰老也很敏感,尤其诗人动辄叹老已成习惯。
“冬至阳生春又来”,这句对我们现代人很新鲜。从冬至开始进入最冷的数九天,然而这一天却是阳气已生,春天已经发动。下联的日增一线与六管飞灰,皆为由此而来的物象。今天比昨天白昼长了一点,这个变化很细微难以显现,我们虽然可以用日出日落的时间加以计算,但算出的数字仍是抽象而无法感知的。古人以女工日增一线来描述,实在很形象很易于感知。六管则是将苇膜烧成细灰,置于律管中,冬至前灰飞向下,冬至阳生则灰飞向上。
五纹、六管也并非诗人写诗当日亲眼所见之物,但作为人所共知的常识,用在诗中仍是形象化的,且语言上也自然玄妙地对仗成文。这则又是语言、事物和诗,三者之间不可言说的神秘关系。
尽管寒冬腊月刚到,但冬至阳气发动,诗人心中已满是春天的愿景。“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这两句读起来哪像要进数九天?岸柳将舒,山梅欲放,分明看得见、摸的着的勃勃生机。而“待腊”与“冲寒”,也似乎是滋润而欢喜的。一个人如若没有对生命的爱,能在漫漫严冬歌唱春天吗?
云物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诗人此时的心情且喜且悲,且叫儿子斟上酒来,不如痛饮。
项圣谟 《雪影渔人图》
美好的生活步行而来
《冬至夜发峡州舟中作》
舟中万里行,灯下一阳生。
不减在家好,都忘为旅情。
霜干风愈劲,云淡月微明。
况有诗兼酒,樽前莫问更。
南宋诗人范成大此诗,亦作于冬至夜,亦身在客途,较白居易的三首冬至夜诗,其处境更加荒野。但石湖此诗并没有叹老嗟病,也没有孤寂无聊,反而十分快意洒脱。
尽管“舟中万里行”,诗人却不觉得孤凄。即使在三峡的江上,他仍喜悦于冬至的“灯下一阳生”。不系情于一乡一土,而将生命安放于广阔的天地之间,有此大境界,烦恼忧戚自然就少。
在天涯就一定没有在家好吗?诗人说“不减在家好”,他没有否认在家好,但在天涯也挺好。或许他心里更加自在,乃至都忘了身在羁旅,此种心态在古代实属难得。农业时代的人安土重迁,只要出门在外,不论是不是真苦过在家,也往往被认为且自认为是苦的。诗人们常常哀叹不能赶紧回家,如果真的回到家里,心情也未必就比在外面更好吧。
真正通达之人,在家也好,在外也好,一好皆好,一不好皆不好。世上没有乐土,只有心里清净。心清净了,处处不妨是乐土。
峡州江岸,山林间霜风猎猎,云月也并不明朗,但诗人并不因外境欠佳而生烦恼。外境无所谓好坏,且不由我们做主,而心境却在于自己。何况诗人说,还有诗还有酒呢。有诗有酒,还有什么消化不了的烦恼?“樽前莫问更”,这句话说给自己,也说给旁人。当此长夜,喝酒吟诗,管他现在几点了!
冬至阳生,熬过数九,不知不觉,我们就又在春天了。这一年不可重启,也不必重启,经受住绝望的氛围,美好的生活就像春天,早已孕育在严寒中。它将出现,步行而来。
作者:三书
编辑:张进、李永博
校对: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