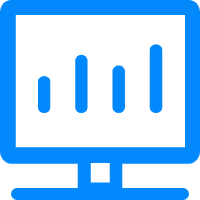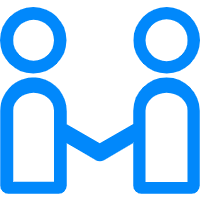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薛龙春(章静绘)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薛龙春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国书法篆刻史与尺牍文献,长期关注明代书法家王铎其人其书。近期,他先后推出了《王铎四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版)与《王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版)。前者是四篇长文的合集,后者则巨细无遗、竭泽而渔地网罗了各类有关王铎的资料。薛龙春谈到,他想做的不单单是王铎的书法研究,而是以王铎为中心的文化研究,而这两本专著,既是某一个学术阶段的研究成果,也为将来计划中的王铎研究专著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接受《上海书评》的采访时,薛龙春谈到了他所理解的王铎其人其书,与他的王铎研究的缘起,发展以及未来的计划。
《王铎四题》,薛龙春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292页,65.00元
《王铎年谱长编》,薛龙春著,中华书局2020年10月出版,1976页,388.00元
关于王铎的研究,给人留下的基本印象是,着重于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至于其人如何,以及他与钱牧斋的出降,都是一笔带过。不知您这次出版的《王铎年谱长编》,对丰富我们关于王铎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助益?能请您谈谈王铎其人此前不太受人关注,甚至为人所忽略的部分吗?
薛龙春:孤立地讨论王铎的书法意义不大。过去已经有很多类似的讨论,比如有学者说他的书法章法有“中轴线的摇摆”,这只是粗浅观察的结果,不是研究,也很难深入。艺术史研究强调艺术现象的历史性,必须将王铎放在晚明社会与晚明文化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他艺术形式的意义。
这本年谱,是我系统搜集与整理王铎与晚明书法相关材料的成果。在书中,我运用各种史籍、地方志、笔记、诗文集、书画作品、题跋、书信、日记等,细致重构了王铎的一生,他的行履、作为,他的诗文书画,他的友人,他的欢欣,他的悲慨,都在我展示的材料之中。我相信我是最熟悉他的人,有时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或许他当时的朋友中也没有我这样了解他的人。这本年谱向读者提供了这样一个个案:明清鼎革之际一位满怀名臣之想的文人,如何最终当了贰臣,在当了贰臣之后,又如何重新规划自己传于后世的形象。这个文人的观念、行为与艺术创作何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表征,和当时的社会文化、他各时期的社交圈又有怎样密切的联系。相信读者会从这本书中获得各种有用的信息。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文学史、绘画史和鉴藏史的学者,也会从中发现许多过去可能没有关注到的材料。
我们过去的研究热衷于讨论王铎的书法形式,但是对他的创作环境毫不关心。通过撰写年谱,这方面的问题就会涌现出来。比如,王铎在旅途中的书作常常显得有些怪异,这一方面可能与他在舟中场地局促有关(图一),另一方面也因为书写工具不能惬心,在旅途中的酬应之作,大多是求书人提供的工具与材料,他常常使用较小的毛笔,但要写很大的字(图二),有时他还得使用自己不经常使用的羊毫笔;又如,王铎入清之后经常参加北京贰臣的聚会,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喝酒,听昆曲,和歌人厮混,在这样的场合,他常常被要求即席挥毫,他曾向戴明说抱怨“刻下赴无益宴聚,又劳五指,奈何”(图三),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很享受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表演。在观众围观的环境中,王铎如何调动观看者的欲望,这最终在他的作品形式上又有什么体现,就成为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白谦慎先生研究傅山的书法应酬,指出傅山厌恶俗物面逼,甚至与他讨价还价,因此他的应酬通常带有报复性,作品的质量也很差。王铎则恰恰相反,他的应酬作品中有许多杰作,与他享受这种书写环境并善于操控环境有关。
图一:王铎《文语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二:王铎《杜甫诗轴》,广州美术馆藏
图三:王铎《致戴明说札》,香港近墨堂书法基金会藏
此前您在《上海书评》发表过《王铎,一个南明“贰臣”的标本》一文,在您看来,王铎何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标本?同样是贰臣,同样是名重一时的大家,他和钱谦益有何异同?与钱谦益心怀故国相比,王铎似乎甘心投降,个中原因是什么呢?
薛龙春:这个标题当时应该是编辑所取,不过似乎也可以这么说。晚明文化中产生了无数言不由衷的人,王铎确实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在1644年六月就任弘光朝大学士之后,他很快发现马士英专权,而弘光帝也没有恢复中原的愿望,于是三次上疏要求放还山林,语词甚为激切:“坏我国家者,……皆十七年之所以谄事欺蒙刑名雕刻为能事、卖官剥削为勋劳。……臣受此任,居于纶扉,亦仍旧之泄沓,隐默木偶欤?……甘为卢杞、李林甫一流人,辱名籍于史传,播臭声于千载耶?”可见这时的王铎对自己的名臣形象仍颇有期许,但令人咋舌的是,第二年五月,他就大张旗鼓地与钱谦益等文武大臣献城投降,并于1646年正月接受新廷任命。他成了自己最鄙夷的人。
晚明文化中还有另外一类极端的人物,如王铎的同年进士黄道周,当时的评价是,他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不仅不容小人,也不容君子。1638年七月,他上疏弹劾夺情入阁的杨嗣昌,不惜在朝堂上向崇祯帝叫板:“臣今日不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是陛下负臣。”皇帝拿他没办法,只说了句:“平生学问只得佞口。”但黄道周却以此为骄傲。读这一时期的史料,你会发现,大臣们争名的愿望,远大于解决复杂的社会运转问题的愿望。至于能力,则更值得怀疑,就像大儒刘宗周,为弘光帝开出的药方也只有“讲学”二字,在清兵窥江的紧迫情势下,这些建议都远水解不了近渴。钱谦益是王铎的前辈,王铎在他面前一直很谦卑(图四),关系也很好,尽管他们的文学主张有所不同,但都以公安、竟陵为针砭的对象,因此有许多共同语言。王铎去世之后,钱谦益为他写了墓志铭,在文中,他不仅鼓吹王铎的书学、书才与书品,还委婉地回护他降清一事:“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什么投降满清之后就颓然自放,溺情昆曲,是因为他仍有羞耻感,放纵的表象背后是深沉的故国之悲。不过,这个墓志铭像是钱谦益为自己写的。虽然在《无笑》一诗中,王铎描述了自己入清后无言无笑、味同嚼蜡的生活,但他似乎从未像钱谦益那样怀有异志,更没有任何反清复明的实际行动。
图四:王铎跋钱谦益藏《圣教序》宋拓本,北京保利2014年春拍
这与王铎的政治遭际有关。1638年,是王铎疏离权力中心的转折点。这一年春天,他经筵讲学,有所触忌,谈到当日的时局,又有“白骨如林”等语,讲毕崇祯帝大怒,谓其敷衍数语,支吾了事,全不能发挥精义。到了七月,王铎听闻杨嗣昌与满清和议,认为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上疏之后,杨嗣昌奏辩。结果是王铎虽免遭廷杖,却被降三级照旧管事。此时他因与同僚许世荩交换保举对方的子弟一事,为御史喻上猷所纠,在回奏中,他一一例举四弟王镆的才识,并请求说:“皇上倘采臣言,臣愿与弟镆得四千强兵,请缨以繋寇颈,致之阙下。或巡边阅师,修理边堡,可效一臂之需。”(图五)
图五:王铎《手稿》,中国嘉德2011春拍
不过对这个主动请战以示忠心的申请,崇祯帝丝毫并未理会。到了年底,满怀失望的他连续上疏要求归田,对朝廷的愤懑形诸辞色。1640年冬天,王铎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他终于离开了北京,因为遇到父母连续病逝,他在黄河北岸的怀庆府守制一年有余,此后直到1644年五月他始终携带众家小辗转于新乡、南京、苏州、嘉兴等地,躲避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
到了弘光朝,他虽然以外地被任命为内阁次辅,却与首辅马士英水火不容。弘光召见王铎时,“屏去左右,进臣于膝前,皇上流泪,臣亦流泪,曰:有当言卿即言,勿学马士英蒙蔽也。”但当他要求弘光帝解除马的兵权时,弘光帝却不为所动。在清兵进入南京前数天,弘光帝与马士英先后出奔,并不关白王铎,以至南京民众抓住王铎,群殴至须发尽秃,勋臣赵之龙将之移入中城狱,才获得保全。可想而知,王铎关于旧朝的回忆没有任何愉悦。在《纪昔年旧事》一诗中,他甚至感激清兵的到来:“乙酉群孽兵自起,攘夺锱铢成荒垒。……喜逢大军收婵连,苏死回伤见阳天。”入清以后,王铎颇为享受这难得的太平,在接受新廷任命后不久的一件书作中,他写道:“燹惊颠沛,乃得优游燕衎,昨年江澨,安得有此欤?”(图六)这是一个饱经战乱后的明代官员,重回平静生活之后的由衷欣慰。当年三月,王铎次子王无咎考中进士,王铎对他曾有这样一番交代:“吾自幼读书,任世事,幽轲三十年,志未行,今老矣。汝曹其竭力报国。”一方面他为自己不为明朝廷所用感到遗憾,另一方面要求子弟矢志报效满清。类似的劝诫,也屡见于他赠予清初新进官员的各种序文与书作之中。
图六:王铎《赠侯佐文语轴》,香港艺术馆藏
从政治道德的角度,人们当然可以指摘王铎的失节,但王铎在回应明亡之后少有人臣殉节一事时的一段话,颇耐咀味:“是上剥下,下亦剥上也。操锷而自剚其躬也,不克以天下为心。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为崇祯、弘光这样的帝王殉节,他不愿!不愿!不愿!王铎内心是否有深深的耻辱感?我想熟读儒家书的王铎是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文化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对个人感受与个人欲望总体上是鼓励的,这些感受与欲望也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王铎入清后的七年,并非生活在没有尊严之中,他在属于自己的文化共同体中仍备受崇仰。就书法而言,北方五省皆奉为宗主。
您谈到,这部《王铎年谱长编》完成之后,“重构王铎的生平、仕履、行踪、交游及艺术创作活动就成为可能,这也为勾勒王铎的同僚圈、乡党圈、艺文圈等不同的社会网络提供了一个基础”。那么,王铎的同僚圈、乡党圈、艺文圈有着怎样的特点?他都与哪些人物来往?这些人物对他的文艺创作乃至政治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们如何评价王铎在政治上的选择?
薛龙春:这些圈子不是固定的,在王铎生活的不同时期,圈子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以同僚圈而言,入仕之初自然是同为庶吉士的一干同年进士,他们大多在散馆后任编修或是检讨,如蒋德璟、郑之玄、文震孟、黄道周、陈仁锡、倪元璐、南居仁等人,也有陈子壮、赵南星、何吾驺、孙承宗、姚希孟、吕维祺(图七)、董其昌这样的前辈;1635年他到南京任翰林院掌院,自然就是南京衙门的一班官员,如张镜心、张四知、屈动、范景文、赵志孟、戈允礼、郑三俊等;1644年任弘光朝次辅,则是史可法、钱谦益、刘宗周、马士英、高弘图、阮大铖、张慎言、杨文骢等人;入清之后,主要是在北京任职的贰臣圈,如梁云构、戴明说、龚鼎孳、张缙彦、薛所蕴、李元鼎、张鼎延、宋权(图八)、孙承泽、陈名夏、陈之遴、刘正宗、周亮工、曹溶等人,也有一些清初入仕的如单若鲁(图九)、魏象枢、魏裔介、傅维鳞、法若真、杨思圣等,他们大多是王无咎的同年进士。当然,我这里提到的只是他朋友圈的一角。
图七:王铎《挽吕维祺诗轴》,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图八:王铎跋宋权藏范宽《雪山萧寺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馆
图九:王铎赠单若鲁《花卉卷》,故宫博物院
这些友人中有一些是当日的名臣,如孙承宗、范景文、郑三俊、史可法、张慎言;吕维祺、黄道周、刘宗周、孙承泽、魏象枢是理学名家;钱谦益、龚鼎孳文名藉甚,薛所蕴、刘正宗、张缙彦也是重要的作家,阮大铖则是度曲高手;董其昌、黄道周、倪元璐是和王铎齐名的书家;董其昌之外,戴明说、法若真、马士英、杨文骢等都有画名;宋权、孙承泽、戴明说、李元鼎(图十)、曹溶、周亮工则是重要的收藏家。我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说清这些人对王铎有哪些影响,但是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比如王铎和董其昌的交往,我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在与董其昌相交集的时期,他们感情甚洽,在学古、鉴定、社交策略及传播手段上,董氏都启发了年轻的王铎。而在董其昌去世之后,王铎却毫不讳言他和董的分歧。在绘画方面,他不认同董源在山水画史上的宗主地位,而对荆关李范等五代北宋画家给予更高的评价。在书法方面,与董其昌推崇“秀”与“淡”不同,王铎将气势、力量与层次的繁复作为经营的重心。在绘画与书法上追随董其昌的松江派与时流,也成为王铎严厉批判的对象。甚至对董本人,王铎也表现出轻视,1649年十月,王铎在一则题跋中指出董其昌与他的代笔人赵左相比,“赵厚董薄,赵大董隘”,他认为董氏小楷有晋人遗意,但草行大书则没有讨论的必要。在书法上,王铎为适应立轴新形式对整体感的要求,完成了以结构模式对董其昌用笔模式的取代。董、王之间的分歧成为当日书法新变的动力,但王铎对偶然性的强化又隐然可见董其昌所提倡的“生”之美学的遗响。
图十:王铎跋米芾《韩马帖卷》 ,故宫博物院
由于王铎的友人大多投降了满清,因此对王铎的政治选择,他们大多采取同情与回护的态度。就贰臣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言,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危机,也有共同的消释耻辱感的内在要求。与钱谦益在墓志铭中对王铎的回护相一致,张凤翔在王铎墓表中也说:“归或呼青楼,杂沓桐阴梧月间,琵琶声噪唳凉婉,衣垢不浣,病不尝药,亲者怪之,贻书劝曰:‘素不迩声色者,今际开辟,曾无所光赞,而沉湎若此,谓平生何?’笑不答。更谏,乃曰:‘少也贫,从未适吾欲,今逢盛世,待老臣以不死,诚溢望外……’”张镜心《赠太保礼部尚书王文安公神道碑铭》亦称:“出则召歌童数十人为曼声,歌吴歈,取醉,或宵分不寐,以为常。……间召青楼姬,奏琵琶月下,其声噪唳凉婉,辄凄凄以悲。居尝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肯服药,久之,更得愈,愈则纵饮,頺堕益甚。”这是清初贰臣传记书写的一种模式,他们笔下的王铎入清以后沉湎声色,不沐不浣,生了病也不吃药,似乎将入清以后的岁月视作苟且偷生,这种修辞策略是刻意强化王铎道德感的一面。
王铎无论是诗文还是书法创作,都一味求奇求怪,这种思路是如何形成的?赵园教授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提到,晚明的士人之中普遍存在着一股“戾气”,这种社会风气与王铎的创作思路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薛龙春:无论诗文书画,人们视之为奇怪的,王铎恰恰认为是正体。比如当人有指王铎好写“奇字”,王铎辩解说:“盖俗字、野字、吏书、商贾字,及演义传奇一种邪书,浸淫以夺正体,而正书反讶为奇字。不亦深可慨乎?”
相比起奇怪,王铎作品给人感受更强的是“粗猛”。这和这个时代的气质有关。明代自天启朝以来,吏治失序,民怨沸腾,加之清兵窥视关内,一时战乱频仍。其时朝野普遍弥漫着难以消除的戾气,如赵园先生所观察的那样,因为这种戾气,晚明的政治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滋生出一种畸形与病态。陈仁锡将这种戾气的产生归结为中外太隔,上下不交,因此人气不和,戾气凝而不散,怨毒结而成形。这种戾气最终带来政治的崩溃与陵谷迁变。
这种朝野之间普遍弥漫的戾气,与士人意欲消除末世衰飒,重铸磅礴元气的诉求相交织,似也影响到书法作品尺幅的展大,以及对粗猛之气的追逐。王铎曾一件条幅的题跋中写道:“绫帧上下不绰,极欲纵笔,不繇纵,岂非命欤?”(图十一)这件作品超过两米,而王铎尚恨其短。另一件立轴的题跋也说:“苦绫不七尺,不发兴耳。”王铎观摩古画时也经常发出“小不及大”的评论,在为高克恭一件山水大画作跋时,王铎写道:“昼日对此画,长人壮心,坚人强骨。”顺治辛卯(1651)二月,在常州友人庄冏生家中,王铎见到黄公望一件长达三丈的巨作,大为赞叹,以为“元气含吐,草树滃郁,泉石变幻,胸中一派天机生趣与墨渖湿流”。而王铎经常批评松江一派狭小,不能博大深厚,即使稍有小致,也只是像盆景那样,“二寸竹、七寸石、一寸鱼耳”,其魄力自无法与四海五岳相颉颃,又说倪瓒一流竞为薄浅习气,他们的画作大抵二树、一石、一沙滩,便称山水,何能和荆、关、李、范的巨障相提并论?(图十二)这里所说的倪瓒一流指的就是董其昌及其留给画坛的遗产,因为倪瓒正是南宗实际的取法对象之一。
图十一:王铎《五言律诗轴》,中国嘉德2005年春拍
图十二:王铎跋关仝《秋山晚翠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表达自己的审美倾向时,王铎更是毫不讳言对粗猛的青睐。在为友人乔钵诗集所作序言中,他批评唐宋时期的诗人元稹、白居易、苏轼、黄庭坚说:“譬之蝘蜒,非不眉颏荧然,爪尾轻秀,音响清细,无粗猛之气,然非龙之颉颃也,龙则力气充实,近而虎豹鬼鬽不敢攫,远而紫日丹霄云翳电火金石不能锢。”在这里,他将文章的细响与大音,比为虫与龙,二者气魄迥别。他甚至不惜“尽黜幽细而存粗猛”。矫枉必须过正,以王铎为代表的晚明书法正是以粗猛来回应董其昌的轻秀。从某种程度上说,高卷大轴是晚明政治文化环境的产物,其中蕴藏着巨大的迁逝感与变动感。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晚明书法创造了恢弘的格局与气象,但“戾气犹未尽消,雅道犹未尽回”。张瑞图的一件巨轴行书《王维诗句》,极好地诠释了粗猛的旨趣。这件长度超过四米的大轴,单行最多只有八个字,雄健饱满之中难掩衰飒之气。张瑞图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毛笔似乎不能完全聚锋,以至于笔画时常出现空心的现象。这种笔触可以诠释为“粗”,而作品的体量所带来的压迫感,则无疑是“猛”(图十三)。至于王铎书作,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
图十三:张瑞图《王维诗句轴》,美国观远山庄藏
您曾经提到,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学习书法以来,就一直关注王铎,这么多年下来,王铎对您本人的书法学习和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薛龙春:研究书法史同时又从事创作的学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研究与创作是一致的,像曹宝麟先生研究宋四家,书法也学宋四家,华人德先生研究两汉六朝,书法也不涉唐以下一笔;还有一类将研究与创作分开,如白谦慎先生研究八大、傅山,研究吴大澂,他写的最多的却是唐人端楷。我的情况大概也是后者,我研究王铎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的研究不完全以“求真”为目标,而有一定的当代关怀,今天有很多人欣赏与学习王铎的书法,说明他有些趣味和当代趣味有相似之处;二是王铎这个人物足够复杂,与各层次的社会交往也非常丰富,传世诗文书画作品及各种题跋、信札也多,透过这个个案来观察晚明社会与文化是可能的。
我个人的书法创作并没有明确的风格意图,我将之作为一种令自己感到愉悦的游戏。要说学书法的机缘,我其实是不错的,在碑学与帖学两个取径,我都有很好的师承,但未来能到何种程度自己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享受学习书法的过程。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汉碑与唐宋人对我影响最大,比如《乙瑛碑》与《礼器碑》,孙过庭与米芾,都是我反复临习的。此外,清代一些碑学书家的行书,如何绍基、翁同龢,我也非常喜欢。当然我看的要比学的多得多。看不明白,就什么也学不到。
在我看来,与其说书法的趣味在于技巧,不如说“见字如面”,字所反映的是一个人气质,一个有气质的人最令人着迷,其人不足道,则字也不值得珍视。气质有各种各样的,我最喜欢超逸之气。但写字又不能不讲究技巧,没有高超的技巧,超逸之气是无从体现的。从时间上说,书法是节奏自然舒展的艺术,从空间上说,书法是块面自然衔接的艺术。做到这些,而且自然,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也不光是技巧训练就能解决的。阮元致仕后的一批家书,我印象很深的,真是触遇生变,妙不可言。对他而言,这不过是长期书写养成的右手肌肉的条件反射,但背后是修养所决定的文化趣味。修养不到,写得再好,也是白开水。不过今天的书法家大多不会相信这些。
我非常欣赏王铎的书法,他的笔墨技巧令人惊叹,在楷书、行书、草书上都能跻身书史一流,在碑学未兴起的时代,他的隶书已经不俗。他的书学成就远在董其昌之上。王铎书作最重要的特点有二。一是呼应,在整体篇章中,遥山遥水别有映带,不是老手绝难梦见。二是意外,如他自己所说的:“如寂寥深山,独坐无人,老猿忽叫,陡然一惊。”他的作品因此有很强的观赏性(图十四)。但我不学王铎的书法,因为他的字学不好会有纵横习气。前面我说过,晚明书法有粗猛的一面,在他们身上可以说是特色,但学的人却很可能堕入恶道。今天学王铎的书家十之八九只得了蛮横。王铎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说怀素、张旭并非不佳,但后来学他们的总把字写坏,可以说是怀素、张旭的罪人。我要说,现在很多学王铎的书家,也是王铎的罪人。
图十四:王铎《雒州香山作轴》,《王铎の书法》条幅编
您此前出版的《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这次您也提到,您做的是以王铎为中心的文化研究,那么,您也会出版一部类似“王铎的人生与书法”这样的作品吗?
薛龙春:是的,这是我的抱负。2006年开始研究王铎时,一本像样的专著就是我的目标。我是研究艺术史的,不是专门做文献学的,所以《王铎年谱长编》只是我研究过程中的副产品。就像您提到的《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一书,在出版以前,我也写过一本《王宠年谱》。去年出版的《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出版》,原先是作为《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一书的前言来写作的,《辑考》的内容有四十多万字,涉及两百余人六百五十余封信,如果按时间而不是人物来编排,也可以看作黄易年谱的主体。做年谱、辑考一类的工作虽然费时费力,却是好的研究专著的基础。艺术史研究的目标不仅是材料的整理,还要能够解释艺术品,并与传统观念对话。没有扎实的基础工作,特别是系统的资料搜集、甄别与考证,一切都免谈。
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有自己的特点,好的学者要能发掘出他们身上的议题,而不是按什么套路来研究或是写作。我研究的王宠、王铎、郑簠与黄易几个个案分处于十六至十八世纪,我借助对他们讨论不同的问题,如王宠年不及四十而卒,但他的字不见得嫩,文徵明活到九十岁,但字也不见得老。我在《雅宜山色》中花了一章的篇幅讨论时间对艺术的意义。又如郑簠,身处十七世纪的汉碑热潮中,他以隶书鸣世,众多一流学者与诗人赠之以“八分书歌”,鼓吹他是“古”的代言人,但在乾嘉以后,他又被学者们集体指斥为“不古”,那么我们在艺术批评中常常使用的“古”,到底指什么?这种评价的逆转又是如何发生的?再如黄易,他只是一个河道低级官员,他如何成为乾嘉金石学的发动机?对个人在学术共同体中的身份与形象,黄易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加以形塑的?
与前三者相比,王铎在艺术史上的影响显然更大,我不仅希望通过研究来回应艺术史的问题,也借此对晚明文化作深入的反思。这本专著的提纲,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反反复复,主要的困难在于我将围绕一个什么样的中心议题来组织我的论述,这个中心议题可以是王铎与董其昌的竞争,也可以是王铎书法的创作情境,还可以是艺术品的功能与趣味的关系,不同的中心,就会有不同的材料去取与组织方式。尽管王铎的材料极为丰富,但我从未打算将什么都写进这本书里。
最近您也出版了一本《王铎四题》,出这本书是怎样的考虑?与未来的研究著作是什么样的关系?
薛龙春:《王铎四题》是应王家葵、贺宏亮二兄主编的一套艺术史小丛书的一种,字数只有七八万,是我四篇长文——《王铎与集王字碑》《王铎刻帖考论》《王铎诗文稿的文献价值与艺术趣味》与《工具、材料与王铎的书法》——的合集,这四篇文章写于2009年至2016年之间,或可视为我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不过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与未来的研究专著不会有多少重叠。
这几篇文章主要集中于以下的一些问题:
宋明之间对集王字碑的批评,何以从品格化的“俗书”转向“集字”工艺的缺陷?王铎为什么人终于临写集王字碑,并有那么多自己集王字的尝试,其意义是什么?
王铎有大量刻帖,如《拟山园帖》《琅华馆帖》《日涉园帖》《论诗文歌》《二十帖》等,除了《拟山园帖》为王无咎所主持,其他大部分是他的姻亲主持的,所收入的也是王铎赠予的作品、与主持者的通信以及主持者相关的家族文献,除了传刻书法,这些刻帖在塑造家族文化身份上有怎样的作用?
有意识的“作品”对日常书写产生怎样的冲击?我选择了一些内容一致的手稿与“作品”加以比较,发现其形式存在巨大差异。手稿无疑比“作品”更为自然,更是心画的流露,但无论是欣赏者、收藏家还是研究者,对手稿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作品”。这是为什么?
在过去的认识中,一个面目张扬的艺术家可能对工具、材料不加选择,但通过大量题跋与书札的整理,我发现王铎对材料异常讲究,他喜欢湖州笔、宣德笺、吴江绫、徽州墨,这些都是当日的文房名品。但是,精良的材料是不是一定就会产出书法精品,恶笔恶墨会不会也能写出杰作?
《王铎四题》所讨论的问题,大致代表了我一个阶段的研究旨趣。在今天的研究氛围中,艺术史所讨论的问题已经不局限于审美与技巧,艺术的历史性、艺术品与具体环境的复杂关系等,在新一代艺术史学者中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史研究已经突破美术的范畴,开始了历史学的转向。这本小书中的一些思考,正得益于研究环境的这种变化。关于研究专著,我已经写下较为详细的提纲,现在最希望接下来的一两年能有整块的时间,完成最后的写作。
责任编辑:沈关哲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