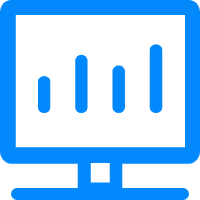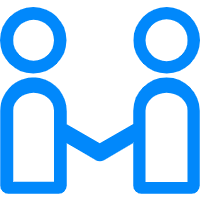来了来了,飘来还债了。
豆瓣8.3分的《刑侦日记》,今天就给你们翻牌。
这部开局就杀疯的港剧,颇有回归“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的港剧传统。
播出迄今,烂不烂尾不好说。
起码有一点,是被公认的好——
你永远可以相信惠英红
演这类略带点神经质的恶母,惠英红是一绝。
哪怕在全员神经病的《刑侦日记》里,惠英红饰演的杨碧芯,也是最有病的一人。
她是个母亲,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幻听,幻视,感觉全世界都想整死她。
她常常能“见到”一个贵妇和小女孩。
以慈悲的姿态,俯瞰着她的不堪,怂恿她自杀。
并且,要带上一双儿女一起走。
所以,险些毒杀年幼儿女的她,只能远远地逃去异乡治疗。
17年后,她再度回国。
疾病仍未治愈,拥有多个“面孔”,随时挣扎在正常与癫狂之间。
因此,“秒变脸”的神切换,成为杨碧芯每集必有的表演。
恍如幽灵的母亲,游走在人间与鬼蜮之间。
是杨碧芯,更是“中女”惠英红近年来反复被观众记住的一张张脸。
歇斯底里,非理性,极端化。
贤妻良母型的顾家主妇,很难轮得到她来表演。
银幕上的她,大眼睛里往往透着绝望,痴狂与怨毒。
图源|《幽灵人间》
但这类不算有新鲜感的角色,她每次演绎,都能让人尝出不同的滋味。
更妙的是,再神憎鬼厌的人物,都能被她赋予角色尊重感。
比如《血观音》里的棠夫人。
她是棠将军的遗孀。
以贵妇姿态穿针引线,看似做的是古董生意,实则是政商间做暗箱操作的中间人。
棠夫人的女儿和孙女,都被她当作待价而沽的商品。
片中有幕她与女儿棠宁(吴可熙 饰)闲话家常。
话说三分,剩下七分戏,留在眉梢眼角,要人细品。
棠宁和她聊得欢,顺势凑过去。
棠夫人笑笑,摸摸头,拍拍膝盖,让女儿枕了上来,继续抚摸她的秀发。
这是母女俩难得的温情时刻。
接下来棠夫人却笑着递出了一把刀:“你还记得廖队长吗?”
注意细节。
她问这句话的时候,逐渐收了笑,伴着话音收尾的,是一个得意的挑眉。
得到女儿轻声肯定后,她的笑才再度慢慢溢开。
什么意思?这一套话术她已经提前做过了演练。
前面鼓励小动物般的示好,只是铺垫。
为的就是放松女儿的戒心,掉入她用爱编制的陷阱。
而当棠宁识破了她的计谋,不愿嫁给廖队长做后妈时,两个人距离远了,气氛也骤然变冷。
棠夫人推了下棠宁,说了句大概全天下父母都说过的话:
我只是为你好
她讲得仿佛贴心熨肺,紧着眉,额头上都爆出了青筋。
却在下意识间,由并不流畅的国语,切换回了母语广东话。
这场戏还有一句说话,也是用广东话说的:
公主命 丫鬟身
这时棠宁已经从拒绝,变成了对母亲肆无忌惮的蔑笑。
棠夫人面子上挂不住,有一瞬间掩不了的阴毒流出来。
看这爱即地狱的表情,即可一窥人物佛口蛇心的心性。
这样的“变脸”,在《刑侦日记》里比比皆是。
就说她亮相的那场戏,与女儿叶朗晴并未相见。
可仅仅通过单向的人物观察,就侧写出了心态的变化。
刚开始,她是满怀期待的。
带着花来女儿画展,说到“妈妈”二字时,自豪溢于言表。
时隔多年初见女儿,她眼里盈着泪。
有欣喜,有爱恋,有隐隐的哀伤,更有思念成灾、一夕落地后的激荡。
再过片刻,杨碧芯已收敛了心绪。
看着女儿接受采访、提及对她的思念,面上只浅浅含笑,像个再普通不过的慈母。
转变发生在下一瞬。
女儿说她已经离世。
正常人的反应,是错愕、难过乃至愤怒。
精神病患的第四层反应,是会在强刺激下产生情绪抽离。
比如,下意识的眼神放空,身体抽搐如扭脖。
当悲怆的母亲在将将背身的那刻。
投向女儿的最后一眼,目光已如毒蛇。
好演员不光懂得抓住镜头前的灵光,甚至在镜头看不见的地方,也在调动所有情绪演戏。
你看杨碧芯的背影,步伐迟缓,微弓着背,往事的重压让人瞬间苍老。
但毫无踉跄的坚定,又预告了复仇风暴即将发生。
发现没,同样是演,杨碧芯是棠夫人的反面。
棠夫人是要在不爱中表演出爱;
而杨碧芯,则要在爱里诠释与疯狂与极端揪斗的不爱。
电视剧相比电影,情绪转换的动作设计也来得更明显。
能重拿,可轻放。
红姐对复杂人物的驾驭力,得益于驾轻就熟的经验与技巧。
更来源于生活这个最好的表演老师。
她习惯在还没进组前,用一星期的时间,以角色的性格去生活。
当活在角色里面时,不演,就是最好的表演。
吊诡的是,演过那么多母亲的角色,惠英红却从未当过母亲。
甚至,61岁的她,还没结过婚。
她的演员身份也是割裂的。
2011年的《武侠》,因缘际会地,凑齐了邵氏当年两大武侠巨星。
男有大哥王羽,凭一己之力开张彻“武侠新世纪”高峰。
女则是惠英红,香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凭打戏夺小金人的女明星。
命运使然,当年,惠英红以“打女”的身份,闯荡娱乐圈。
然而,昔年如长辈般指点后人的大侠,现在,却变成了衬托正面角色的反派。
让人依稀想起《三少爷的剑》里的狄龙。
从前带刀的时候,人们叫他傅红雪。
如今没了刀,就是黄山上无名的樵夫。
之于大多数打星,岁月如刀,刀刀催人老。
自古美人如良将,不准人间见白头。
当她既是美人又是良将时,遭遇的便是加倍的速朽。
惠英红曾说,她的一生相当于别人的两世,分割线是40岁的一场自杀。
第一世,她为了家人的生计奔波。
第二世,她才懂得为自己而活。
第一世的她,演出靠的是原始本能,是跟着导演“照葫芦画瓢”的学习与模仿。
甚至关于要演什么样的角色,她也没得选。
她入邵氏出演的第一个角色,难得便有名有姓,是《射雕英雄传》里仅次于恬妞的女二号:穆念慈。
选择她出演的理由,和郑佩佩差不多。
尽管二人都没学过功夫,但因为跳过舞,身体柔韧性好,打起架来姿态也就漂亮。
初次演出,惠英红的表现中规中矩,片中难度较高的武打戏份(如比武招亲)都是由替身完成。
但她让导演记住的,是大胆。
面对镜头,毫不缩手缩脚,见不到新人的生涩。
半是出于从三岁起,在红灯区要了十年饭的摔打磨炼。
半是因为咬紧牙关要熬出头的硬颈。
从卖口香糖、到舞狮、再到去夜总会跳舞,17岁的她,在社会这所大学里,早已读懂“逆天改命”四个字。
和懵懵懂懂“撞运”进圈的明星不同,她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清醒规划。
作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放弃当舞女时1500元的月薪,选择500元月薪的演员时,她妈妈是坚决反对的。
她让家人点头的理由是:“我现在是500元,做下做下就有可能是五万元。”
那个时候,之于惠英红,演戏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赚钱,就是要一步一步望到天。
所以在邵氏几个月做到主角后,她第一时间返回昔日让她舞狮的夜总会“探班”。
为的是,“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威风。”
所以《长辈》拿奖几天后,她就忙着跟老板讲要加人工。
薪水由年薪变到部头,就足够激励她继续搏命。
邵氏与她同期的女星,是钟楚红和张曼玉。
提起她们,惠英红不是不羡慕的。
从一开始,她就不愿意做辛苦的打女。
但大片场时代,拍板权落在老板手里,明星也只是打工的螺丝钉。
一朝成名,便给你定了型。
惠英红没读过什么书,身后又有数张口要养,退无可退。
命运,提前给她上了锁。
就像穆念慈一样,自幼跑江湖谋生的少女,要背负起和男性一样赚钱养家的壳。
她英气里淡淡的愁苦,是过早就被迫长大,尝不到孩童的天真。
造化弄人,惠英红的“打女”身份,是被塑造出来的,是被代表权威的男性所构建出来的。
甚至,连定义她的男性,本身也并不认同她的女性价值。
惠英红加入“刘家班”前,刘家良曾扬言女性并不适合做武打演员:
女演员就算打得好,观众亦不会接受,他们只觉得她在做戏。
武打片失去逼真感,还有什么气氛?
何况,大部分女演员拿起刀枪来,总是姐手姐脚不象样,还是用男的利落。
来源|《香港影画》
惠英红“打”出来后,他们则叫她“仔红”,并不把她当女人看待。
她在片场拍戏,工作人员会对她讲粗口,有些男演员甚至当着她面换裤子。
让她常常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女孩子。
那个时候的惠英红,会让飘想起她演过的一个角色——《戏说乾隆2》里的邱罔市。
《戏说乾隆》系列里最缠绵的一幕戏,是属于邱罔市的。
磨坊里,她和郑少秋饰演的乾隆相拥。
长发如瀑,腰肢柔若柳丝。
她被压在石磨上,伴着二人的热吻,豆子霹雳吧啦滚落一地。
可这属于女人的似水柔情,只出现在乾隆的梦境里。
她的名字“罔市”,是东南地区沿海人家的通称。
意为生个女孩,就“随便养活”,和“招娣”同义。
在重男轻女的湄洲,穷苦人家出身的罔市,从小就女扮男装,夹在男孩子当中练功。
后来便拜了妈祖,做了乩童,发愿终生不嫁。
女性身份,也是罔市的困惑乃至恐惧之源。
以致当乾隆点破她是女人时,她当即失态。
大吼着“我是男人”,跑至柱子旁害怕得发抖。
最终,罔市的选择,是跪别乾隆帝,终身侍奉妈祖。
惠英红的选择,则是征询黄霑的意见后,为《花花公子》杂志中文版拍摄裸体写真。
通过展现自己的身体,她想要告诉公众的,只是“我也是一个很有女人味的女人。”
图源|《今夜不设防》
只是,事与愿违。
重文轻武的影视圈内,依然把惠英红定义为,“会打”不等于“会演”的打女。
当花前面加上“霸王”的定语时,她便不再被视为需要珍重对待的娇花。
图源|《92霸王花与霸王花》
当属于打女们的天地,被喜剧片和荷尔蒙更重的男性警匪片占据后,找不到用武之地的霸王花,也只能慢慢凋落了。
小人物的宿命,大多便是随着大江湖而浮沉。
和惠英红同时代的那些霸王花,如今大部分在影视圈内,已查无此人。
为何偏偏是惠英红,可以从谷底再翻覆过来,行上另一个高峰。
甚至,迎来比早年更丰茂的事业之春?
从“小红”到被封神的“大红”,没人不喜欢这样励志的传奇。
他们喜欢把这叫做苦尽甘来,喜欢把她视为演员自我修养的典范。
而在飘看来,红姐如今之所以为红姐,恰恰在于她接纳了自己的不传奇。
在死过一次后,她还是害怕掉下来的恐惧。
她还是会有浓重的不安全感。
坐车永远坐在司机后面。
《怪你过分美丽》里,她出演的影后阮荔华,与她形成奇妙的映照。
息影多年,阮荔华复出伊始,是从容且自信的。
她认为凭借自己的名气,回归肯定会造成轰动性的话题。
所以,她一度坚持非大女一不演。
可人走茶凉的现实,却狠狠打了她的脸。
最残忍的一幕戏,发生在饭桌上。
因为破产着急还债,她不得不和大老板谈代言。
然而,这个粉丝却当面戳破了肥皂泡:尽管你是我的女神,你的商业价值也不值代言费。
她强忍着眼泪、勉强微笑的神态,何尝不是惠英红自己的人生?
复出后,学会了打电话求人,去争取小角色。
被删过戏,被白过眼,甚至因为演得太好,被对手骂,嫌她抢风头……
但与此同时。
她接受了自己会老,不再认为“老等于无用,等于犯法”。
她也接受了自己会不红,自己不可能一直是众星捧月的焦点。
过山车般的高低起伏,让2010年凭借《心魔》拿下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她最快乐的一天。
在去年《人物》的采访里,描述起这段经历,惠英红坦诚了她的“丑陋面”。
《人物》:可以描述一下你曾经度过的最快乐的一天吗?
惠英红:就是2010年,拿了第29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吐了一口气吧,因为过程很难受,心里想着,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看看今天的我,脸上挂着那种微笑。
我妹妹说,「你看你的脸,那种笑是在说,嗯,你看,说我不行?」
她告诉我,你这个笑容太邪恶了,你忘了你要感恩,你忘了,别人那样对你,你不要学他们,那样你和当时的他们有什么分别。你这几天样子都变了。
相由心生,我就马上知道,我要调整了。
来源|《人物》
这样的惠英红,并非大众印象里,那个完美熟女的投射——
风来,我自岿然不动。
恰恰相反,她是在俗世里摸爬滚打几回的,俗女。
会恐惧,会难过,会不甘,会心生怨怼。
哪怕得过再多的奖,哪怕工作能给予她足够重要的存在价值与生活保障。
她,依然希望拥有一段爱情。
她说,结婚生仔,“可以令我感觉正常。”
在江湖闯荡40余年,惠英红自承“表里不一”,和棠夫人有相似的一面。
所以她能理解棠夫人的恶。
《血观音》演到中段,她遇上妈妈过世。
处理完葬礼回组后,她迎来了杀女的重头戏。
那场戏她主动提出了修改。
原因是,棠夫人始终是个母亲,不是没人性的野兽。
是为了自身利益,才要坚持走下去。
于是棠夫人最后,从《心经》改念了《往生咒》,眼里滑落两行泪水。
惠英红小时候,常常会有人来家里勒索掏钱,把她爸妈骂到哭。
那时她不过十岁。
气不过,叫妹妹去买毒药,大声讲给他们听。
他们害怕,走了,再也没来家。
歇斯底里,保护了家。
可妈妈却觉得她很“歹毒”,至死未改。
半个世纪后,惠英红回忆起来,脸上挂着有些僵硬的微笑。
在湾仔,每天都有人死,坏人不是天生的坏人,但为了过好点,就可能变成歹毒或愚蠢的人。
来源|《今周刊》
那个始终被妈妈否定的野孩子,如今再也不是寂寂无名、可任人欺负的路人甲。
可她老虎般威风凛凛的皮相下。
却依旧有只会瑟缩,渴望温暖的小猫。
可站在高处四望,身边只余呼呼风声,别无他人。
一路走来使她成为如今,风筝般的女性。
漂泊,随风,傲然,自由。
而风筝的憧憬在于,可飞翔,亦可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