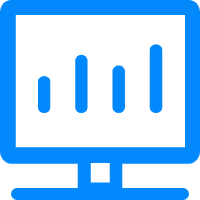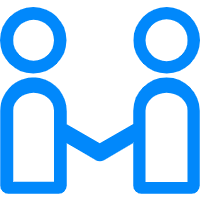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作为齐鲁文化”的中心,济南历来人文昌盛,从“二安”到“济南诗派”,乃至出现王献唐、季羡林等现当代大家,济南可谓代有名人出。这显露的“山峰”之下,便是巨大的文化本体,如藏书之风的兴盛。徐北文先生曾引用《山东藏书家史略》中数据,指出所收录的山东历代藏书家559人,远超南宋以来素称“文化昌盛之地”的江苏与浙江地区。济南的藏书家、爱书人在《山东藏书家史略》中立传的就有12人。藏书散出,最常见的就是流入书肆,而记载民国时期济南旧书肆的,当属张景栻的《济南书肆记》。
张景栻(1913-2006年),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祖籍济南历城南乡白土岗。其父为中医大夫,幼时的张景栻常跟随父亲到旧书肆买书,种下了爱书、读书的种子。从济南省立一中毕业后,张景栻考入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子承父业,悬壶济世。行医之余,张景栻常出入济南书肆及古玩店。几十年下来,他对济南书肆了若指掌,写下《济南书肆记》,为20世纪30年代的济南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史料。
摄影:李锋
济南旧书肆约从乾隆时期始,至20世纪50年代因公私合营而逐渐消亡,约200多年历史。主要区域在大明湖南岸至南护城河边老城区范围内,以文庙、贡院(今省政府后院)、和抚院(今省人大礼堂)为中心,包括大布政司街、小布政司街、后宰门街、辘轳把子街(今省府前街一带)、曲水亭街、芙蓉街、舜井街等地,许多古玩字画和旧书店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内。见于张景栻笔下的旧书肆即有近20家。这些书店大都有二三间门面,青瓦粉墙,房檐下悬挂一块店名匾牌。店内牙签插架分类有序,几张长桌上也摆满一摞摞线装书,从蓝布书套中垂下一张签条,书名、作者、年代、版式等一目了然。一些书店墙壁上还挂着名人字画,颇有书翰气息。
摄影:李锋
旧书肆的集中出现,与济南府作为明清时期府、县学及院试和乡试地点有直接关系。光绪年间,济南贡院内号舍多达14500多个。前来参加考试的书生们因各种原因,买书卖书极为频繁,逐渐形成了类似今天文化市场的交易场所。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山东地区屡经兵火战乱,济南周边地区的文物、典籍纷纷流入济南,著名者有聊城海源阁藏书、淄川毕自严家万卷楼藏书、曲阜孔氏微波榭藏书、新城(今桓台)王士祯藏书、潍县陈氏万印楼藏印、潍县高氏藏绝世砖瓦等。济南作为山东省府,全国各大书局均在此设立分店或联号,如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北洋书局、东方书社、中华书局等。其时,众多有价值的书籍,经史子集,珍本善本,甚至海内孤本,时有出现。1933年,国学大师钱穆到济南,让他记忆颇深的是,他在城中一家书肆看到大字《仪礼》一部,“眉端行间校注满纸,朱楷工丽,阅之怡神,竟是王筠手笔”。王筠为清代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为一时之冠。
摄影:海纳百川mcc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益于旧书肆繁荣的独特环境,济南学界出现了“山左三杰”:王献唐(1896-1960年)、栾调甫(1889-1972年)和路大荒(1895-1972年)。
王献唐为著名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精于文字、音韵、金石、目录、版本,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栾调甫长于墨学和古文字学,时任齐鲁大学国文系教授;路大荒为聊斋学研究第一人,为版本、目录、书画、古玩鉴定专家。“山左三杰”均在旧书肆收获颇丰。路大荒曾在此觅得蒲松龄诗文集手稿,该手稿后成为山东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他还觅得磁版张尔岐《蒿庵闲话》下册,与王献唐昔年所得上册合璧。该磁版《蒿庵闲话》上、下册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王献唐购得海源阁旧藏黄尧圃手校《穆天子传》和顾千里手校《说文解字系传》。王献唐后与著名墨学大家栾调甫等人合作,整理了从旧书肆中得来的山左先贤手稿精品,包括李文藻、周永年、桂馥、牟庭、王筠、许瀚、陈介祺、刘喜海、宋书升、高鸿裁等人的手稿20余种,辑刊为《山左先贤遗书》,在海内外有较大的影响。
因书结缘,“山左三杰”与张景栻成为好友,几人来往密切。栾调甫为学徒出身,1920年从上海来到齐鲁大学翻译医书。那时的高校不像如今只重文凭,由于他的墨学功底,被破格聘为国文系教授。梁启超极为佩服他对墨学的研究,称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课余,栾常优游于书肆之中。据张景栻回忆,他先在书肆认识了栾调甫,后由栾调甫领着拜见了王献唐。栾在淘书过程中,少有的一次打眼,便被张景栻捡漏买下。张景栻回忆说:“尝笑余收书好买些奇奇怪怪,然调甫先生其后收书亦好买奇奇怪怪。”对书的默契,使两人友情更胜以往。
王献唐对张景栻进入学术道路有着引路之功。张景栻常去王献唐家中,后来其购买书画多让王献唐过目。王献唐曾介绍济南藏书家马惠阶将珍稀宋刻《文选》残本转给张景栻收藏(后归山东省图书馆)。王献唐于战乱中购得海源阁旧藏黄尧圃手校《穆天子传》和顾千里手校《说文解字系传》,极为珍爱,并由此将其书斋命名为“顾黄书寮”。新中国成立后,路大荒任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劝王献唐捐二书。王献唐不愿,私下对张景栻说:“我要带着它们,让它们为我殉葬。”后因其老伴治病急用,《穆天子传》出让于著名藏书家周叔弢,《说文解字系传》则让归张景栻。张景栻一时拿不出足够的钱,便分几次付清,可见二人情谊深厚。
学者路大荒亦与张景栻以书相友。路大荒先居于大明湖畔秋柳园,后移居曲水亭街河东,于金石书画、书籍皆有所藏,“文革”中惨遭迫害而亡。张景栻挽联痛悼:“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柳泉故居共说鬼;论交四十年,忆秋园于旧梦,曲水新亭独怆神。”通过对联,张景栻对路大荒的生平、学术水平和他二人之间的友谊作出了动人的评价。
张景栻记下了他与王献唐、栾调甫、路大荒共游舜井街南首路西的友竹山房的轶事。店老板吕川升,字小舟,绰号“吕狠子”。栾调甫曾购《顾虎头画列女传》,被吕川升敲了竹杠,却说:“明知出价大,不得不忍痛出之。”栾、王均被其沾过不少便宜。某日,王献唐、栾调甫、张景栻到店,吕以自拓钱谱请王献唐题跋。王献唐提笔写道:“吕狠公以贩书起家,然较他人尚不甚狠。”一旁的张景栻笑着说:“吕狠子居然升公爵,加官晋级。”王献唐听后,继续写道:“以子爵升公爵,连升三级。”众人相视大笑。吕接着请栾调甫题跋,栾题作“恨公”。张题作“很公”。三人在书肆老板名字上做文章,王献唐无意中让吕狠子连升三级;而另外两人则是寓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有“心”方为“人”,使其从犬到人,留下了文化名家之间机智与默契的一段佳话。
除了这些轶事外,张景栻还记下了济南本地众多书商与藏书家的众生相。芙蓉街北首路东郑家书铺的经营情形在张景栻笔下十分有趣。“郑氏售书好索高价,顾客议价不成交,出门离去,追回再议,仍不成交,再离去,再追回。一进三出,七擒七纵,仍未成交。”“七擒七纵”让人想起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仍未成交”却把郑某的商人算计抛洒在地,让人读之捧腹不已。
济南本地吴友石、唐仰杜等19位藏书家在他笔下也栩栩如生。最让人深思的是其藏书的命运。在张景栻的笔下,许多藏书家生前辛苦聚书,却在一夕散尽。或因为保存不善,“老房漏雨,尽数霉烂”;或为家中仆人盗卖;或为不肖子孙低价换钱挥霍;或身故后“家人不能守”,斥卖一空。也有藏书家被生活所迫,出售珍爱藏品。例如张英麟,字振清,济南本地人,为清朝翰林,官至都御史,入民国,以遗老终。其故居在省府前街南端路东。张氏想要聚集有清一代文献,想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所以藏书中清人集部居多。可惜生逢乱世,其藏书散出不下万斤,书纸用来包花生、卷鞭炮。“爱莫能救,徒唤奈何”,八个字显出张景栻的伤痛之情。
由此引出一个话题:藏书的意义到底何在?藏书家身故后所藏书籍应向何去?这个问题很是让人深思。
作者:施永庆
来源:新黄河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