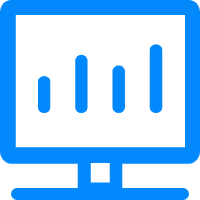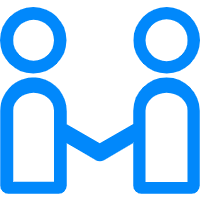王诤
在度过了自己的百岁生日近两个月后,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今晨仙逝。了解他,或是但凡接触过他,看过他接受访问或出镜讲话的人们,恐怕都会和我一样,惊诧于一位耄耋老人,何以在人生的夕阳晚景,依旧葆有如此丰沛的情感?记得他上董卿老师的《朗读者》,提到自己开始翻译诗词是在1939年,翻译的第一首诗便是林徽因的《别丢掉》。而动因呢,却是当时“喜欢一位女同学”。
讲到“一样是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老人在节目中鼻头一酸,眼眶竟然红了,完全是他翻译过的《牡丹亭》题记中的况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样子。彼时彼刻,到底是林徽因、徐志摩间的天人永诀,还是自己过往的爱而不得令许渊冲感伤难抑,确切的答案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吧——反正,许渊冲的夫人照君就坐在台下。镜头扫过,夫君的坦荡和炽烈,虽令夫人微微嘟起了嘴角,看上去倒也不以为意,那旁人又缘何置喙呢?
许渊冲 受访者家属供图
但不管如何,许渊冲毕生的译介志业是因情而起,当是确凿无疑。今年三月底,去北大“畅春园”拜访许先生,老人拿出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和昆明天祥中学编写的《许渊冲画册》兴致勃勃,记得他找到一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友人合影,蜷着的手指在照片中每个人的脸孔上划过,最后停在他身旁一位清癯端庄、满头银丝的女士那里。
她便是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的女儿梅祖彬。许渊冲回忆说那是1942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前,出演德克的英语剧《鞋匠的节日》,“当时我是男主角,梅校长的女儿梅祖彬演我在戏里的夫人。我演的是鞋匠,追求一位女店员(梅祖彬饰演)。梅祖彬身高一米七四,是西南联大个子最高的女生。一开始她还不想和我配戏,结果我和她比,我的身高是一米七五,正好比她高一厘米。”犹记得他说到这,手指着照片中两人差可相匹的个头,哈哈大笑。
梅祖彬女士就是当年许渊冲翻译《别丢掉》相赠的女生吗?我没有问,也从来没有在可考的文字中见到相关的记述。这其实无关紧要,天地阴阳,铄劲成雄,熔柔制雌,而况开风气之先的西南联大,更不会将“男女大防”列为成年学生的雷池禁区。仪表堂堂,风华正茂的许渊冲喜欢哪个姑娘,递过纸条、写过情诗,甚至当面表白,都是昔年的孟浪,暮年的追怀,人生回味诸般里最甜的那一桩。
西南联大校友在京聚会。许渊冲(二排左一),梅校长的女儿梅祖彬(二排左二)。
那次拜访,还有一件事既能见得许渊冲的“狂”,又能得见他的情趣。《西厢记》中有一句最著名的‘露滴牡丹开’,略懂床帏之私,这句话的别有深意,自有会意。许渊冲的表叔,翻译家熊式一译的是,“露水滴下来,牡丹盛开”。后来许渊冲再去译《西厢记》,认为露水代表张生,牡丹代表的是崔莺莺,“这一句描绘的是他们美好的爱情,是在写男女之事,有这个意象但不能明说,又要人能理解到这层意思。我的译本就译成,‘The dew drop drips/The peony sips with open lips.’drips、lips还押着韵,翻得简直绝了!现在我敢吹这个牛,后人要超过我也很难、很难。”
自视甚高,那是他有著作等身的成就可标榜,有苦心孤诣自成体系的翻译论说可资凭,更有那迟来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为背书。更何况,又有谁会把一个老人的骄傲,真正视作狂妄?他越是真的骄傲,越是让人觉得,他是真的可爱啊。
许渊冲先生老顽童的一面,更在他和西南联大同班同学杨振宁晚年雅集中可见一斑。据媒体报道,2004年左右,杨振宁和翁帆新婚不久,老同学许渊冲做东小聚。席间,许渊冲递给弟子、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王强两页纸,让王强去念给杨振宁听。上面是打印出来的《一树梨花压海棠》诗的英、法译文。杨振宁有一点耳背,王强走到他身边先用英文、再用法文大声念了一遍,举座皆乐。
许老90岁时,清华大学约了三位90岁老人一起过生日,有王希季(1921年生,“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何兆武(1921年生,历史学家),还有杨振宁翁帆夫妇等,大家一起吃了个饭。
乐在切题而又无伤大雅。《一树梨花压海棠》本是北宋词人张先和苏轼,两位老友间的酬酢调侃,“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且看,许老是怎么译的?“The bridegroom is eighty and eighteen the bride. White hair and rosy face vie side by side. The pair of love-birds lie in bed at night. Crab-apple overshadowed by pear white.”一样是译得节节押韵,而“rosy face”一句,更能使人联想到他当年将“不爱红装爱武装”译作“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的才思敏捷。在“文革”期间,受到红卫兵胁迫,他曾不情愿地把这浑然天成的译句改成了,“They love to be battle-dressed, and not rosy-gowned.”也算译得上佳了。
《书剑恩仇录》中,金庸借乾隆送陈家洛佩玉上之刻字,道出自己人生特别推崇的境界,“情深不寿,强极必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其中,“情深不寿”四个字,怕早已深深刻进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心怀,成为他们尤其是岁过中年,修身养性的律令。但许渊冲似乎从来不愿意遮掩自己的情感,不管是对待初恋,还是术业上的论敌,他都敢于直抒胸臆。他活了100岁,今晨在睡眠中“走得很安详”,更是对“喜怒忧思悲恐惊”所谓七情与脏腑致病,中医劝诫的反动。
夫人照君的卧室依旧保持原样,两位的形象还印在靠枕上。 王诤 摄
在许老府上,我曾看到夫人照君的卧室,基本保持逝者生前的样子,床铺的枕头上甚至还套了层塑料薄膜。据媒体报道,2018年,照君去世,许渊冲在葬礼上嚎啕大哭。第二天,97岁的老人一个人在家,依雷打不动地坐在电脑前做翻译。照君曾如此评价夫君,“许先生很爱美的,一生都在追求美,唯美主义。”或许爱美的人,都不愿意暧昧地活着。在这个年轻人动辄“躺平”,中年人不假猥琐“我命油我不油天”的时代,许渊冲留给我们除了煌煌译著,更是他音容宛在的真性情。
在今年4月出版的《许渊冲百岁自述》一书中,他曾专门在“西南联大”章中辟出一节谈“一代人的爱情”。“当时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他们的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据说陈岱孙和周培源在美国留学时同爱上了一个女同学;回国后,这个女同学成了周培源的夫人,陈岱孙就终身不婚,但却成了周培源家的常客……和陈岱孙一样,金岳霖确实爱上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因为愿破坏朋友的婚姻,宁可自己牺牲。这就是叶公超说的宗教精神,哲学家金岳霖和经济学家陈岱孙都在恋爱中付诸实行了。”
“他们这一代人的言行对我们下一代产生了不少的影响。”末了,许渊冲写道。
《许渊冲百岁自述》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