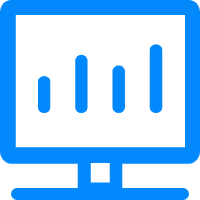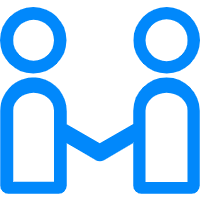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关注
摘要:朝阳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其建城之始,可以追溯到史书记载的黄龙亭。东汉时期,黄龙亭隶属辽东属国昌黎道,其治所在柳城。前燕慕容皝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建都,即以黄龙亭为基址,名之为龙城。推溯地名可能涵括的历史深度,黄龙亭应是黄帝族的史迹遗存。慕容皝与其父慕容廆“以棘城即颛顼之墟”一脉相承,在启导边疆民族的认同意识,推动黄帝文化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核心理念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朝阳;昌黎;黄龙亭;龙城
位于辽宁西部的朝阳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追本溯源,大多数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柳城。史载柳城肇建于舜帝,目前的考古实证也已推溯到战国时期。但遗憾的是这座柳城并不在朝阳城里,而是在城南袁台子村。朝阳城第一次被称为柳城是东晋太和五年(370年)前燕灭亡之后的前秦,论年代自然晚于龙城。鲜卑慕容氏建都龙城是中国4世纪的一件大事,文献多有记载,举如《十六国春秋》云:“咸康七年春正月,(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福德之地也。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龙城,构门阙、宫殿、庙园、籍田,遂改柳城为龙城县。”咸康七年即公元341年,龙城历前燕、后燕和北燕而成为“三燕”故都,去今已近1700年。因此人们又普遍把龙城视为朝阳城的开辟之始。金毓黻《东北通史》就曾断言:“兹以《通鉴》建龙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二语证之,龙山者,今朝阳县城东之凤凰山也,中隔大凌河,相去不过数十里,以城近龙山,故曰龙城。以此例彼,则知龙城之建,亦不过在旧柳城之北鄙,别觅佳地,以建新城耳。”以为龙城因龙山而得名,始于前燕。
其实,追溯朝阳建城史的源头仅到前燕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北凉阚骃《十三州志》的记载,朝阳城的真正起点最晚应在西汉,而追溯其历史景深,又与红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辽东属国昌黎道治西汉柳城
阚骃《十三州志》是这样记载的:“辽东属国都尉治昌黎道,有黄龙亭,魏营州刺史治。”可见,早在慕容皝建都龙城以前,朝阳已经建城。
为了厘清朝阳这座古都的“龙脉”缘起,首先要强调一点,即阚骃所谓“十三州”,指的是“两汉地制”,而非当时的行政区划。《十三州志》上追三代,下及十六国,涉猎甚广,但主要还是记录两汉史事,因此书中所述历史地理均以两汉时期的名称为基准。书中不言龙城而称黄龙亭,原因在此。按营州始置于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治龙城,而辽东属国是东汉安帝(106—125年在位)分析辽东、辽西两郡6县所置,其时尚无龙城,只有黄龙亭。阚骃约生于公元380年至452年,《十三州志》则撰成于北魏灭凉(439年)前后,也就是说,阚骃不仅亲眼见证了后燕、北燕的灭亡,而且当时专记“三燕”的史著如杜辅《燕记》、范亨《燕书》、封懿《燕书》、崔逞《燕纪》等也已行世,龙城的前尘往事纵非尽人皆知,但至少不乏丝迹可寻。惜原书至宋明间亡佚,有关龙城的这段记载幸赖郦道元《水经注》引据而存世,字数虽然不多,内蕴的信息却十分丰富,值得深入解读。
秦汉间“凡县主蛮夷曰道”。黄龙亭上属昌黎道,即昌黎县。如果按所在地划分,此昌黎不在顾炎武“五昌黎”之内,因为涉及黄龙亭的定位,需加以明确。《东北历代疆域史》认为:“前汉时西部都尉柳城县(原注:故县址在今之朝阳南数十里),安帝时为辽东属国都尉治所。”对此,张国庆《东汉“辽东属国”考略》也有详尽论述:“西汉时的交黎,东汉时已改称昌黎,同时又有天辽、夫黎之称,并已由今大凌河城西迁至今朝阳市南……即原西汉柳城县治地,旧址在今朝阳市南约二十里处的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本文赞同这一看法,理由除去此说的史料基础扎实,信而有征,还因为其立论是以属国性质的总体考察为支撑,而非一味牵缠,泥于琐屑而忽略大势。
两汉属国是秦代属邦制度的延续,内附的游牧民族“存其国号而属汉朝”,中央政府在管理上也相应地采取了“因其故俗”的羁縻制,境内各族依然保有过去的部落组织和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游徙不定。因此属国是“稍有分县,治民比郡”,有别于中原的“城国”制度,属于“双重管理”。安帝置辽东属国,主要是为安置东汉初年作为“蕃蔽”入塞的乌桓人。其最高长官都尉,原为西汉在少数民族地区正式设郡之前实行“军管”的武职,后演变成郡守副贰,至东汉时期因属国置于边郡,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一地,安帝始命其兼理民事,称之为“别领”,其属官自然也有县令、长吏之名,余如王、君、邑长、仟长、佰长、目长则一律由部落首领担任,大抵如隋唐“即其部落列置州县”,亦即“大部落就是州府,小部落就是县”,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划地而治。因此,有学者通过对东汉属国设置背景、管辖对象等分析,提出“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的观点,但对官署之流动性的估计仍显不足。客观地看,羁属关系本非牢不可破,尤其是至东汉末期,国势衰微,绥边乏力,受制于乌桓和鲜卑,辽东属国及辽西郡所属县道或勉强维持,或弃地南移,实大势所趋。退一步说,即便确如有些学者所论,昌黎县曾经设治于今义县或凌海市境内,为形势所迫,也难免随时迁转。根据《后汉书》刘昭注,辽东属国位于“洛阳东北三千二百六十里”,而辽西郡则在“洛阳东北三千三百里”,辽东属国距离洛阳少于辽西郡40里。这个数字不一定精确,但大致可以看出,无论按照哪一条古道来衡量,辽东属国昌黎道都只能在辽西郡阳乐县(通说在今锦州附近)之南或西,而义县及凌海市恰好相反。
有关东汉昌黎曾经设治于柳城的史证,还有李泰主编的《括地志》,内云:“后汉省柳城入昌黎,慕容皝都龙城,本昌黎县地,相去数十里而近也。”分析《十三州志》各种辑本的来源,《括地志》这类条目很可能是《十三州志》的转述或改写。依照“数十里而近”的里程求索,柳城之外,其余各家考证的地点,与今朝阳的直线距离均在八九十公里以上,不可能是其所指。柳城原为辽西郡西部都尉治,其地正当大凌河谷道,素有“肘腋咽喉”之喻,论规格或重要程度不在其他任何一县之下,然而《后汉书》辽东属国、辽西郡均无柳城县,这是说不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汉省柳城入昌黎”,而此昌黎又恰好设治于柳城。由此我们可以弥补以往所论昌黎沿革中的缺环,并校正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置柳城于辽东属国之外的错误。
至于辽东属国何以名为“辽东”而不曰“辽西”,金毓黻先生曾以“不能辽东、辽西并用”释之,择其一而已,试图以“置本郡名”来推断都尉治必在原辽东郡地界,自难成说。当然,从史书里也能找到此后昌黎又迁离柳城的一些零散信息。《后汉书》记赵苞守辽西郡,“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此事发生在熹平六年(177年),昌黎被鲜卑占领,显然已经迁移,柳城又恢复了旧名。不过,这并不能证明昌黎从未设治柳城,也不能因为曹魏另立昌黎于别地而以后推前,两相牵混。
二、龙城的前身即黄龙亭
亭作为军事防御机构始见于战国,秦汉间演变为基层行政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按此种说法,亭介于里、乡之间,里隶属亭,亭隶属乡。当代学者则普遍认为“十里”的“里”指步里,非里居之义,亭与乡、里不在同一行政系列,而与“五里一邮”相属,由专管治安捕盗的县尉统领。不过“十里一亭”大体上是成立的,因为无论是政区规划还是道路设计,都要考虑空间因素。实地测量,柳城故址袁台子村距离朝阳市区12公里,以秦汉10里约当今8里计,正相符合,朝阳即黄龙亭旧地无疑。
目前在亭的问题上还存在许多争议,但有几点已达成共识。其一,类型不同。亭有都亭、市亭、乡亭、门亭、道亭之分,其性质和管理范围也略有异同。其二,功能多样。亭本身兼有递驿、侦候、治安、止宿之职,因所在地不同,其功用各有侧重,并随形势需要而变化。其三,应有辖地。秦汉列侯有县侯、乡侯,也有亭侯,可见亭是管辖一定区域的,因而才能作为食邑封赏功臣。
关于亭的构成及样貌,就其一般情况而言,顾炎武总结了三点:一是“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二是“必有城池,如今之村堡”;三是“必有人民,如今之集市”。其中“必有城池”是亭的主要特征,“城,以盛民也”,没有城,其他都无从谈起。古代文献经常亭、城互称,而置于边塞的亭,又往往与障(小型城堡)连称。民国《朝阳县志》卷10《古迹》记载无考废城数座,一在“县东北九十里”,一在“县北十里”,另有两座分别在“县西北青沟梁”和“大青山上”,基本分布在柳城西北燕、秦长城和汉代烽燧(墩台长城)沿线内侧,确切地说都属于屯兵的亭障,历代沿袭,发展成类似村镇的聚落。只可惜今已不能一一考实,除了黄龙亭,只知道还有一座曲水亭,借此可以对黄龙亭作进一步的了解。
曲水亭见于《前燕录》。咸康二年(336年),同时驻牧于辽西的另两个鲜卑部落即段氏和宇文氏,与慕容氏争夺柳城,“(段)辽别遣弟兰帅步骑数万屯于曲水亭,将攻柳城西曲水”,未果。昱年,慕容皝“筑好城于乙连东,使折冲将军兰勃戍之,以逼乙连。又城曲水,以为勃援”。曲水,《资治通鉴》别作回水,推测应为今大凌河某一支流,无确考。但于此可知,曲水亭位于柳城之西,东与黄龙亭互为犄角,显示出军事要塞的一般情形。慕容皝先建曲水城,后建龙城,均是由亭障改扩而成。换言之,慕容皝建都龙城之前,此地至少曾经出现过人烟攒集的一幕。说是“曾经”,是因东汉末期,战乱叠起,百姓纷纷逃离,众多亭障也人去城空。其时,公孙瓒任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这座空亭史书没有留下名号,大概是一座普通的小亭。一座小亭能容纳数十骑,足见古代的亭与今天的亭不同。
同样,作为柳城属地,黄龙亭在辽西鲜卑诸部之间也历经数次争夺。慕容氏与柳城渊源甚深,早在曹魏时期莫护跋即以军功拜率义王,建国于棘城之北(今北票市境),其孙慕容涉归又“以全柳城之勋,进拜鲜卑单于”。估计慕容涉归参与的这场柳城保卫战是在鲜卑诸部间展开的,作为胜出一方,显然慕容氏的领地已延展到黄龙亭一带。但奇怪的是,慕容涉归随后却率部“迁邑于辽东北”。为什么?据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所述,鲜卑宇文氏自“太康之世据有黄龙”。这等于说,在公元280年至289年期间,慕容涉归丢了黄龙亭,所谓“迁邑于辽东北”并非出于游牧之需,而是战败后的一次逃亡!《前燕录》记“涉归与宇文鲜卑素有隙”,慕容廆“将修先君之怨”,原来是指宇文氏侵占了他们家园。这片土地重新回到慕容氏手中,已是四五十年之后,如前所述,宇文氏联合段氏几次试图收复柳城,无奈此时慕容氏已今非昔比。宇文氏和段氏亡国后,其领土纳入慕容氏的版图,黄龙亭也随之变成了前燕腹地。
前燕于咸康七年建都黄龙亭。择地建都,一般首先要考虑区位优势和人居环境,但从史料上看,慕容皝所谓“福德之地”,最在意的恐怕还是“黄龙”二字。慕容皝一向以“真龙”自命,对他而言,创建新都不过是托情寄志的政治手段,由黄龙亭而龙城,以此宣示慕容氏逐鹿中原、建立帝业的“鸿渐之始”才可能是其本意。因而早在迁都之前,他便开始大造声势。
后来的故事自然也是按照预设的脚本继续演绎下去。据说,前燕迁都龙城不久,城东的龙山(今凤凰山)突然腾空飞起一黑一白两条巨龙,“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于是慕容皝借题发挥,又给新建的宫城起了一个别有意味的名号——和龙宫,后来龙城又名和龙城,龙山又名和龙山,皆由此而来。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而此类诞妄不经的“天降祥瑞”却层出不穷。其实,所谓“黑白二龙”很可能是大凌河流域常见的龙卷风,让慕容皝拿来做成了噱头。仅就字面理解,“和龙”似取“双龙和合”之义,以象天下允协。显而易见,这是依照“君权神授”的套路编造出来的虚假故事,却很容易让后人信以为真,以为这是龙城一名的来源,黄龙亭变身龙城之前的历史真相反倒被淹没。
直到北燕,谜底才被捅破。太兴五年(435年),最后一任北燕国主冯弘,为联手抵抗北魏入侵,主动称藩于南朝刘宋。《资治通鉴》记之曰:“燕王数为魏所攻,遣使诣建康称藩奉贡,诏封为燕王;江南谓之黄龙国”。胡三省注:“以其都和龙也。今北国以和龙为黄龙府。”《宋书》亦云:“(冯)跋自立为主,自号燕王,以其治黄龙城,故谓之黄龙国。”初看,不免一头雾水:自前燕以至北燕,龙城或和龙城已是地道的“百年老号”,刘宋何以要说成“黄龙城”?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在宋人眼里,龙城或和龙城是鲜卑人所立名号,而冯弘是汉人,封爵不能不遵汉法,故名之为“黄龙”而不称“和龙”,这说明当时南方人对龙城的渊源并不陌生。胡注似乎是在暗示“和龙”实即“黄龙”的音变,然语焉不详。他所处的时代,“黄龙府”一般指辽太祖平渤海扶余府之后改置的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石重贵墓志》出土以前,正因为不知“黄龙府”的确切所指,石晋的北迁路线一度成为谜团。因此,“和龙”究为何义,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应当注意,检索二十五史,《晋书》《魏书》除外,《宋书》《隋书》《北齐书》以及新、旧《五代史》,以“黄龙”指称龙城的频次明显高于“和龙”。翻阅其他史料,除去前面提到的庾信,如慧皎《高僧传》述龙城名衲昙无竭、昙顺等七八人无不称籍“黄龙”,还有郦道元《水经注》记白狼水的流经、道宣《续高僧传》记宝安法师奉敕置塔于营州,以及众多唐代石刻资料如杨和、孙道、左才、韩相等墓志亦皆如此,抛开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不论,从中不难看出古人正本清源的良苦用心。
此外,史料中还有黄龙道、黄龙县、黄龙山等一系列名目,也都是从黄龙亭衍化而来,与朝阳有关。其中武则天设立的黄龙县,是古代朝阳最后一个以“黄龙”为名的建制,初隶营州都督府,为契丹十七州之一信州治,至神龙初(705年)改属幽州——自此以后,“黄龙”一名便彻底淡出了朝阳历史。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东汉辽东属国是在西汉郡县基础上建立的,汉承秦制,而秦代在东北设置的郡县又是沿袭战国燕的建制,故黄龙亭的启建不会比西汉设置柳城县更晚,最迟也应断定在西汉初期。自此算起,“黄龙”一名沿用了900余年,堪称是古代朝阳第一张历史文化名片。
三、黄龙亭的史学价值
众所周知,龙是由原始图腾演变而成的一种具有浓郁的华夏民族特点的文化符号。而在古代传说中,黄龙则被奉为“神灵之精”,是黄帝轩辕氏土德的象征,代表真命天子。它与朝阳联系在一起,不能没有原因。
就一般规律而言,地名大都是依据当地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而命名。朝阳位于红山文化核心区,而红山文化又是以龙和玉为标志与黄帝文化相对应的一种文化,“黄龙”作为地名出现在此不应是偶然现象,所谓“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查考史著,五帝之一的黄帝在卜辞中书作“黄”(无谥号),而在神话传说中却被塑造成黄龙的化身,他不仅有“黄龙之体”,而且临终又化为黄龙飞升,据说其玄孙大禹也是黄龙转世。所以者何?通过古文字学和考古学双重印证得出结论,“黄”乃“璜”(半圆形的玉器)之本字,指玉,象佩玉之形。由此可窥见神话传说所蕴含的古史原貌。究其实,神话传说演绎的“黄龙”,初始不过是象征图腾的礼玉及其作为法器的功能延伸,其背后的隐喻也不过是黄帝一族以玉通神、随玉而葬的信仰习俗。黄帝的真实身份不仅仅是当今学者所说的佩玉的享有者,作为世代因袭的氏族首领,他们应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Charisma)型人物,在以玉传信,以玉示德的同时,其所扮演的“角色”也随之与佩玉同化,乃至以玉为名。黄帝之所以在道教神系中演化成玉帝,也根源于此。
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如今以“红山”命名的考古文化,古代先民并非一无所知。事实上,代际相传的群体记忆一直都在上古时期延续,《山海经》便是最好的典证。《晋书》关于“(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的记载,也足以说明古人在某些不经意的偶然“发现”中会洞见远古真相。红山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绩之一,是通过古史传说的解读,推迹红山文化分布区即黄帝、颛顼活动区。为此,学者提供了包括化石、玉器以及文献资料在内的一系列物证和书证,可是至今尚无一人将黄龙亭纳入证据链的研究。笔者以为,推溯地名可能涵括的历史深度,黄龙亭应是比“颛顼之墟”及“舜筑柳城”年代更早的黄帝族的史迹遗存,慕容氏很可能因此将其认定为黄帝之都。退一步说,也许事实并非尽皆如此,但客观上,慕容氏自认黄帝之裔,追循先祖遗迹肯堂肯构的民族发展历程却无可置疑。总观慕容氏从紫蒙之野到颛顼之墟,再从黄龙亭建都到迁都蓟、邺的百年历史,与其说是重演了征服中原的一幕长篇大剧,不如说他们完成了文化信仰上的一次归宗壮举。后者在启导边疆民族的认同意识,推动黄帝文化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核心理念的进程中无疑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对于红山文化学者而言,如果将上述古史文献联系起来排比融通,综合考量,势必会更好地揭示黄帝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内在联系及其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而掘井及泉,为红山文化研究推拓出更加广阔的空间。
文章作者:陈守义
文章来源:《渤海大学学报》2021年02期
选稿:甄艺涵
编辑:吴雪菲
校对:徐省之
审定:吴雪菲
责编:汪晨云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